
“没有哪位科学家能比贾雷德·戴蒙德带来更多来自实验室和田野的经验,没有人对社会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也没有人能像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那样阐述得更清晰。在这本可读性极强的著作中,他展示了历史学和生物学如何相互丰富,从而产生对人类状况的更深刻理解。”
——爱德华·O·威尔逊,哈佛大学佩莱格里诺大学教授
“严肃、开创性的人类历史生物学研究似乎每一代人才会出现一次……现在贾雷德·戴蒙德必须被加入这个精英行列……戴蒙德将技术掌握与历史视野、轶事趣味与宏观概念愿景、对资料来源的把握与创造性飞跃融为一体。今年没有出版过比这更好的同类作品,过去许多年也没有。”
——马丁·西夫,《华盛顿时报》
“[戴蒙德的]杰出综合研究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非传统历史著作,融合了人类学、行为生态学、语言学、流行病学、考古学和技术发展等领域的知识。”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贾雷德·戴蒙德博学多识,用通俗易懂的美式英语表达科学概念,几乎完全处理那些关心人类如何发展的每个人都应该感兴趣的问题……[他]为我们提供了种族主义答案的可靠替代方案,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一本极其有趣的书。”
——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洛杉矶时报》
“引人入胜且极其重要……[简单的]概述无法体现这本书巨大的精妙之处。”
——大卫·布朗,《华盛顿邮报书评》
“值得任何关注人类历史最根本层面的人关注。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戴蒙德撰写的人类历史总结,就目前而言,可以说具有达尔文式的权威性。”
——托马斯·M·迪施,《新领袖》
“一本极其引人入胜的书……贾雷德·戴蒙德带我们进行了一次令人振奋的历史世界之旅,让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观念,以及我们在整体事物格局中的位置。”
——克里斯托弗·埃雷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非洲历史教授
“贾雷德·戴蒙德巧妙地汇集了考古学和流行病学等不同探索领域的最新发现,阐明了不同大陆的人类社会在过去13000年中如何以及为何遵循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布鲁斯·D·史密斯,史密森学会考古生物学项目主任
“’为什么人类社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这个问题通常得到的是种族主义的答案。贾雷德·戴蒙德掌握了许多不同领域的信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先发优势和当地条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将吸引广大读者。”
——卢卡·卡瓦利-斯福扎,斯坦福大学遗传学教授
人类社会的命运

W. W. Norton & Company
纽约 伦敦
献给埃萨、卡林加、奥姆瓦伊、帕兰、绍阿卡里、维沃以及我所有其他的新几内亚朋友和老师们——他们是艰难环境的掌控者
版权所有 © 1999, 1997 贾雷德·戴蒙德
版权所有
有关复制本书选段的许可信息,请致函:Permissions,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5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110.
本书正文使用 Sabon 字体排版,标题使用 Trajan Bold 字体排版和制造由 Maple-Vail 图书制造集团完成书籍设计:Chris Welch
国会图书馆出版物编目数据 Diamond, Jared M.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 贾雷德·戴蒙德页码 厘米包含参考文献 ISBN: 978-0-393-06922-8 1. 社会演化 2. 文明——历史 3. 民族学 4. 人类——环境的影响 5. 文化传播 I. 标题 HM206.D48 1997
303.4—dc21
96-37068 CIP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5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 Y. 10110 www.wwnorton.com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Castle House, 75/76 Wells Street, London W1T 3QT
平装版前言
历史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进程
公元前11000年之前所有大陆上发生了什么?
地理如何塑造了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社会
为什么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没有俘获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根源
食物生产开始时间的地理差异
食物生产传播的原因
[第八章 苹果还是印第安人
为什么某些地区的人们未能驯化植物?]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为什么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未被驯化?]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倾斜的轴线
为什么粮食生产在不同大陆的传播速度不同?]
[第三部分 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馈赠
病菌的演化]
[第十二章 蓝图与借用的字母
文字的演化]
[第十三章 需求之母
技术的演化]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的演化]
[第四部分 用五章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 亚力的人民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历史]
[第十六章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东亚的历史]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南岛语族扩张的历史]
[第十八章 半球的碰撞
欧亚大陆与美洲历史的比较]
[第十九章 非洲何以成为黑色
非洲的历史]
[尾声 作为科学的人类历史的未来]
[2003年后记:今日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致谢]
[延伸阅读]
[图片来源]
为什么世界历史像洋葱?
本书试图提供过去13000年来所有人的简史。激发这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在不同大陆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如果这个问题立即让你担心即将读到一篇种族主义论文,请放心:正如你将看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不涉及人种差异。本书的重点在于寻找终极解释,并尽可能向前推进历史因果链。
大多数讲述世界历史的书籍集中于欧亚大陆和北非有文字社会的历史。世界其他地区的本土社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东南亚岛屿、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太平洋群岛——只得到简短处理,主要涉及它们历史中很晚的时期,即它们被西欧人发现和征服之后发生的事情。即使在欧亚大陆内部,关于西欧亚的历史也比中国、印度、日本、热带东南亚和其他东欧亚社会的历史占据更多篇幅。公元前3000年左右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也只得到简短处理,尽管它构成了人类物种500万年历史的99.9%。
这种狭隘聚焦的世界历史叙述有三个缺点。首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很自然地对西欧亚以外的其他社会感兴趣。毕竟,那些”其他”社会涵盖了世界大部分人口以及绝大多数世界民族、文化和语言群体。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是、另一些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和政治力量。
其次,即使对于专门关注现代世界形成的人来说,一部仅限于文字出现以来发展的历史也无法提供深刻理解。并非不同大陆上的社会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彼此相当,然后西欧亚社会突然发展出文字并首次开始在其他方面领先。相反,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有欧亚和北非社会不仅拥有初步的文字,还拥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城市、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和武器、使用驯化动物进行运输和牵引以及机械动力,以及依赖农业和家畜获取食物。在其他大陆的大部分或全部地区,当时这些都不存在;其中一些但并非全部后来在美洲本土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出现,但仅是在接下来的五千年中;而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一个也没有出现。这已经提醒我们,西欧亚在现代世界的主导地位的根源在于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史前时代(我所说的西欧亚主导地位,是指西欧亚社会本身以及它们在其他大陆产生的社会的主导地位)。
第三,专注于西欧亚社会的历史完全绕过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成为了不成比例地强大和创新的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常见答案会援引近因(proximate forces),比如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科学探究、技术,以及在西欧亚人与其他大陆人民接触时杀死他们的致命病菌。但为什么所有这些征服的要素都出现在西欧亚,而在其他地方只是较小程度地出现或根本没有出现?
所有这些要素只是近因因素,而不是终极解释(ultimate explanations)。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美洲原住民墨西哥繁荣,重商主义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繁荣,科学探究没有在中国繁荣,先进技术没有在北美原住民中繁荣,致命病菌没有在澳大利亚土著中繁荣?如果有人通过援引特殊的文化因素来回应——例如,科学探究据称在中国被儒家思想压制,但在西欧亚被希腊或犹太-基督教传统激发——那么这个人仍在继续忽视对终极解释的需求:为什么像儒家思想和犹太-基督教伦理这样的传统没有分别在西欧亚和中国发展?此外,这个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公元1400年之前,儒家中国在技术上比西欧亚更先进。
如果只关注西欧亚社会本身,就不可能理解它们。有趣的问题涉及它们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区别。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也理解所有其他社会,这样西欧亚社会才能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
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走向了与传统历史相反的极端,对西欧亚投入的篇幅太少,而牺牲了世界其他地区。我会回答说,世界其他一些地区非常有启发性,因为它们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包含了如此多的社会和如此多样化的社会。其他读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意本书的一位评论者。带着温和批评的玩笑语气,这位评论者写道,我似乎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洋葱,现代世界只构成表面,而它的层次需要被剥开以寻求历史理解。是的,世界历史确实是这样一个洋葱!但这种剥开洋葱层次的过程是迷人的、具有挑战性的——而且对我们今天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试图把握过去对未来的教训。
J. D.
耶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来自地球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历史的进程非常不同。在末次冰河时代结束以来的13000年里,世界上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拥有金属工具的识字工业社会,其他地区只发展出了不识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保留了使用石器工具的狩猎-采集社会。这些历史不平等在现代世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拥有金属工具的识字社会征服或消灭了其他社会。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历史最基本的事实,但它们的原因仍然不确定且有争议。这个关于它们起源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在25年前以一种简单、个人化的形式向我提出。
1972年7月,我正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的一个海滩上散步,作为生物学家,我在那里研究鸟类进化。我已经听说过一位名叫耶利的杰出地方政治家,他当时正在该地区巡回。偶然地,耶利和我那天朝同一个方向走,他追上了我。我们一起走了一个小时,整个时间都在交谈。
耶利散发着魅力和活力。他的眼睛以一种令人着迷的方式闪烁。他自信地谈论自己,但他也提出了很多探索性的问题并专注地倾听。我们的对话从当时每个新几内亚人心中都在想的一个话题开始——政治发展的快速步伐。巴布亚新几内亚,耶利的国家现在的名称,当时仍由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托管地管理,但独立已经迫在眉睫。耶利向我解释了他在让当地人民为自治做准备方面的作用。
过了一会儿,耶利转变了对话并开始询问我。他从未离开过新几内亚,受教育程度没有超过高中,但他的好奇心是永不满足的。首先,他想知道我在新几内亚鸟类方面的工作(包括我为此得到多少报酬)。我向他解释了不同的鸟类群体如何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殖民新几内亚。然后他问他自己人民的祖先如何在过去数万年里到达新几内亚,以及白人欧洲人如何在过去200年里殖民新几内亚。
对话保持友好,尽管耶利和我所代表的两个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俩都很熟悉。两个世纪前,所有新几内亚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使用石器工具,类似于数千年前在欧洲被金属工具取代的那些工具,他们居住在没有在任何中央政治权威下组织的村庄里。白人到来了,强加了中央集权政府,并带来了新几内亚人立即认识到其价值的物质商品,从钢斧、火柴和药品到衣服、软饮料和雨伞。在新几内亚,所有这些商品被统称为”货物”。
许多白人殖民者公开蔑视新几内亚人,称他们为”原始人”。即使是新几内亚最无能的白人”主人”——1972年他们仍然这样被称呼——也享有比新几内亚人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甚至比像亚利这样富有魅力的政治家还要高。然而,亚利曾经像现在问我一样询问过很多白人,而我也询问过很多新几内亚人。他和我都非常清楚,新几内亚人平均而言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所有这些事情一定都在亚利的脑海中,当他用闪亮的眼睛再次投来洞察的目光时,他问我:“为什么你们白人开发了这么多货物并把它带到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货物?”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触及了亚利所经历的生活核心。是的,普通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与普通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之间。这些巨大的差异必定有强大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亚利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当时我没有答案。专业历史学家们对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分歧;大多数人甚至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在亚利和我进行那次对话之后的这些年里,我研究并撰写了关于人类进化(evolution)、历史和语言的其他方面的文章。这本书写于二十五年后,试图回答亚利的问题。
虽然亚利的问题只涉及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之间生活方式的对比,但它可以扩展到现代世界内更大范围的对比。欧亚大陆起源的民族,特别是那些仍然生活在欧洲和东亚的人,以及那些移居到北美的人,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主导着现代世界。包括大多数非洲人在内的其他民族,虽然已经摆脱了欧洲殖民统治,但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还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最南部的原住民,甚至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被欧洲殖民者削弱、征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灭绝。
因此,关于现代世界不平等的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会按照现在的方式分配,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分配?例如,为什么不是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削弱、征服或灭绝欧洲人和亚洲人?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个问题往前推一步。到公元1500年,当欧洲的全球殖民扩张刚刚开始时,不同大陆上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已经存在很大差异。欧洲、亚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是装备金属工具的国家或帝国的所在地,其中一些处于工业化的门槛上。两个美洲原住民族——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用石器统治着帝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被使用铁器的小国家或酋邦(chiefdom)分割。大多数其他民族——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所有民族、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小部分——以农耕部落的形式生活,甚至仍然以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群体(hunter-gatherer band)的形式生活。
当然,公元1500年时的这些技术和政治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拥有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灭绝使用石器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世界是如何在公元1500年变成这样的呢?
我们可以再次很容易地将这个问题往前推一步,通过借鉴书面历史和考古发现。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最后一个冰河时代(Ice Age)结束时,所有大陆上的所有民族仍然是狩猎采集者。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上不同的发展速度导致了公元1500年的技术和政治不平等。虽然澳大利亚原住民和许多美洲原住民仍然是狩猎采集者,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逐渐发展出了农业、畜牧业、冶金术(metallurgy)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地区也独立发展出了文字。然而,这些新发展在欧亚大陆出现的时间都比其他地方更早。例如,青铜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刚刚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开始,而在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这一技术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了。当欧洲探险家在公元1642年首次遇到塔斯马尼亚人时,他们的石器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部分地区流行的技术更简单。
因此,我们最终可以将关于现代世界不平等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为什么人类发展在不同大陆上以如此不同的速度进行?这些不同的速度构成了历史最广泛的模式,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
虽然这本书最终是关于历史和史前史的,但它的主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压倒性的实践和政治重要性。不同民族之间互动的历史通过征服、流行病(epidemic)和种族灭绝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些碰撞产生的反响在许多世纪后仍未平息,并且在当今世界一些最动荡的地区仍在积极持续。
例如,非洲大部分地区仍在与其近代殖民主义的遗产作斗争。在其他地区——包括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前苏联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内乱或游击战使仍然众多的土著人口与由入侵征服者后裔主导的政府对立。许多其他土著人口——如夏威夷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原住民,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种族灭绝和疾病而人数大幅减少,现在已被入侵者的后裔远远超过。尽管因此无法发动内战,但他们仍在越来越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
除了过去不同民族间碰撞在当今政治和经济上的这些反响之外,还有当今语言上的反响——尤其是现代世界幸存的6000种语言中大多数即将消失,被英语、汉语、俄语和其他几种在近几个世纪说话人数大幅增加的语言所取代。现代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亚利问题中隐含的不同历史轨迹。
在寻求亚利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些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意见。出于几个原因,有些人对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感到不快。
一种反对意见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成功解释了一些人如何统治其他人,这难道不会为统治辩护吗?这难道不是在说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试图改变今天的结果是徒劳的吗?这种反对意见基于一种常见倾向,即混淆对原因的解释与对结果的辩护或接受。如何使用历史解释是一个与解释本身分开的问题。理解更常被用来试图改变结果,而不是重复或延续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试图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试图理解种族灭绝,为什么医生试图理解人类疾病的原因。这些研究者并不寻求为谋杀、强奸、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相反,他们寻求利用对因果链的理解来打断这条链。
第二,讨论亚利的问题难道不会自动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西欧人的美化,以及对西欧和欧化的美洲在现代世界突出地位的痴迷吗?这种突出地位难道不只是过去几个世纪的短暂现象,现在正在日本和东南亚的突出地位背后消退吗?事实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将涉及欧洲人以外的民族。我们不仅关注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互动,还将考察不同非欧洲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那些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在这些地区原住民之间的互动。我们将看到,他们文明的大多数基本要素是由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其他民族发展起来的,然后被引进到西欧,而不是美化西欧血统的民族。
第三,“文明”这样的词,以及”文明的兴起”这样的短语,难道不会传达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部落狩猎采集者是悲惨的,过去13000年的历史涉及朝着更大人类幸福的进步吗?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工业化国家比狩猎采集部落”更好”,或者放弃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转向基于铁器的国家代表”进步”,或者这导致了人类幸福的增加。我自己的印象来自于我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庄之间分配我的生活,即所谓的文明祝福是混合的。例如,与狩猎采集者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更低的被谋杀死亡风险和更长的寿命,但从友谊和大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要少得多。我研究人类社会中这些地理差异的动机不是要赞美一种社会而非另一种,而只是为了理解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亚利的问题真的需要另一本书来回答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如果是这样,答案是什么?
可能最常见的解释涉及隐含或明确地假设民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当欧洲探险家意识到世界各民族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巨大差异时,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源于先天能力的差异。随着达尔文理论的兴起,解释被重新表述为自然选择和进化后裔的术语。技术原始的民族被认为是人类从类人猿祖先进化的演化遗迹。工业化社会的殖民者对这些民族的取代体现了适者生存。随着遗传学的后来兴起,解释再次被重新表述,用遗传学术语。欧洲人被认为在遗传上比非洲人更聪明,尤其比澳大利亚土著更聪明。
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些群体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然而,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西方人仍然私下或潜意识地接受种族主义解释。在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这类解释仍然被公开提出,且毫无歉意。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当谈到澳大利亚土著时,也会认为土著本身有某种原始性。他们看起来确实与白人不同。在欧洲殖民时代幸存下来的土著后裔中,许多人现在发现很难在白人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中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一个看似有说服力的论点是这样的:白人移民在殖民澳大利亚大陆后的一个世纪内,建立了一个基于金属工具和粮食生产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的、政治集权的民主国家。而土著在这片大陆上作为部落狩猎采集者生活了至少4万年,却一直没有金属工具。这是人类发展的两个连续实验,环境完全相同,唯一的变量是占据该环境的人群。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澳大利亚土著与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源于人群本身的差异?
对这种种族主义解释的反对,不仅因为它们令人厌恶,还因为它们是错误的。缺乏可靠证据表明,人类智力差异与技术差异存在平行关系。事实上,正如我马上要解释的,现代”石器时代”民族平均而言可能比工业化民族更聪明,而不是更不聪明。听起来可能矛盾,但我们将在第15章看到,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并不值得因建立一个拥有上述各种优点的有文字的工业化社会而获得通常给予他们的赞誉。此外,直到最近还在技术上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如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在获得机会时,通常能够掌握工业技术。
认知心理学家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寻找现在生活在同一国家、但来自不同地理起源的人群之间的智商差异。特别是,数十年来,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一直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黑人天生不如欧洲裔美国白人聪明。然而,众所周知,被比较的人群在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给检验智力差异导致技术差异这一假设的努力带来了双重困难。首先,即使我们成年后的认知能力也受到童年时期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这使得很难辨别出任何先前存在的遗传差异的影响。其次,认知能力测试(如智商测试)往往测量的是文化学习而非纯粹的先天智力(无论那是什么)。由于童年环境和习得知识对智商测试结果的这些无可置疑的影响,心理学家迄今的努力未能令人信服地证实非白人民族智商存在假定的遗传缺陷。
我对这一争议的看法来自于33年在新几内亚人自己完整社会中与他们共事的经验。从我与新几内亚人工作的一开始,他们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平均而言,他们比欧洲人或美国人更聪明、更机警、更善于表达,对周围的事物和人更感兴趣。在一些人们可能合理地认为反映大脑功能方面的任务上,比如在陌生环境中形成心理地图的能力,他们似乎比西方人熟练得多。当然,新几内亚人在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训练而新几内亚人没有接受训练的任务上往往表现不佳。因此,当来自偏远村庄、未受过教育的新几内亚人访问城镇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愚笨。相反,当我与新几内亚人在丛林中时,我不断意识到自己在他们眼中看起来有多愚蠢,在一些简单的任务上(如沿着丛林小径行走或搭建庇护所)表现出的无能,而这些是新几内亚人从小就接受训练、我却没有的。
很容易看出两个理由,说明我认为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更聪明的印象可能是正确的。首先,数千年来,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人口密集、有中央政府、警察和司法机构的社会中。在这些社会中,人口密集地区的传染性流行病(如天花)历史上是主要的死亡原因,而谋杀相对少见,战争状态是例外而非常态。大多数逃过致命感染的欧洲人也逃过了其他潜在的死亡原因,并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下去。今天,大多数在西方出生的婴儿也能逃过致命感染并繁衍后代,无论他们的智力和所携带的基因如何。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一直生活在人口数量太少、无法演化出人口密集地区流行病的社会中。相反,传统的新几内亚人因谋杀、长期部落战争、事故和获取食物的困难而遭受高死亡率。
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那些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然而,传统欧洲社会中流行病造成的差异性死亡率与智力关系不大,而是涉及依赖于身体化学细节的基因抗性(genetic resistance)。例如,B型或O型血的人比A型血的人对天花有更强的抵抗力。也就是说,在新几内亚,促进智力基因的自然选择可能比在人口更密集、政治更复杂的社会中要残酷得多,而在后者,针对身体化学特性的自然选择反而更强大。
除了这个基因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可能比西方人更聪明。现代欧美儿童花费大量时间被动地接受电视、广播和电影的娱乐。在普通美国家庭中,电视每天开着七个小时。相比之下,传统新几内亚儿童几乎没有这种被动娱乐的机会,而是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在主动做事情,比如与其他儿童或成人交谈或玩耍。几乎所有儿童发展研究都强调童年刺激和活动在促进智力发展中的作用,并强调与童年刺激减少相关的不可逆转的智力发育迟缓。这种影响肯定为新几内亚人表现出的优越平均智力功能贡献了非基因成分。
也就是说,在智力方面,新几内亚人可能在基因上优于西方人,而且他们肯定在逃避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儿童现在成长所面临的毁灭性发育劣势方面更胜一筹。当然,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新几内亚人有任何智力劣势可以用来回答亚力的问题。同样的两个基因和童年发育因素不仅可能区分新几内亚人与西方人,而且通常也区分狩猎采集者和其他技术原始社会成员与技术先进社会成员。因此,通常的种族主义假设必须被颠倒过来。为什么欧洲人尽管可能有基因劣势,并且(在现代)无疑有发育劣势,却最终拥有了更多的货物?为什么新几内亚人最终技术落后,尽管我相信他们有优越的智力?
基因解释并不是亚力问题的唯一可能答案。另一个流行于北欧居民的解释援引了他们家乡寒冷气候对人类创造力和精力的所谓刺激作用,以及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的抑制作用。也许高纬度地区季节性变化的气候比季节性恒定的热带气候提出了更多样化的挑战。也许寒冷的气候要求人们在技术上更具创造性才能生存,因为必须建造温暖的房屋和制作保暖的衣服,而在热带地区,人们可以用更简单的住房和不穿衣服就能生存。或者这个论证可以反过来得出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漫长的冬季让人们有大量时间坐在室内进行发明创造。
虽然以前很流行,但这类解释也经不起仔细审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北欧人民直到最近一千年才对欧亚文明做出根本性的重要贡献;他们只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地理位置上,在那里他们可能接收到在欧亚大陆温暖地区发展起来的进步(如农业、轮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陆,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甚至更加落后。唯一发展出文字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来自南美洲热带地区的赤道附近;而被普遍认为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新大陆社会是公元一千年热带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的古典玛雅社会。
第三种对亚力问题的解释援引了干燥气候中低地河谷的所谓重要性,在那里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反过来又需要集权官僚机构。这一解释的依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已知最早的帝国和文字系统出现在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水利控制系统似乎也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集权政治组织有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低地以及秘鲁的海岸沙漠。
然而,详细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未伴随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兴起而出现,而是在相当长的滞后期之后才出现。也就是说,政治集权化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随后才允许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同一地区,政治集权化之前的所有关键发展都与河谷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无关。例如,在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粮食生产和村落生活起源于丘陵和山区,而非低地河谷。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区,村落粮食生产开始繁荣之后约3000年,尼罗河谷仍然是文化落后地区。美国西南部的河谷最终支持了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但这仅仅是在这些社会所依赖的许多发展成果从墨西哥引入之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仍然被没有农业的部落社会占据。
还有另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杀死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特别是欧洲的枪支、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制成品。这种解释方向正确,因为这些因素确实直接导致了欧洲的征服。然而,这个假设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仍然只提供了一个近因(proximate)解释(第一阶段),识别了直接原因。它引发了对终极原因的寻找: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最终拥有了枪支、最致命的病菌和钢铁?
虽然在确定欧洲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原因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非洲仍然是一个大谜题。非洲是原始人类进化时间最长的大陆,也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可能起源的地方,这里的本地疾病如疟疾和黄热病曾杀死欧洲探险家。如果先发优势有任何意义的话,为什么枪支和钢铁不是首先在非洲出现,从而允许非洲人及其病菌征服欧洲?又是什么导致澳大利亚原住民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者阶段?
从人类社会的全球比较中产生的问题曾经吸引了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大量关注。此类努力最著名的现代例子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12卷本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汤因比特别关注23个先进文明的内部动力,其中22个有文字,19个在欧亚大陆。他对史前史和更简单的无文字社会不太感兴趣。然而,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因此,汤因比没有提出Yali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所看到的历史最广泛的模式。其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现有书籍同样倾向于关注过去5000年的先进有文字的欧亚文明;它们对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原住民文明的处理非常简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更加简短,除了其与欧亚文明最近的互动。自汤因比的尝试以来,历史因果关系的全球综合已经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中失宠,因为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提供了其学科的全球综合。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以及关注传染病对历史影响的学者做出了特别有用的贡献。这些研究引起了人们对拼图某些部分的注意,但它们只提供了所需的广泛综合的片段,而这种综合一直缺失。
因此,对于Yali的问题没有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近因解释是清楚的: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早地发展出枪支、病菌、钢铁以及赋予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其他因素;而一些民族从未发展出这些权力因素。另一方面,终极解释——例如,为什么青铜工具在欧亚大陆部分地区出现较早,在新大陆出现较晚且仅限于局部地区,而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从未出现——仍然不清楚。
我们目前缺乏这样的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智识空白,因为历史最广泛的模式因此仍然无法解释。然而,更严重的是未能填补的道德空白。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明显,无论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还是其他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上的命运各不相同。现代美国是一个由欧洲塑造的社会,占据了从美洲原住民手中征服的土地,并融入了数百万从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奴隶带到美国的黑人后裔。现代欧洲不是一个由撒哈拉以南黑人非洲人塑造的社会,他们也没有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作为奴隶带来。
这些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不是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51%被欧洲人征服,而欧洲的49%被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或非洲人征服。整个现代世界都是由一边倒的结果塑造的。因此,它们必定有不可避免的解释,这些解释比关于谁碰巧在几千年前的某个时刻赢得了某场战斗或发展了某项发明的细节更基本。
这似乎符合逻辑地假设历史的模式反映了人们自身之间的先天差异。当然,我们被教导在公共场合说这些是不礼貌的。我们读到声称证明先天差异的技术研究,也读到声称这些研究存在技术缺陷的驳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被征服的民族在征服或奴隶进口发生几个世纪后仍然形成下层阶级。我们被告知这也不应归因于任何生物学缺陷,而应归因于社会劣势和有限的机会。
然而,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不断看到人们地位中所有那些明显的、持续的差异。我们被保证,对公元1500年世界不平等现象看似透明的生物学解释是错误的,但我们没有被告知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在我们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一致认可的解释之前,大多数人将继续怀疑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毕竟是正确的。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写这本书的最有力论据。
作者经常被记者要求用一句话概括一本长书。对于这本书,这里有这样一句话:“历史对不同民族遵循了不同的路线,是因为民族环境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因为民族本身之间的生物学差异。”
自然,环境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影响社会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古老的想法。然而,如今这种观点并不受历史学家的推崇;它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过于简单化的,或者被讽刺为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而被否定,或者试图理解全球差异的整个主题被搁置为太困难。然而地理学显然对历史有一些影响;悬而未决的问题涉及多大的影响,以及地理学是否可以解释历史的广泛模式。
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来自看似远离人类历史的科学学科的新信息。这些学科首先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应用于作物及其野生祖先;同样的学科加上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应用于家养动物及其野生祖先;人类病菌和相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epidemiology);人类遗传学;语言学;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的考古研究;以及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历史的研究。
这种学科的多样性给旨在回答亚力问题的书的潜在作者带来了问题。作者必须拥有跨越上述学科的专业知识范围,以便可以综合相关的进展。每个大陆的历史和史前史必须同样被综合。本书的主题是历史,但方法是科学的——特别是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的方法,如进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作者必须从第一手经验理解一系列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太空时代文明。
这些要求起初似乎需要一部多作者作品。然而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一个统一的综合。这种考虑决定了单一作者,尽管它带来了所有困难。不可避免地,那个单一的作者将不得不大量流汗以吸收来自许多学科的材料,并将需要许多同事的指导。
在1972年亚力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背景已经引导我进入这些学科中的几个。我母亲是一名教师和语言学家;我父亲是一名专门研究儿童疾病遗传学的医生。由于我父亲的榜样,我在整个学校期间都期望成为一名医生。到七岁时我也成为了一个狂热的观鸟者。因此在大学最后一个本科学年,从我最初的医学目标转向生物学研究目标是一个容易的步骤。然而,在我整个学校和本科时期,我的训练主要是语言、历史和写作。即使在决定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我在研究生第一年几乎退出科学成为一名语言学家。
自1961年完成博士学位以来,我将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分为两个领域:一方面是分子生理学,另一方面是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作为这本书目的的意外收获,进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被迫使用不同于实验室科学的方法。这种经验使我熟悉了设计人类历史科学方法的困难。1958年到1962年生活在欧洲,在生活被20世纪欧洲历史残酷创伤的欧洲朋友中间,让我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因果链如何在历史的展开中运作。
在过去的33年里,我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的田野工作使我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有了密切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进化,我在南美洲、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尤其是新几内亚研究这个课题。通过与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共同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原始的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者到部落农民和渔民,他们直到最近还依赖石器工具。因此,对大多数识字的人来说属于遥远史前时代的奇特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却是生活中最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虽然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小部分,却包含了不成比例的人类多样性。在当今世界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仅限于新几内亚。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因为我需要用将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收集当地鸟类物种名称的列表。
从所有这些兴趣中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一部关于人类进化的非技术性著作,书名为《第三种黑猩猩》。该书第14章名为”意外的征服者”,试图理解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相遇的结果。在我完成那本书之后,我意识到其他现代以及史前时期人类之间的相遇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看到我在第14章中探讨的问题,本质上就是雅利在1972年问我的问题,只是转移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因此最终,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将尝试满足雅利的好奇心——以及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书的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由三章组成。第1章提供了一次人类进化和历史的快速浏览,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与类人猿的分化,一直延伸到大约13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结束。我们将追踪人类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起源到其他大陆的传播,以便理解在通常被归纳为”文明崛起”一词的事件开始之前世界的状态。结果发现,某些大陆上的人类发展在时间上比其他大陆上的发展领先一步。
第2章通过简要考察岛屿环境对历史在较小时间尺度和区域上的影响,为我们探索大陆环境对过去13000年历史的影响做准备。当波利尼西亚祖先在大约3200年前扩散到太平洋时,他们遇到了环境差异很大的岛屿。在几千年内,那个单一的波利尼西亚祖先社会在那些多样化的岛屿上产生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后代社会,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这种辐射(radiation)可以作为一个模型,用于理解自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不同大陆上社会更长时间、更大规模且更不为人理解的辐射,最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和帝国。
第3章通过当代目击者的叙述,重述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此类遭遇,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人群之间的冲突: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一小队征服者在秘鲁城市卡哈马卡,在最后一位独立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整个军队面前俘虏了他。我们可以识别使皮萨罗能够俘虏阿塔瓦尔帕的直接因素链,这些因素在欧洲人征服其他美洲原住民社会时也起了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马匹、识字能力、政治组织和技术(尤其是船只和武器)。对直接原因的分析是本书简单的部分;困难的部分是识别导致这些因素和实际结果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相反可能的结果——阿塔瓦尔帕前往马德里并俘虏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兴起和传播”,由第4章至第10章组成,专门讨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根本原因组合。第4章概述了粮食生产——即通过农业或畜牧业种植食物,而不是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最终如何导致使皮萨罗获胜的直接因素。但粮食生产的兴起在全球各地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世界某些地区的人们自己发展了粮食生产;其他一些人在史前时期从那些独立中心获得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发展也没有在史前获得粮食生产,而是一直保持狩猎采集者的状态直到现代。第6章探讨了推动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众多因素,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发生而在其他地区没有发生。
第7章、第8章和第9章随后展示了农作物和牲畜如何在史前时期从祖先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驯化而来,由那些对结果毫无预见的初期农民和牧民完成。当地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套件(suite)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少数地区成为粮食生产的独立中心,以及为什么它在其中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出现。从那些少数起源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速度比向其他地区快得多。造成这些不同传播速度的一个主要因素,原来是各大陆轴线的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主要是南北向(第10章)。
因此,第3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原住民背后的直接因素,第4章则讲述了这些因素从粮食生产这一根本原因的发展。在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1-14章)中,从根本原因到直接原因的联系被详细追溯,首先是人口密集的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病菌的演化(第11章)。死于欧亚病菌的美洲原住民和其他非欧亚民族,远远多于死于欧亚枪炮或钢铁武器的人数。相反,在新大陆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独特的致命病菌等待着那些想要征服的欧洲人。为什么病菌交换如此不平等?在这里,最近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结果很有启发性,它将病菌与粮食生产的兴起联系起来,在欧亚大陆比在美洲要多得多。
另一条因果链从粮食生产导向了文字,这可能是过去几千年来最重要的单项发明(第12章)。文字在人类历史上只独立演化了几次,在各自地区粮食生产最早兴起的地方。所有其他识字社会都是通过从这些少数主要中心之一传播文字系统或文字概念而实现识字的。因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文字现象对于探索另一个重要的因果关系群特别有用:地理对思想和发明传播的难易程度的影响。
适用于文字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技术(第13章)。一个关键问题是,技术创新是否如此依赖于罕见的发明天才和许多特殊的文化因素,以至于无法理解世界格局。事实上,我们将看到,矛盾的是,大量文化因素使理解世界技术格局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难。通过使农民能够产生粮食剩余,粮食生产使农业社会能够供养不自己种植粮食并发展技术的全职工艺专家。
除了供养书吏和发明家之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供养政治家(第14章)。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相对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仅限于群体自己的领地以及与邻近群体的不断变化的联盟。随着密集、定居、粮食生产人口的兴起,酋长、国王和官僚也随之兴起。这样的官僚机构不仅对管理辽阔和人口众多的领土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索舰队以及组织征服战争也至关重要。
第四部分(“五章环游世界”,第15-19章)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教训应用于各大洲和一些重要岛屿。第15章考察了澳大利亚本身以及新几内亚大岛的历史,后者曾与澳大利亚连接在一个大陆上。澳大利亚的案例,拥有技术最简单的近代人类社会的家园,也是唯一一个粮食生产没有本土发展的大陆,为关于洲际人类社会差异的理论提出了关键性考验。我们将看到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即使邻近新几内亚的大多数民族都成为了粮食生产者。
第16章和第17章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整合到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岛屿的整个地区的视角中。粮食生产在中国的兴起催生了史前人类群体或文化特征或两者兼有的几次大迁徙。其中一次迁徙发生在中国内部,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徙导致整个热带东南亚几乎所有地区的土著狩猎采集者被最终源自华南的农民所取代。还有一次,南岛语族扩张(Austronesian expansion),同样取代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狩猎采集者,并扩散到波利尼西亚最偏远的岛屿,但未能殖民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者来说,东亚和太平洋民族之间的所有这些碰撞具有双重重要性:它们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居住的国家,经济实力日益集中的国家;它们为理解世界其他地方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型。
第18章回到了第3章中提出的问题,即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碰撞。对新大陆和西欧亚大陆过去13000年历史的总结清楚地表明,欧洲对美洲的征服仅仅是两条漫长且大部分独立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些轨迹之间的差异是由可驯化动植物、病菌、定居时间、大陆轴线方向和生态屏障方面的大陆差异所决定的。
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第19章)与新大陆历史既有显著相似之处,也有对比。塑造欧洲人与非洲人相遇的同样因素也塑造了他们与美洲原住民的相遇。但非洲在所有这些因素上也与美洲不同。结果,欧洲征服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创造广泛或持久的欧洲人定居点,除了在最南端。更具持久意义的是非洲内部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班图扩张(Bantu expansion)。事实证明,它是由许多在卡哈马卡、东亚、太平洋岛屿以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上演的相同原因所触发的。
我并不奢望这些章节能够成功解释过去13000年所有大陆的历史。显然,即使我们确实了解所有答案(但我们并不了解),在一本书中完成这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本书充其量只是识别出几组环境因素的组合,我相信它们为Yali的问题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答案。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尚未解释的剩余部分,理解这些将是未来的任务。
题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历史的未来”的尾声,列举了一些剩余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问题中最大的一个是将人类历史确立为一门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与进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等公认的历史科学相提并论。人类历史的研究确实存在真正的困难,但那些公认的历史科学也遇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其他一些领域开发的方法也可能在人类历史领域证明是有用的。
不过,我希望已经说服了你,读者,历史不是”一个接一个该死的事实”,正如一个愤世嫉俗者所说的那样。历史确实存在广泛的模式(patterns),对其解释的探索既富有成效又引人入胜。
比较不同大陆历史发展的一个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个日期大致对应于世界少数地区村落生活的开端、美洲首次无可争议的人类定居、更新世(Pleistocene Era)和末次冰期的结束,以及地质学家所称的全新世(Recent Era)的开始。在此后的几千年内,世界上至少有一个地区开始了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截至那时,某些大陆的人们是否已经比其他大陆的人们抢先一步或具有明显优势?
如果是这样,也许那个领先优势在过去13000年中被放大,为Yali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本章将对所有大陆上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进行快速浏览,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起源直到13000年前。所有这些现在将在不到20页的篇幅中概述。自然,我将忽略细节,只提及在我看来与本书最相关的趋势。
我们现存的近亲是三种幸存的大猿(great ape)物种: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侏儒黑猩猩(也称为倭黑猩猩)。它们仅限于非洲,加上丰富的化石证据,表明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也是在非洲上演的。人类历史,作为与动物历史分离的东西,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那里(估计范围从500万到900万年前)。大约在那个时候,一群非洲猿类分裂成几个群体,其中一个进化成现代大猩猩,第二个进化成两种现代黑猩猩,第三个进化成人类。大猩猩谱系显然在黑猩猩和人类谱系分裂之前稍微分裂了。
化石表明,导致我们的进化谱系在大约400万年前已经实现了基本直立的姿态,然后在大约250万年前开始增加体型和相对脑容量。这些原始人类通常被称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它们显然按此顺序相互进化。尽管大约170万年前达到的直立人阶段在体型上与我们现代人类接近,但其脑容量仍然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石器工具在大约250万年前变得普遍,但它们只是最粗糙的剥落或敲击的石头。在动物学意义和独特性上,直立人不仅仅是猿类,但仍然远远不如现代人类。
所有这些人类历史,在我们起源后大约700万年的最初5到6百万年里,一直局限于非洲。第一个扩散到非洲以外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这一点得到了在东南亚爪哇岛上发现的化石的证实,这些化石通常被称为爪哇人(见图1.1)。最古老的爪哇”人”化石——当然,它们实际上可能属于爪哇女人——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大约100万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认为它们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0万年前。(严格来说,直立人这个名字属于这些爪哇化石,而被归类为直立人的非洲化石可能需要一个不同的名字。)目前,人类在欧洲最早的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但也有更早存在的说法。人们当然会认为,对亚洲的殖民化也同时允许了对欧洲的殖民化,因为欧亚大陆是一个单一的陆地块,没有被主要障碍分隔开。
这说明了一个将贯穿本书的问题。每当某位科学家声称发现了”最早的X”——无论X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化石、墨西哥最早的驯化玉米证据,还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东西——这一声明都会促使其他科学家通过寻找更早的发现来挑战这一说法。实际上,必定存在某个真正”最早的X”,所有关于更早X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几乎任何X,每年都会带来新的发现和声称找到更早X的说法,同时也会对前几年关于更早X的部分或全部说法进行驳斥。考古学家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探索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大约在50万年前,人类化石与较早的直立人(Homo erectus)骨骼开始出现差异,表现为头骨更大、更圆、棱角更少。50万年前的非洲和欧洲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足够相似,因此被归类为我们的物种智人(Homo sapiens),而不是直立人(Homo erectus)。这种区分是武断的,因为直立人(Homo erectus)进化成了智人(Homo sapiens)。然而,这些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在骨骼细节上仍与我们不同,大脑明显小于我们,在人工制品和行为上与我们差异巨大。现代制作石器的民族,如亚力的曾祖父母,会认为50万年前的石器非常粗糙。在那个时期,我们祖先的文化技能中唯一可以确信的重要补充是火的使用。
除了骨骼遗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早期智人(Homo sapiens)没有留下任何艺术品、骨器或其他任何东西。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类,原因显而易见:从东南亚到达那里需要船只。美洲任何地方也没有人类,因为这需要占据欧亚大陆最近的部分(西伯利亚),可能还需要造船技能。(现在的浅白令海峡将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分隔开,在冰河时代海平面反复上升和下降期间,它在海峡和宽阔的洲际陆桥之间交替变换。)然而,造船和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存都远远超出了早期智人(Homo sapiens)的能力。
50万年前之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类种群在骨骼细节上开始相互分化,也与东亚种群分化。13万年前至4万年前欧洲和西亚的人类种群保留了特别多的骨骼,被称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有时被归类为独立物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尽管在无数漫画中被描绘成住在洞穴里的类猿野蛮人,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比我们自己的略大。他们也是第一批留下埋葬死者和照顾病人强有力证据的人类。然而,与现代新几内亚人磨光的石斧相比,他们的石器仍然粗糙,通常还没有制成标准化的多样形状,每种都具有明确可识别的功能。
少数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非洲骨骼碎片比尼安德特人骨骼更接近我们现代的骨骼。已知的同时代东亚骨骼碎片更少,但它们似乎又不同于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至于那个时期的生活方式,最完好的证据来自南非遗址积累的石器和猎物骨骼。尽管10万年前的那些非洲人拥有比尼安德特人同时代人更现代的骨骼,但他们制作的石器本质上与尼安德特人相同,都是粗糙的,仍然缺乏标准化形状。他们没有留下艺术品。从他们捕猎的动物物种的骨骼证据来看,他们的狩猎技能不令人印象深刻,主要针对容易捕杀、完全没有危险的动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屠宰水牛、野猪和其他危险的猎物。他们甚至不能捕鱼:他们紧邻海岸的遗址缺乏鱼骨和鱼钩。他们和尼安德特人同时代人仍然算不上完全的人类。
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起飞,这就是我所说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时期。这次飞跃最早的明确迹象来自东非遗址,那里有标准化的石器和最早保存下来的珠宝(鸵鸟蛋壳珠子)。类似的发展很快出现在近东和东南欧,然后(大约4万年前)出现在西南欧,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与被称为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的完全现代的骨骼相关联。此后,考古遗址保存的垃圾迅速变得越来越有趣,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处理的是生物学上和行为上的现代人类。
克罗马农人的垃圾堆中不仅有石器工具,还有骨制工具,这些骨头的可塑性(例如可以制成鱼钩)显然之前的人类并未意识到。工具被制作成多样化和独特的形状,如此现代化,以至于我们能够轻易识别它们作为针、锥子、雕刻工具等的功能。除了手持刮削器等单件工具外,多件式工具也开始出现。克罗马农人遗址中可识别的多件式武器包括鱼叉、投矛器,以及最终的弓箭,这些都是步枪和其他现代多件式武器的前身。这些能够在安全距离内杀戮的高效手段使得捕猎犀牛和大象等危险猎物成为可能,而用于制作网、线和陷阱的绳索的发明则让鱼类和鸟类被加入到我们的饮食中。房屋和缝制衣物的遗迹证明了在寒冷气候中生存能力的大幅提升,而珠宝和精心埋葬的骨骼遗迹则表明了革命性的审美和精神发展。
在克罗马农人遗留下来的产品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艺术品:宏伟的洞穴壁画、雕像和乐器,这些作品至今仍被我们视为艺术。任何亲身体验过法国西南部拉斯科洞穴中真人大小的公牛和马壁画所带来的震撼力量的人都会立刻明白,它们的创作者在思想上一定和他们的骨骼结构一样现代。
显然,在大约10万到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次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提出了两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涉及其触发原因和地理位置。关于其原因,我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发声器官的完善,因而也是现代语言的解剖学基础的完善,而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其他人则认为,大约在那个时期大脑组织结构的变化,而非大脑尺寸的变化,使得现代语言成为可能。
至于大跃进的发生地,它主要是在一个地理区域、一个人类群体中发生的,从而使他们能够扩张并取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前人类种群吗?还是它在不同地区平行发生的,在每个地区,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种群都是跃进之前生活在那里的种群的后裔?来自大约10万年前非洲的看起来相当现代的人类头骨被认为支持前一种观点,即跃进特别发生在非洲。分子研究(所谓的线粒体DNA)最初也被解读为支持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尽管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存在疑问。另一方面,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生活在数十万年前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头骨展现出的特征,仍然分别存在于现代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身上。如果这是真的,这一发现将表明现代人类是平行演化和多地区起源的,而不是起源于单一的伊甸园。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现代人类局部起源,随后扩散并取代其他地区其他类型人类的证据,在欧洲似乎最为有力。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农人带着他们现代的骨骼结构、先进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来到欧洲。在几千年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而他们作为欧洲的唯一占据者已经演化了数十万年。这一序列强烈暗示,现代克罗马农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远为优越的技术、语言技能或大脑,使尼安德特人感染、死亡或被取代,几乎没有留下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之间杂交的证据。
大跃进恰好与自我们祖先殖民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得到证实的人类地理范围的重大扩展相吻合。这次扩展包括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占据,当时它们连接成一个单一的大陆。许多经过放射性碳定年的遗址证明,在4万到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出现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加上不可避免的一些年代更久但有效性存疑的说法)。在最初的定居后不久,人类就已经扩展到整个大陆,并适应了其多样化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到澳大利亚干燥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
在冰河时代,大量海洋水分被锁在冰川中,导致全球海平面比现在低数百英尺。因此,现在亚洲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婆罗洲、爪哇岛和巴厘岛之间的浅海变成了陆地。(其他浅海峡也是如此,比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当时东南亚大陆的边缘位于现在位置以东700英里处。然而,巴厘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岛屿仍然被深水海峡包围和分隔。当时从亚洲大陆到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仍需跨越至少八条海峡,其中最宽的至少有50英里宽。这些海峡大多分隔着彼此可见的岛屿,但澳大利亚本身从最近的印度尼西亚岛屿帝汶岛和塔宁巴尔岛都看不见。因此,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占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需要水上交通工具,并提供了迄今为止历史上使用水上交通工具的最早证据。直到大约30,000年后(13,000年前),世界其他地方才有使用水上交通工具的有力证据,那是在地中海地区。
最初,考古学家认为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殖民可能是偶然实现的,只有少数人在印度尼西亚某个岛屿附近的木筏上捕鱼时被冲到海上。在一个极端的假设中,第一批定居者被描绘成一个怀着男性胎儿的年轻孕妇。但是,偶然殖民理论的信奉者们对最近的发现感到惊讶,新几内亚以东的其他岛屿在新几内亚本身被殖民后不久,大约在35,000年前也被殖民了。这些岛屿是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的布卡岛。布卡岛在西边最近的岛屿视线之外,只能跨越大约100英里的水域才能到达。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有能力有意识地渡水到达可见的岛屿,并且足够频繁地使用水上交通工具,以至于即使是看不见的遥远岛屿也被反复无意中殖民。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定居可能与另一个重大的首次事件有关,除了人类首次使用水上交通工具和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首次扩展范围之外:人类首次大规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今天,我们把非洲视为大型哺乳动物的大陆。现代欧亚大陆也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物种(尽管不像非洲塞伦盖蒂平原那样明显丰富),比如亚洲的犀牛、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驼鹿、熊和(直到古典时期)狮子。今天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没有同等大小的哺乳动物,实际上没有比100磅重的袋鼠更大的哺乳动物。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前有自己的多样化大型哺乳动物群,包括巨型袋鼠、类似犀牛的有袋动物称为双门齿兽(diprotodonts),体型可达牛的大小,以及一种有袋类”豹”。它还曾经有一种400磅重的鸵鸟般的不会飞的鸟,以及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爬行动物,包括一吨重的蜥蜴、一条巨蟒和陆生鳄鱼。
所有这些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所谓的巨型动物群(megafauna))在人类到来后消失了。虽然对它们灭绝的确切时间存在争议,但几个澳大利亚考古遗址经过仔细发掘,这些遗址的年代跨越数万年,拥有极其丰富的动物骨骼沉积物,但在过去35,000年里没有发现任何现已灭绝的巨型动物的痕迹。因此,巨型动物群可能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后不久就灭绝了。
如此多的大型物种几乎同时消失引发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一个明显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第一批到达的人类杀死,或者被间接消灭了。回想一下,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动物在没有人类猎人的情况下进化了数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极洲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同样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进化,直到现代才看到人类,它们今天仍然无可救药地温顺。如果保护主义者没有迅速采取保护措施,它们早就被灭绝了。在其他最近发现的岛屿上,保护措施没有迅速生效,确实导致了灭绝:其中一个受害者,毛里求斯的渡渡鸟(dodo),几乎成了灭绝的象征。我们现在还知道,在史前时代被殖民的每一个经过充分研究的海洋岛屿上,人类殖民都导致了物种灭绝潮,受害者包括新西兰的恐鸟(moas)、马达加斯加的巨型狐猴和夏威夷的大型不会飞的鹅。正如现代人类走近毫不畏惧的渡渡鸟和岛屿海豹并杀死它们一样,史前人类大概也走近毫不畏惧的恐鸟和巨型狐猴并杀死了它们。
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巨型动物灭绝的一个假说是,它们在大约40,000年前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相比之下,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存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与原始人类(protohumans)共同进化了数十万年或数百万年。因此,随着我们祖先最初较差的狩猎技能慢慢提高,它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化出对人类的恐惧。渡渡鸟、恐鸟以及也许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不幸的是,在没有任何进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面对拥有完全发达的狩猎技能的入侵现代人类。
然而,这个被称为”过度捕杀假说”(overkill hypothesis)的理论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问题上并非没有受到质疑。批评者强调,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灭绝巨兽的骨骼存在被人类捕杀的确凿证据,甚至连与人类共存的证据都没有。过度捕杀假说的支持者回应说:如果灭绝在很久以前就非常迅速地完成了,比如在大约4万年前的几千年内,你很难指望能找到捕杀遗址。批评者则提出反理论:也许这些巨兽是因为气候变化而灭亡的,比如在本来就长期干旱的澳大利亚大陆上发生的严重干旱。争论仍在继续。
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巨兽能在它们数千万年的澳大利亚历史中挺过无数次干旱,却选择几乎同时(至少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死去,而且恰好、仅仅是巧合地发生在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候。这些巨兽不仅在干燥的澳大利亚中部灭绝了,在潮湿多雨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东南部也灭绝了。它们在每一种栖息地都灭绝了,无一例外,从沙漠到寒冷的雨林和热带雨林。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巨兽确实很可能是被人类灭绝的,既有直接原因(被捕杀作为食物),也有间接原因(人类引发的火灾和栖息地改变的结果)。但无论过度捕杀假说还是气候假说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后来的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些灭绝消除了所有本来可能成为驯化候选对象的大型野生动物,使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原住民连一种本地驯化动物都没有。
因此,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殖民化直到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前后才实现。随后不久发生的另一次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是进入欧亚大陆最寒冷的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生活在冰河时代并适应寒冷,但他们向北推进的最远距离只到德国北部和基辅。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缺乏针、缝制的衣服、温暖的房屋以及在最寒冷气候中生存所必需的其他技术。确实拥有这些技术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大约2万年前扩展到了西伯利亚(当然也有一些更早的有争议的说法)。这次扩展可能导致了欧亚大陆猛犸象和披毛犀的灭绝。
随着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定居,人类现在占据了五个适宜居住大陆中的三个。(在本书中,我将欧亚大陆算作一个大陆,并且不包括南极洲,因为南极洲直到19世纪才有人类到达,而且从未有过自给自足的人类种群。)这样只剩下两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它们肯定是最后被定居的,原因很明显:从旧世界到达美洲要么需要船只(即使在印度尼西亚也没有证据表明直到4万年前才有船只,在欧洲则要晚得多)才能横渡海洋,要么需要占据西伯利亚(直到大约2万年前才有人居住)才能穿越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
然而,美洲何时首次被殖民,是在大约14000年到35000年前之间的某个时候,这一点尚不确定。美洲最古老的无可置疑的人类遗骸位于阿拉斯加的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0年,随后在公元前1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在加拿大边境以南的美国和墨西哥出现了大量遗址。后面这些遗址被称为克洛维斯遗址(Clovis sites),以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镇附近的典型遗址命名,那里首次发现了它们特有的大型石矛头。现在已知有数百个克洛维斯遗址,遍布美国下48州并延伸到墨西哥。不久之后,在亚马逊地区和巴塔哥尼亚也出现了人类存在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这些事实表明,克洛维斯遗址记录了人类对美洲的首次殖民,这些人迅速繁衍、扩张并充满了这两个大陆。
人们起初可能会感到惊讶,克洛维斯的后代能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到达距离美加边境以南8000英里的巴塔哥尼亚。然而,这相当于平均每年扩张8英里,对于一个狩猎采集者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他们甚至在一天的正常觅食中就可能走完这段距离。
人们起初可能也会感到惊讶,美洲显然如此迅速地充满了人类,以至于人们有动力继续向南扩散到巴塔哥尼亚。当我们停下来考虑实际数字时,这种人口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洲最终以平均每平方英里略少于一人的人口密度(这对现代狩猎采集者来说是一个较高的数值)容纳狩猎采集者,那么整个美洲地区最终将容纳约1000万狩猎采集者。但即使最初的殖民者只有100人,他们的人数以每年仅1.1%的速度增长,殖民者的后代也会在一千年内达到1000万人的人口上限。1.1%的年人口增长率同样微不足道:在现代,当人们殖民处女地时,观察到的增长率高达3.4%,比如当”邦蒂号”(HMS Bounty)的叛变者和他们的塔希提妻子殖民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时。
克洛维斯猎人遗址在他们到达后最初几个世纪内的大量出现,与考古学记录的毛利人祖先发现新西兰时遗址大量出现的情况相似。早期遗址的大量出现也见于更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对欧洲的殖民,以及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占领。也就是说,克洛维斯现象及其在美洲的扩散的一切特征,都与历史上其他无可置疑的处女地殖民发现相符。
克洛维斯遗址在公元前1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突然涌现,而不是在公元前16,000年或21,000年之前,这可能有什么意义?回想一下,西伯利亚一直很寒冷,在更新世冰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片连续的冰盖作为不可逾越的屏障横跨整个加拿大。我们已经看到,应对极端寒冷所需的技术直到大约40,000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入侵欧洲之后才出现,而人类直到20,000年后才殖民西伯利亚。最终,那些早期西伯利亚人跨越到阿拉斯加,要么通过海路穿过白令海峡(即使在今天也只有50英里宽),要么在冰期白令海峡是陆地时步行穿过。白令陆桥在其断断续续存在的数千年间,宽度可达一千英里,覆盖着开阔的冻原,对于适应寒冷条件的人来说很容易穿越。陆桥最近一次被淹没并再次成为海峡是在公元前14,000年左右海平面上升之后。无论那些早期西伯利亚人是步行还是划船到达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存在人类的最早可靠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
此后不久,加拿大冰盖中出现了一条南北向的无冰走廊,使第一批阿拉斯加人得以通过,并在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附近的大平原上出现。这消除了现代人类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之间的最后一道严重障碍。埃德蒙顿的先驱者们会发现大平原上野生动物成群。他们会繁荣发展,数量增加,并逐渐向南扩散,占领整个半球。
克洛维斯现象的另一个特征符合我们对加拿大冰盖以南首次出现人类的预期。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美洲最初也充满了大型哺乳动物。大约15,000年前,美国西部看起来很像今天非洲的塞伦盖蒂平原,成群的大象和马被狮子和猎豹追逐,还有骆驼和巨型地懒等奇异物种。就像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在美洲,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大多数都灭绝了。澳大利亚的灭绝可能发生在30,000年前,而美洲的灭绝发生在大约17,000到12,000年前。对于那些骨骼最丰富且年代测定特别准确的已灭绝美洲哺乳动物,可以将灭绝时间精确定位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也许最准确测定年代的两次灭绝是大峡谷地区的沙斯塔地懒和哈林顿山羊;这两个种群都在公元前11,100年前后一两个世纪内消失了。无论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这个日期在实验误差范围内,与克洛维斯猎人到达大峡谷地区的日期相同。
发现大量猛犸象骨骼肋骨间夹着克洛维斯矛尖,表明这种日期的一致性不是巧合。向南扩张穿过美洲的猎人,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人类的大型动物,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捕杀,并可能将它们灭绝了。一个反对理论认为,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是由于末次冰期结束时的气候变化而灭绝的,这(让现代古生物学家的解释更加混乱)也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美洲巨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有着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这类理论同样的问题。美洲的大型动物已经经历了之前22次冰期结束的考验。为什么它们大多数选择在第23次,在所有那些所谓无害的人类面前一起灭绝?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栖息地都消失了,不仅在收缩的栖息地,也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大幅扩张的栖息地?因此我怀疑是克洛维斯猎人干的,但这场辩论仍未解决。无论哪种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大多数本可能后来被美洲原住民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物种都因此被消灭了。
同样未解决的问题是克洛维斯猎人是否真的是第一批美洲人。就像每当有人声称第一个发现什么东西时总会发生的那样,关于在美洲发现前克洛维斯人类遗址的说法不断被提出。每年,当这些新说法最初公布时,确实有少数看起来令人信服和激动人心。然后不可避免的解释问题就出现了。遗址中报告的工具真的是人类制造的工具,还是只是天然的岩石形状?报告的放射性碳测年真的正确吗,而不是被可能困扰放射性碳测年的众多难题中的任何一个所否定?如果年代是正确的,它们真的与人类产品有关吗,而不只是一块15,000年前的木炭块碰巧放在一件实际上制作于9,000年前的石器旁边?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克洛维斯前期(pre-Clovis)证据的典型案例。在巴西一个名为Pedra Furada的岩棚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毫无疑问由人类创作的洞穴壁画。他们还在悬崖底部的石堆中发现了一些石头,其形状暗示可能是粗糙的工具。此外,他们还发现了疑似的火塘,其中烧焦的木炭经放射性碳测年约为35,000年前。关于Pedra Furada的文章被权威且高度挑剔的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接受发表。
但是,悬崖底部的那些石头没有一个是明显的人造工具,不像克洛维斯尖器和克罗马农人(Cro-Magnon)工具那样。如果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有数十万块石头从高耸的悬崖上掉落,当它们撞击下面的岩石时,许多石头会被削裂和破碎,其中一些会变得类似于被人类削裂和破碎的粗糙工具。在西欧和亚马逊地区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对洞穴壁画中使用的实际颜料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但在Pedra Furada没有这样做。该地区经常发生森林火灾,产生的木炭会被风和水流定期吹入洞穴。没有证据将35,000年前的木炭与Pedra Furada确凿无疑的洞穴壁画联系起来。尽管最初的挖掘者仍然坚信,但一队未参与挖掘但对克洛维斯前期证据持开放态度的考古学家最近访问了该遗址,离开时并不信服。
目前在北美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克洛维斯前期遗址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Meadowcroft岩棚,据报道与人类相关的放射性碳测年约为16,000年前。在Meadowcroft,没有考古学家否认在许多仔细挖掘的地层中确实存在许多人类文物。但最古老的放射性碳年代说不通,因为与之相关的植物和动物物种是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近代温和气候下的物种,而不是16,000年前冰川时代所预期的物种。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从最古老的人类居住层测年的木炭样本是由克洛维斯后期的木炭混入了更古老的碳组成的。南美最有力的克洛维斯前期候选遗址是智利南部的Monte Verde遗址,至少可追溯到15,000年前。它现在似乎也让许多考古学家信服,但鉴于之前所有的失望,仍需谨慎对待。
如果美洲真的存在克洛维斯前期的人类,为什么现在仍然很难证明他们的存在?考古学家已经挖掘了数百个明确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至11,000年的美洲遗址,包括北美西部数十个克洛维斯遗址、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岩棚以及加州海岸的遗址。在许多这些相同的遗址中,在所有确凿无疑存在人类的考古层下方,更深更古老的地层也被挖掘出来,仍然出土了确凿无疑的动物遗骸——但没有进一步的人类证据。美洲克洛维斯前期证据的薄弱与欧洲证据的充分形成对比,在欧洲,数百个遗址证明了现代人类在公元前11,000年克洛维斯猎人出现在美洲之前很久就已存在。更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证据,那里的考古学家数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这些少数考古学家仍然发现了分散在整个大陆的一百多个明确无疑的克洛维斯前期遗址。
早期人类肯定不是乘坐直升机从阿拉斯加飞到Meadowcroft和Monte Verde,跳过了中间的所有地貌。克洛维斯前期定居的倡导者认为,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时间里,克洛维斯前期人类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或者在考古学上不太明显,原因不明,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比Monte Verde和Meadowcroft最终会被重新解释的说法更难以置信,就像其他声称的克洛维斯前期遗址一样。我的感觉是,如果美洲真的存在克洛维斯前期定居,到现在应该已经在许多地方变得显而易见了,我们不会还在争论。然而,考古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无论哪种解释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我们理解后来的美洲史前史的影响都是一样的。要么:美洲首次定居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并迅速被人类填满。要么:首次定居发生得稍早一些(大多数克洛维斯前期定居的倡导者会认为是在15,000或20,000年前,可能是30,000年前,很少有人会认真声称更早);但这些克洛维斯前期定居者在公元前11,000年之前一直人数很少,或不起眼,或影响甚微。无论哪种情况,在五个适宜居住的大陆中,北美和南美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
随着美洲的占领,大多数大陆和大陆岛屿的可居住地区,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东部的海洋岛屿,都有了人类居住。世界其余岛屿的定居直到现代才完成:地中海岛屿如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大约在公元前8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之间;加勒比海岛屿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岛屿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马达加斯加在公元300年至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冰岛在公元九世纪。美洲原住民,可能是现代因纽特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遍布北极高地。这使得在过去700年里等待欧洲探险家的唯一无人居住地区,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最偏远的岛屿(如亚速尔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以及南极洲。
各大陆不同的定居日期对后续历史有什么意义吗?假设一台时间机器可以将一位考古学家送回过去,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进行一次环球之旅。考虑到当时世界的状态,考古学家能否预测各大陆人类社会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顺序,从而预测今天的世界状况?
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考虑先发优势的可能益处。如果这有任何意义,那么非洲享有巨大的优势:至少比任何其他大陆多了500万年的独立原始人类存在。此外,如果现代人类确实在大约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传播到其他大陆,那将抹去其他地方在此期间积累的任何优势,并给予非洲人一个新的领先起点。此外,人类遗传多样性在非洲最高;也许更多样化的人类会集体产生更多样化的发明。
但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进一步思考: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先发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赛跑的比喻。如果你所说的先发优势是指最初几个开拓殖民者到达后填满一个大陆所需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相对较短:例如,填满整个新大陆只需不到1000年。如果你所说的先发优势是指适应当地条件所需的时间,我承认某些极端环境确实需要时间:例如,在北美洲其余地区被占领后,占领北极高地又花了9000年。但一旦现代人类的创造力发展起来,人们就会迅速探索和适应大多数其他地区。例如,在毛利人的祖先到达新西兰后,他们显然只花了不到一个世纪就发现了所有有价值的石材来源;在世界上一些最崎岖的地形中,只用了几个世纪就杀死了每一只恐鸟;只用了几个世纪就分化成一系列不同的社会,从沿海狩猎采集者到实行新型食物储存方式的农民。
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看着美洲并得出结论:尽管非洲人明显有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早的美洲人最多只需一千年就会超越他们。此后,美洲更大的面积(比非洲大50%)和更大的环境多样性将使美洲原住民比非洲人更具优势。
考古学家可能会转向欧亚大陆并作如下推理。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除了非洲,它被占领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陆都长。非洲在一百万年前欧亚大陆被殖民之前的长期占领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当时的原始人类处于如此原始的阶段。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看看公元前20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间西南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繁荣,看看所有那些著名的艺术品和复杂的工具,并想知道欧亚大陆当时是否已经获得了先发优势,至少在局部地区是这样。
最后,考古学家会转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首先注意到它的面积小(它是最小的大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只能养活少数人的沙漠覆盖,这个大陆的孤立性,以及它比非洲和欧亚大陆更晚被占领。所有这些可能会导致考古学家预测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发展缓慢。
但请记住,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拥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船只。他们创作洞穴绘画的时间显然至少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一样早。乔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和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指出,从亚洲大陆架的岛屿殖民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需要人类学会处理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岛屿上遇到的新环境——这是一个提供世界上最丰富海洋资源、珊瑚礁和红树林的迷宫般的海岸线。当殖民者穿越将每个印度尼西亚岛屿与下一个东边岛屿分隔开的海峡时,他们重新适应,填满了下一个岛屿,然后继续殖民下一个岛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连续人口爆炸的黄金时代。也许正是这些殖民、适应和人口爆炸的循环选择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然后又向西扩散回欧亚大陆和非洲。如果这个场景是正确的,那么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可能在大跃进之后很长时间内继续推动那里的人类发展。
因此,一位回到公元前11,000年的观察者无法预测哪个大陆上的人类社会会发展得最快,但可以为任何一个大陆提出有力的论据。当然,事后看来,我们知道是欧亚大陆。但事实证明,欧亚社会更快速发展背后的实际原因,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公元前11,000年的考古学家所猜测的那些直接原因。本书的其余部分就是探索这些真正原因的旅程。
1835年12月,对于新西兰以东500英里查塔姆群岛(Chatham Islands)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ri)来说,数百年的独立生活以残酷的方式终结了。那年11月19日,一艘载有500名毛利人(Maori)的船只抵达,他们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12月5日又有一船400名毛利人到来。成群的毛利人开始走过莫里奥里人的定居点,宣布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反对的人。当时莫里奥里人若组织起抵抗,仍然可以击败毛利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是毛利人的两倍。然而,莫里奥里人有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反击,而是提供和平、友谊和资源分配。
在莫里奥里人能够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毛利人就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杀死了数百名莫里奥里人,烹煮并吃掉了许多尸体,奴役了所有其他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心所欲地杀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一位莫里奥里幸存者回忆道:“[毛利人]开始像杀羊一样杀我们……[我们]惊恐万分,逃到丛林中,藏在地下的洞穴里,藏在任何能躲避敌人的地方。但这毫无用处;我们被发现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幸免。”一位毛利征服者解释说:“我们按照我们的习俗占领了……我们抓住了所有人。一个也没逃掉。有些人逃离我们,我们杀了他们,其他人我们也杀了——但那又怎样?这符合我们的习俗。”
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这场冲突的残酷结果本来很容易预测。莫里奥里人是一个小规模、孤立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只配备了最简单的技术和武器,完全没有战争经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或组织。毛利入侵者(来自新西兰北岛)来自一个密集的农民人口,长期参与激烈的战争,配备了更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并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行动。当然,当两个群体最终接触时,是毛利人屠杀了莫里奥里人,而不是相反。
莫里奥里人的悲剧类似于现代和古代世界中许多其他这样的悲剧,都是众多装备精良的人对抗少数装备简陋的对手。使毛利-莫里奥里冲突显得格外惨烈而富有启发性的是,这两个群体从共同的起源分化出来还不到一千年。两者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约公元1000年殖民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农民的后裔。不久之后,这些毛利人中的一群人又殖民了查塔姆群岛,成为莫里奥里人。在两个群体分离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岛毛利人发展出更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里人则发展出更简单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莫里奥里人退化为狩猎采集者,而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化的农业。
这些相反的演化路线决定了他们最终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两个岛屿社会差异化发展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有了一个理解大陆上不同发展这个更广泛问题的模型。
莫里奥里和毛利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简短、小规模的自然实验,检验了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在你阅读一整本书来研究环境对非常大规模的影响——过去13,000年来对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前,你可能合理地希望从较小规模的检验中得到保证,证明这些影响确实是重要的。如果你是研究老鼠的实验室科学家,你可能会通过取一个老鼠群体,将这些祖先老鼠分组分配到许多环境不同的笼子中,然后在许多代老鼠之后回来看发生了什么来进行这样的检验。当然,这种有目的的实验不能在人类社会上进行。相反,科学家必须寻找”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即过去人类身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这样的实验在波利尼西亚的定居过程中展开了。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之外,散布在太平洋上的数千个岛屿在面积、隔离程度、海拔、气候、生产力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面差异极大(图2.1)。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岛屿远远超出了水上交通工具的到达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群来自新几内亚北部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的从事农业、捕鱼和航海的人们终于成功到达了其中一些岛屿。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后代几乎殖民了太平洋上每一块可居住的土地。这一过程主要在公元500年完成,最后几个岛屿在公元1000年前后或不久之后定居。
因此,在一个适度的时间跨度内,极其多样化的岛屿环境被定居者殖民,而所有这些定居者都源于同一个创始人群。所有现代波利尼西亚人口的终极祖先基本上共享相同的文化、语言、技术以及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因此,波利尼西亚历史构成了一个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适应,而不受通常在世界其他地方试图理解适应时常常遇到的多波次不同殖民者的复杂情况的干扰。
在这个中等规模的测试中,毛利奥里人(Moriori)的命运形成了一个更小的测试。很容易追溯查塔姆群岛(Chatham Islands)和新西兰的不同环境如何以不同方式塑造了毛利奥里人和毛利人(Maori)。虽然最初殖民查塔姆群岛的那些祖先毛利人可能是农民,但毛利人的热带作物无法在查塔姆群岛寒冷的气候中生长,殖民者除了恢复成为狩猎采集者之外别无选择。由于作为狩猎采集者,他们不生产可供重新分配或储存的作物盈余,因此他们无法支持和养活非狩猎的手工艺专家、军队、官僚和首领。他们的猎物是海豹、贝类、筑巢海鸟和可以用手或棍棒捕获的鱼,不需要更精细的技术。此外,查塔姆群岛是相对较小且偏远的岛屿,只能支持大约2000名狩猎采集者的总人口。由于没有其他可以殖民的可到达岛屿,毛利奥里人不得不留在查塔姆群岛,并学会如何相互相处。他们通过放弃战争来做到这一点,并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带来的潜在冲突。结果是一个规模小、非好战的人口,拥有简单的技术和武器,并且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或组织。
相比之下,新西兰北部(较温暖)地区是波利尼西亚迄今为止最大的岛群,适合波利尼西亚农业。那些留在新西兰的毛利人数量增加,直到他们超过10万人。他们发展出局部密集的人口,长期与邻近人口进行激烈的战争。凭借他们能够种植和储存的作物盈余,他们养活了手工艺专家、首领和兼职士兵。他们需要并发展了用于种植作物、战斗和制作艺术的各种工具。他们建造了精心设计的礼仪建筑和数量惊人的堡垒。
因此,毛利奥里和毛利社会从同一祖先社会发展而来,但沿着非常不同的路线发展。由此产生的两个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彼此存在的认知,并且在许多世纪里没有再次接触,也许长达500年。最后,一艘访问查塔姆群岛途中前往新西兰的澳大利亚捕海豹船将关于”那里有丰富的海洋和贝类;湖泊里满是鳗鱼;这是一片盛产卡拉卡浆果(karaka berry)的土地……居民非常多,但他们不懂得如何战斗,也没有武器”的消息带到了新西兰。这个消息足以促使900名毛利人航行到查塔姆群岛。结果清楚地说明了环境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能。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毛利人-毛利奥里人的碰撞代表了一个中等规模测试中的小测试。我们能从整个波利尼西亚关于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学到什么?不同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社会之间的哪些差异需要解释?
整个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呈现出比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更广泛的环境条件范围,尽管后者定义了波利尼西亚组织的一个极端(简单的一端)。在生存模式上,波利尼西亚人从查塔姆群岛的狩猎采集者,到刀耕火种的农民,再到实行集约化粮食生产、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实践者。波利尼西亚的粮食生产者以不同方式集约化生产猪、狗和鸡。他们组织劳动力建造大型农业灌溉系统,并围建大型池塘用于鱼类生产。波利尼西亚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家庭组成,但一些岛屿也养活了世袭的兼职手工艺专家行会(guilds)。在社会组织上,波利尼西亚社会涵盖了从相当平等主义的村落社会到世界上一些最分层的社会,拥有许多等级森严的血统(lineages)以及成员在各自阶级内通婚的首领和平民阶级。在政治组织上,波利尼西亚岛屿从被划分为独立部落或村落单位的景观,到致力于入侵其他岛屿和征服战争的常备军事机构的多岛原帝国(proto-empires)。最后,波利尼西亚的物质文化从仅生产个人用具到建造纪念性石质建筑各不相同。如何解释所有这些差异?
造成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这些差异的因素至少包括波利尼西亚岛屿之间六组环境变量: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破碎度和隔离程度。在考虑这些因素对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之前,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因素的范围。
波利尼西亚的气候从大多数靠近赤道的岛屿上的温暖热带或亚热带,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温带,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的寒冷亚南极气候各不相同。夏威夷的大岛虽然位于北回归线以内,但山脉足够高,可以支持高山栖息地并偶尔降雪。降雨量从地球上记录的最高值(在新西兰的峡湾地区和夏威夷考艾岛的阿拉凯沼泽)到只有其十分之一的岛屿不等,这些岛屿干旱到对农业来说处于边缘状态。
岛屿地质类型包括珊瑚环礁、抬升的石灰岩、火山岛、大陆碎片以及这些类型的混合体。在一个极端,无数小岛,如图阿莫图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的小岛,是几乎不高出海平面的平坦低矮环礁。其他前环礁,如亨德森岛和伦内尔岛,已被抬升到远高于海平面的位置,构成了抬升的石灰岩岛屿。这两种环礁类型都给人类定居者带来问题,因为它们完全由石灰岩组成而没有其他石头,土壤非常薄,缺乏永久性淡水。在相反的极端,最大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新西兰是一个古老的、地质多样化的冈瓦纳大陆(Gondwanaland)碎片,提供一系列矿产资源,包括可商业开采的铁、煤、黄金和玉石。大多数其他大型波利尼西亚岛屿是从海洋中升起的火山,从未成为大陆的一部分,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抬升的石灰岩区域。虽然缺乏新西兰的地质丰富性,但大洋火山岛至少从波利尼西亚人的角度来看是对环礁的改进,因为它们提供多种类型的火山石,其中一些非常适合制作石器。
火山岛之间也存在差异。较高岛屿的海拔在山区产生降雨,因此这些岛屿受到严重风化,拥有深厚的土壤和永久性溪流。例如,社会群岛(Societies)、萨摩亚、马克萨斯群岛,特别是拥有最高山脉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夏威夷就是如此。在较低的岛屿中,汤加和(在较小程度上)复活节岛也因火山灰降落而拥有肥沃的土壤,但它们缺乏夏威夷那样的大型溪流。
至于海洋资源,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屿被浅水和珊瑚礁包围,许多还包含泻湖。这些环境中鱼类和贝类丰富。然而,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的岩石海岸,以及这些岛屿周围陡降的海底和缺乏珊瑚礁的情况,海产品的产量要少得多。
面积是另一个明显的变量,从最小的永久有人居住的孤立波利尼西亚岛屿阿努塔岛(Anuta)的100英亩,到新西兰微型大陆的103,000平方英里不等。一些岛屿的可居住地形,特别是马克萨斯群岛,被山脊分割成陡峭的山谷,而其他岛屿,如汤加和复活节岛,则由缓缓起伏的地形组成,对旅行和交流没有障碍。
最后要考虑的环境变量是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小,与其他岛屿距离遥远,一旦最初被殖民,这些社会就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发展。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非常偏远,但至少后两者在首次殖民后显然与其他群岛保持了一些进一步的接触,而且这三个地区都由许多距离足够近的岛屿组成,可以在同一群岛的岛屿之间保持定期联系。大多数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或多或少与其他岛屿保持定期接触。特别是汤加群岛距离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和瓦利斯群岛足够近,允许群岛之间进行定期航行,最终使汤加人能够征服斐济。
在简要了解了波利尼西亚多样的环境之后,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差异如何影响波利尼西亚社会。生存方式是研究社会的一个便利切入点,因为它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波利尼西亚的生存依赖于捕鱼、采集野生植物和海洋贝类及甲壳类动物、狩猎陆地鸟类和繁殖海鸟以及粮食生产的不同组合。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屿最初都生活着在没有捕食者的情况下进化出来的大型不会飞的鸟类,新西兰的恐鸟(moa)和夏威夷的不会飞的鹅是最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些鸟类对最初的殖民者来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特别是在新西兰南岛,但它们很快就在所有岛屿上被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被猎杀。繁殖海鸟的数量也迅速减少,但在一些岛屿上继续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海洋资源在大多数岛屿上都很重要,但在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最不重要,因此那里的人们特别依赖他们自己生产的食物。
祖先波利尼西亚人带来了三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在波利尼西亚境内没有驯化其他任何动物。许多岛屿保留了所有这三个物种,但更偏远的波利尼西亚岛屿缺少其中一种或多种,要么是因为独木舟中携带的牲畜未能在殖民者漫长的海上旅程中存活下来,要么是因为死亡的牲畜无法轻易从外部再次获得。例如,孤立的新西兰最终只有狗;复活节岛和蒂科皮亚岛只有鸡。由于无法获得珊瑚礁或富饶的浅水区,陆地鸟类又迅速灭绝,复活节岛民转而建造鸡舍进行集约化家禽养殖。
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三种驯化动物也只能提供偶尔的食物。波利尼西亚的粮食生产主要依赖农业,而在亚南极纬度地区农业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波利尼西亚作物都是热带作物,最初在波利尼西亚以外被驯化并由殖民者带入。因此,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寒冷南部地区的定居者被迫放弃他们祖先在过去数千年中发展起来的农业遗产,再次成为狩猎采集者。
其余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人们确实实行基于旱地作物(特别是芋头、山药和红薯)、灌溉作物(主要是芋头)和树木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的农业。这些作物类型的生产力和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岛屿上差异很大,取决于它们的环境。亨德森岛、伦内尔岛和环礁的人口密度最低,因为土壤贫瘠、淡水有限。温带的新西兰密度也较低,那里对一些波利尼西亚作物来说太冷了。这些岛屿和其他一些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实行一种非集约型的轮作、刀耕火种农业。
其他岛屿拥有肥沃的土壤,但海拔不够高,没有大型永久性溪流,因此无法灌溉。这些岛屿的居民发展了集约化旱地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来建造梯田、进行覆盖、轮作、减少或取消休耕期以及维护树木种植园。旱地农业在复活节岛、小小的阿努塔岛和平坦低矮的汤加变得特别富有成效,那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将大部分土地用于种植粮食。
最富有成效的波利尼西亚农业是在灌溉田地中种植芋头。在人口较多的热带岛屿中,汤加因其海拔低、缺乏河流而无法采用这种方式。灌溉农业在夏威夷最西端的考艾岛、瓦胡岛和莫洛凯岛达到顶峰,这些岛屿足够大、足够湿润,不仅能支撑大型永久性溪流,还能支撑可用于建设项目的大量人口。夏威夷的劳役队(corvée)为芋头田建造了精巧的灌溉系统,产量高达每英亩24吨,是整个波利尼西亚最高的作物产量。这些产量反过来支持了集约化养猪生产。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亚境内也独特地将大规模劳动力用于水产养殖,通过建造大型鱼塘来养殖乳鱼和鲻鱼。
由于这些与环境相关的生计变化,整个波利尼西亚的人口密度(以每平方英里可耕地的人口数量计算)差异很大。下限是查塔姆群岛的狩猎采集者(每平方英里只有5人)和新西兰南岛的狩猎采集者,以及新西兰其他地区的农民(每平方英里28人)。相比之下,许多采用集约农业的岛屿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20人。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达到每平方英里210-250人,夏威夷达到300人。人口密度的上限是每平方英里1,100人,出现在阿努塔高岛上,该岛人口几乎将所有土地都转化为集约粮食生产,从而在该岛100英亩土地上容纳了160人,跻身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自给自足人群之列。阿努塔的人口密度超过了现代荷兰,甚至可与孟加拉国相媲美。
人口规模是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人口数)和面积(平方英里)的乘积。相关面积不是岛屿的面积,而是政治单元的面积,它可能大于或小于单个岛屿。一方面,相邻的岛屿可能合并成一个政治单元。另一方面,单个大型崎岖岛屿被划分为许多独立的政治单元。因此,政治单元的面积不仅随岛屿面积而变化,还随其分裂程度和隔离程度而变化。
对于小型孤立岛屿,如果内部交流没有强大障碍,整个岛屿就构成一个政治单元——如阿努塔的情况,拥有160人。许多较大的岛屿从未实现政治统一,要么是因为人口由分散的狩猎采集者群体组成,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要么是农民分散在大片区域(新西兰其他地区),要么是农民生活在人口稠密但地形崎岖、无法实现政治统一的地区。例如,马克萨斯群岛相邻陡峭山谷的人们主要通过海路相互交流;每个山谷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拥有几千居民,大多数马克萨斯大型岛屿仍然分裂成许多这样的实体。
汤加、萨摩亚、社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的地形确实允许岛内政治统一,产生了拥有1万人或更多人口的政治单元(大型夏威夷岛屿超过3万人)。汤加群岛之间的距离,以及汤加与邻近群岛之间的距离,都足够适中,最终建立了一个涵盖4万人的多岛帝国。因此,波利尼西亚政治单元的规模从几十人到4万人不等。
政治单元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相互作用,影响了波利尼西亚的技术和经济、社会及政治组织。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越专业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探讨其中的原因。简而言之,在高人口密度下,只有一部分人成为农民,但他们被动员起来致力于集约粮食生产,从而产生盈余来养活非生产者。动员他们的非生产者包括酋长、祭司、官僚和战士。最大的政治单元可以组织大量劳动力来建造灌溉系统和鱼塘,从而进一步强化粮食生产。这些发展在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尤为明显,按波利尼西亚标准,这些地方都是肥沃、人口稠密且规模适中的。这些趋势在夏威夷群岛达到顶峰,夏威夷群岛由最大的热带波利尼西亚岛屿组成,高人口密度和大片土地意味着个别酋长可能获得非常庞大的劳动力。
与不同人口密度和规模相关的波利尼西亚社会变化如下。在人口密度低(如查塔姆群岛的狩猎采集者)、人口数量少(小型环礁),或密度和数量都低的岛屿上,经济仍然最简单。在这些社会中,每个家庭制造自己所需的东西;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经济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专业化在较大、人口更稠密的岛屿上有所增加,在萨摩亚、社会群岛,尤其是汤加和夏威夷达到顶峰。后两个岛屿支持世袭的兼职工艺专家,包括独木舟建造者、航海家、石匠、捕鸟人和纹身师。
社会复杂性同样各不相同。同样,查塔姆群岛和环礁拥有最简单、最平等的社会。虽然这些岛屿保留了波利尼西亚拥有酋长的传统,但他们的酋长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标志,住在与平民一样的普通茅屋里,像其他人一样种植或捕捉食物。在拥有大型政治单元的高密度岛屿上,社会区别和酋长权力增强,在汤加和社会群岛尤为明显。
社会复杂性再次在夏威夷群岛达到顶峰,那里的酋长后裔被分为八个等级分明的世系(lineage)。这些酋长世系的成员不与平民通婚,只与彼此通婚,有时甚至与兄弟姐妹或同父异母兄弟姐妹通婚。平民必须在高级酋长面前匍匐。所有酋长世系成员、官僚和一些工艺专家都从粮食生产工作中解放出来。
政治组织遵循着同样的趋势。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礁上,酋长几乎没有资源可以支配,决策通过普遍讨论达成,土地所有权归整个社区而非酋长所有。更大、人口更密集的政治单位赋予酋长更多权力。政治复杂性在汤加和夏威夷达到顶峰,那里世袭酋长的权力接近世界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土地由酋长而非平民控制。酋长通过任命的官僚作为代理人,从平民那里征收粮食,还征召他们参与大型建筑项目,这些项目的形式因岛而异:夏威夷的灌溉工程和鱼塘、马克萨斯群岛的舞蹈和宴会中心、汤加的酋长陵墓,以及夏威夷、社会群岛和复活节岛的神庙。
在18世纪欧洲人到达时,汤加酋邦或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跨群岛帝国。由于汤加群岛本身地理上联系紧密,包含几个地形完整的大岛,每个岛都在单一酋长统治下统一;然后最大的汤加岛(汤加塔布岛)的世袭酋长统一了整个群岛,最终他们征服了群岛外远达500英里的岛屿。他们与斐济和萨摩亚进行定期的远距离贸易,在斐济建立汤加定居点,并开始袭击和征服斐济的部分地区。这个海上原始帝国的征服和管理是通过大型独木舟舰队实现的,每艘能容纳多达150人。
像汤加一样,夏威夷成为一个包含几个人口众多岛屿的政治实体,但由于极度孤立而局限于单一群岛。在1778年欧洲人”发现”夏威夷时,每个夏威夷岛内部的政治统一已经完成,岛屿间的一些政治融合已经开始。四个最大的岛屿——大岛(狭义上的夏威夷)、毛伊岛、欧胡岛和考艾岛——保持独立,控制着(或相互争夺控制权)较小的岛屿(拉奈岛、莫洛凯岛、卡胡拉威岛和尼豪岛)。欧洲人到达后,大岛国王卡美哈梅哈一世迅速推进最大岛屿的整合,购买欧洲枪支和船只,首先入侵并征服毛伊岛,然后是欧胡岛。随后卡美哈梅哈准备入侵最后一个独立的夏威夷岛屿考艾岛,该岛酋长最终与他达成谈判协议,完成了群岛的统一。
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有待考虑的其余变化类型涉及工具和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原材料的不同可获得性对物质文化施加了明显的限制。一个极端是亨德森岛,这是一个抬升出海平面的古老珊瑚礁,除了石灰岩之外没有其他石头。其居民被迫用巨型蛤壳制作石斧。另一个极端是新西兰这个小型大陆上的毛利人,他们可以获得广泛的原材料,尤其以使用玉石而闻名。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波利尼西亚的海洋火山岛,它们缺少花岗岩、燧石和其他大陆岩石,但至少有火山岩,波利尼西亚人将其加工成磨制或抛光的石斧,用于清理农田。
至于制作的器物类型,查塔姆岛民只需要手持木棒和棍棒来杀死海豹、鸟类和龙虾。大多数其他岛民生产各种各样的鱼钩、石斧、珠宝和其他物品。在环礁上,就像在查塔姆群岛上一样,这些器物体积小、相对简单、单独生产和拥有,而建筑只不过是简单的小屋。大型和人口密集的岛屿养活了专业工匠,他们为酋长生产各种威望物品——例如为夏威夷酋长保留的羽毛斗篷,由数万根鸟羽制成。
波利尼西亚最大的产品是少数岛屿上的巨大石质结构——复活节岛著名的巨型雕像、汤加酋长的陵墓、马克萨斯群岛的仪式平台,以及夏威夷和社会群岛的神庙。这种纪念性的波利尼西亚建筑显然朝着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和秘鲁金字塔相同的方向发展。自然,波利尼西亚的结构规模不及那些金字塔,但这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埃及法老可以从比任何波利尼西亚岛屿酋长都多得多的人口中征召劳工。即便如此,复活节岛民还是设法竖立起30吨重的石像——对于一个只有7000人、除了自己的肌肉之外没有其他动力来源的岛屿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因此,波利尼西亚岛屿社会在经济专业化(specialization)、社会复杂性、政治组织和物质产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差异有关,而后者又与岛屿面积、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以及生存机会和强化粮食生产的机会差异有关。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和地球表面相对较小的部分,作为单一祖先社会的环境相关变化而发展起来的。波利尼西亚内部文化差异的这些类别,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类别相同。
当然,全球其他地区的变异范围远大于波利尼西亚内部。虽然现代大陆民族中也包括像波利尼西亚人一样依赖石器工具的族群,但南美洲还产生了精通使用贵金属的社会,而欧亚大陆和非洲人则进一步使用了铁。这些发展在波利尼西亚无法实现,因为除新西兰外,没有波利尼西亚岛屿拥有重要的金属矿藏。欧亚大陆在波利尼西亚开始定居之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帝国,南美洲和中美洲后来也发展出了帝国,而波利尼西亚只产生了两个原始帝国(proto-empire),其中一个(夏威夷)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后才整合形成的。欧亚大陆和中美洲发展出了本土文字,但波利尼西亚却未能出现文字,复活节岛可能是个例外,但其神秘的文字可能是在岛民与欧洲人接触之后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切片,而非世界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完整光谱。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波利尼西亚只提供了世界地理多样性的一小部分。此外,由于波利尼西亚在人类历史上很晚才被殖民,即使是最古老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也只有3,200年的发展时间,而即使是最后被殖民的大陆(美洲)上的社会也至少有13,000年的发展时间。再给几千年时间,也许汤加和夏威夷会达到成熟帝国的水平,相互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并拥有本土发展的文字来管理这些帝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可能会在他们的玉石和其他材料的清单中增加铜和铁工具。
简而言之,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与环境相关的人类社会多样化正在运作。但我们由此只能得知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因为它在波利尼西亚发生了。它在大陆上也发生了吗?如果是这样,导致大陆多样化的环境差异是什么,它们的后果又是什么?
现代最大的人口迁移是欧洲人对新世界的殖民,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多数美洲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征服、数量减少或完全消失。正如我在第1章中解释的那样,新世界最初是在公元前11,000年前后或更早通过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和西伯利亚被殖民的。复杂的农业社会逐渐在远离那条进入路线的南方美洲出现,在完全与旧世界新兴的复杂社会隔离的情况下发展。在那次来自亚洲的最初殖民之后,新世界与亚洲之间唯一有充分证据的进一步接触只涉及生活在白令海峡两侧的狩猎采集者,以及一次推断的跨太平洋航行,将甘薯从南美洲引入波利尼西亚。
至于新世界民族与欧洲的接触,唯一的早期接触涉及在公元986年至约1500年间以极少数量占据格陵兰的诺斯人。但这些诺斯人的访问对美洲原住民社会没有明显影响。相反,从实际角度来看,先进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社会的碰撞是在公元1492年突然开始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原住民密集居住的加勒比岛屿。
随后欧洲-美洲原住民关系中最戏剧性的时刻是1532年11月16日,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秘鲁高地小镇卡哈马卡的首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世界最大、最先进国家的绝对君主,而皮萨罗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称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皮萨罗率领着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处于不熟悉的地形中,对当地居民一无所知,与最近的西班牙人(巴拿马以北1,000英里)完全失去联系,远远超出了及时增援的范围。阿塔瓦尔帕位于他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中心,身边立即围绕着他的80,000名士兵的军队,最近在与其他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获胜。然而,在两位领导人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分钟内,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继续囚禁他八个月,同时索取历史上最大的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在赎金——足够填满一个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度超过8英尺的房间的黄金——被交付后,皮萨罗违背了他的承诺并处决了阿塔瓦尔帕。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西班牙人的优越武器无论如何都会确保西班牙最终的胜利,但这次俘虏使征服更快且无限容易。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权威,臣民们甚至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给了皮萨罗时间,可以不受干扰地派遣探险队前往印加帝国的其他地区,并从巴拿马召集增援部队。当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间的战斗最终在阿塔瓦尔帕被处决后开始时,西班牙军队更加强大。
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对我们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标志着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碰撞的决定性时刻。但它也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导致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因素,本质上与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许多类似碰撞结果的因素相同。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历史的宽广窗口。
那天在卡哈马卡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因为许多西班牙参与者都有文字记录。为了体会那些事件的真实感受,让我们通过整合六位皮萨罗同伴的目击者叙述来重温它们,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埃尔南多和佩德罗:
“西班牙人的谨慎、坚韧、军事纪律、劳作、危险的航海和战斗——最无敌的罗马天主教帝国皇帝、我们天然的国王和主的臣民——将给信徒带来喜悦,给异教徒带来恐惧。出于这个原因,为了我们主上帝的荣耀和为了天主教帝国陛下的服务,我认为写下这篇叙述并将它送给陛下是好的,让所有人都能了解这里所记述的事情。这将归于上帝的荣耀,因为在他神圣的引导下,他们征服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异教徒并将他们带入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这将归于我们皇帝的荣誉,因为由于他的强大权力和好运,这样的事件在他的时代发生了。这将给信徒带来喜悦,因为赢得了这样的战斗,发现和征服了这样的省份,为国王和他们自己带回了这样的财富;并且在异教徒中传播了这样的恐惧,在全人类中激起了这样的钦佩。
“因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何时有如此少的人对抗如此多的人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功绩,跨越如此多的气候带,穿越如此多的海洋,在陆地上跨越如此远的距离,去征服看不见和未知的事物?谁的功绩可以与西班牙人的相比?我们的西班牙人,人数很少,从未有超过200或300人在一起,有时只有100人甚至更少,在我们的时代,征服的领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或者比所有信徒和异教徒王子拥有的都多。我现在只写征服中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写太多,以避免冗长。
“总督皮萨罗希望从一些来自卡哈马卡的印第安人那里获取情报,所以他让人折磨他们。他们承认他们听说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等待总督。总督随后命令我们前进。到达卡哈马卡的入口时,我们看到阿塔瓦尔帕的营地在一里格(league)远的地方,在山脚下。印第安人的营地看起来像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他们有如此多的帐篷,我们都充满了极大的忧虑。在那之前,我们在印度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它让我们所有西班牙人都充满了恐惧和困惑。但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恐惧或后退,因为如果印第安人察觉到我们的任何弱点,即使是我们带来作为向导的印第安人也会杀了我们。所以我们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在仔细观察了城镇和帐篷之后,我们下到山谷并进入了卡哈马卡。
“我们在自己人中间讨论了很多该做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人数如此之少,而且我们已经深入到一个我们无法指望得到增援的地方。我们都与总督会面,讨论第二天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那天晚上我们很少有人睡觉,我们在卡哈马卡的广场上守夜,看着印第安军队的营火。那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景象。大部分营火都在山坡上,彼此如此接近,看起来就像天空中布满了明亮的星星。那天晚上,强者和弱者之间、步兵和骑兵之间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执行哨兵任务。善良的老总督也是如此,他四处走动鼓励他的部下。总督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估计那里的印第安士兵人数为40,000人,但他在撒谎只是为了鼓励我们,因为实际上有超过80,000名印第安人。
“第二天早上,阿塔瓦尔帕的一名使者到达了,总督对他说:‘告诉你的主人,他可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无论他以什么方式来,我都会把他当作朋友和兄弟来接待。我祈祷他能快点来,因为我渴望见到他。他不会遭受任何伤害或侮辱。’
“总督在卡哈马卡的广场周围隐藏了他的部队,将骑兵分成两部分,他把其中一部分的指挥权交给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另一部分的指挥权交给埃尔南多·德·索托。他以同样的方式分配步兵,他自己带领一部分,把另一部分交给他的兄弟胡安·皮萨罗。同时,他命令佩德罗·德·坎迪亚带着两三名步兵和号手到广场上的一个小堡垒,并让他们在那里带着一门小炮驻扎。当所有印第安人,以及阿塔瓦尔帕和他们一起进入广场时,总督会给坎迪亚和他的部下发出信号,之后他们应该开始开炮,号手应该吹响号角,听到号角声,骑兵应该从他们隐藏待命的大院子里冲出来。
“正午时分,阿塔瓦尔帕开始集结部队并向我们靠近。很快,我们看到整个平原上都是印第安人,他们不时停下来等待更多从身后营地中鱼贯而出的印第安人。整个下午,他们以独立分队的形式不断涌出。前方的分队已经接近我们的营地,而更多的部队仍在从印第安人的营地中涌出。在阿塔瓦尔帕前面,有2000名印第安人在清扫他面前的道路,紧随其后的是战士们,其中一半在他一侧的田野中行进,另一半在另一侧。
“首先是一个穿着不同颜色服装的印第安人中队,像棋盘一样。他们向前推进,从地上移除稻草并清扫道路。接下来是三个穿着不同服装的中队,边跳舞边唱歌。然后是一群身穿盔甲、佩戴大型金属板和金银王冠的人。他们携带的金银器物数量如此之多,看到阳光在上面闪耀真是令人惊叹。在他们中间,阿塔瓦尔帕的身影出现在一顶非常精美的轿子上,轿杆的两端包裹着银子。八十名贵族用肩膀抬着他,所有人都穿着非常华丽的蓝色制服。阿塔瓦尔帕本人穿着非常华丽,头戴王冠,脖子上挂着一串大翡翠项链。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轿子上放着一个华丽的马鞍垫。轿子内衬着多种颜色的鹦鹉羽毛,并装饰着金银板。
“在阿塔瓦尔帕身后是另外两顶轿子和两个吊床,里面坐着一些高级首领,然后是几个佩戴金银王冠的印第安人中队。这些印第安人中队在嘹亮的歌声伴奏下开始进入广场,就这样进入并占据了广场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我们所有西班牙人都在等待准备,藏在一个院子里,充满恐惧。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极度恐惧而小便失禁却浑然不觉。到达广场中心时,阿塔瓦尔帕仍然高高地坐在轿子上,而他的部队继续在他身后涌入。
“总督(Governor)皮萨罗现在派遣修士比森特·德·巴尔韦德去与阿塔瓦尔帕交谈,并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服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律法并效忠西班牙国王陛下。修士一手拿着十字架,另一手拿着圣经,穿过印第安人的部队来到阿塔瓦尔帕所在的地方,这样对他说:‘我是上帝的牧师,我向基督徒教授上帝的事情,同样地,我来教导你。我所教导的是上帝在这本书中对我们说的话。因此,代表上帝和基督徒,我恳求你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对你有好处。’
“阿塔瓦尔帕要求看那本书,修士把合上的书递给了他。阿塔瓦尔帕不知道如何打开书,修士正要伸手帮忙时,阿塔瓦尔帕非常愤怒地打了他的手臂一下,不希望书被打开。然后他自己打开了书,对书信和纸张毫无惊讶,把它扔到了五六步远的地方,脸色变得深红。
“修士回到皮萨罗身边,大喊:‘出来!出来,基督徒们!攻击这些拒绝上帝之物的敌狗。那个暴君把我的圣法之书扔到了地上!你们没看到发生了什么吗?当平原上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时,为什么还要对这只傲慢的狗保持礼貌和顺从?向他进军,因为我赦免你们!’
“总督随后向坎迪亚发出信号,他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号角吹响,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从藏身之处冲出,直接冲向挤满广场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群,发出西班牙战斗口号’圣地亚哥!’我们在马上放置了响铃来恐吓印第安人。枪炮的轰鸣、号角的吹响和马上的响铃使印第安人陷入恐慌和混乱。西班牙人扑向他们并开始砍杀。印第安人非常恐惧,以至于他们爬到彼此身上,堆成小山,互相窒息而死。由于他们没有武装,他们被攻击时没有给任何基督徒带来危险。骑兵冲垮了他们,杀死和伤害他们,并继续追击。步兵对留下的人发起了如此猛烈的攻击,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大多数都被剑杀死。
“总督本人拿着剑和匕首,与跟随他的西班牙人一起冲入印第安人群中,以极大的勇气到达了阿塔瓦尔帕的轿子。他无畏地抓住阿塔瓦尔帕的左臂并高喊’圣地亚哥!’,但他无法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上拉下来,因为轿子被举得很高。虽然我们杀死了抬轿子的印第安人,但其他人立即接替他们的位置并继续把轿子举高,就这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制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最后,七八个骑马的西班牙人策马向前,从一侧冲向轿子,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推翻在一边。就这样,阿塔瓦尔帕被俘了,总督把阿塔瓦尔帕带到了他的住处。抬轿子的印第安人和护送阿塔瓦尔帕的人从未抛弃他:所有人都死在了他周围。
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留在广场上,被枪炮声和马匹——这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吓坏了,试图通过推倒一段墙壁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我们的骑兵跳过倒塌的墙壁,冲进平原,大喊:“追那些穿华丽衣服的人!别让任何人逃跑!用矛刺他们!”阿塔瓦尔帕带来的所有其他印第安士兵距离卡哈马卡一英里远,准备战斗,但没有一个人行动,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举起武器。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队伍看到其他印第安人逃跑和喊叫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惊慌失措地逃跑了。这是一个惊人的景象,因为整个山谷在15或20英里的范围内完全挤满了印第安人。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的骑兵还在继续在田野上用矛刺杀印第安人,这时我们听到号角召集我们重新集合回营地。
“如果不是夜幕降临,4万多印第安军队中几乎没有几个能活下来。六七千名印第安人死亡,还有更多人被砍断手臂和受其他伤。阿塔瓦尔帕本人承认,我们在那场战斗中杀死了他7000名士兵。在一顶轿子中被杀的人是他的大臣,钦查的领主,他非常喜欢这个人。所有抬阿塔瓦尔帕轿子的印第安人似乎都是高级酋长和议员。他们全部被杀,还有那些被抬在其他轿子和吊床上的印第安人。卡哈马卡的领主也被杀了,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数量太多,数不清,因为所有随从阿塔瓦尔帕的人都是大领主。看到如此强大的统治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俘虏,真是不同寻常,当时他带着如此强大的军队。确实,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因为我们人数太少了。这是上帝的恩典,恩典是伟大的。
“当西班牙人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拉出来时,他的长袍被撕掉了。总督命令给他送衣服来,当阿塔瓦尔帕穿好衣服后,总督命令阿塔瓦尔帕坐在他旁边,安抚他因发现自己如此迅速地从高位跌落而产生的愤怒和激动。总督对阿塔瓦尔帕说:‘不要把你被击败和俘虏当作侮辱,因为与我同来的基督徒虽然人数很少,我已经征服了比你的王国更大的王国,并击败了其他比你更强大的领主,将皇帝的统治强加给他们,我是皇帝的臣民,他是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国王。我们奉他的命令来征服这片土地,让所有人认识上帝和他神圣的天主教信仰;由于我们良好的使命,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允许这样做,以便你可以认识他,摆脱你过的野兽般的魔鬼生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人数很少,却征服了那支庞大的军队。当你看到你生活中的错误时,你会明白我们奉西班牙国王陛下的命令来到你的土地给你带来的好处。我们的主允许你的骄傲被降低,没有一个印第安人能够冒犯基督徒。’”
现在让我们追溯这次非凡对抗的因果链,从直接事件开始。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会面时,为什么皮萨罗俘虏了阿塔瓦尔帕并杀死了他那么多随从,而不是阿塔瓦尔帕人数多得多的军队俘虏和杀死皮萨罗?毕竟,皮萨罗只有62名骑马的士兵,加上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指挥着约8万人的军队。至于这些事件的前因,阿塔瓦尔帕为什么会在卡哈马卡?皮萨罗是如何来到那里俘虏他的,而不是阿塔瓦尔帕去西班牙俘虏查理一世国王?阿塔瓦尔帕为什么走进了在我们看来,凭借事后诸葛亮的礼物,似乎是如此明显的陷阱?在阿塔瓦尔帕和皮萨罗的遭遇中起作用的因素,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人民以及其他人民之间的遭遇中也起到了更广泛的作用吗?
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剑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支和马匹。面对这些武器,阿塔瓦尔帕没有可以骑着进入战斗的动物的军队,只能用石头、青铜或木制的棍棒、狼牙棒和手斧,加上弹弓和缝制盔甲来对抗。这种装备的不平衡在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和其他民族的无数其他对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唯一能够抵抗欧洲征服数个世纪的美洲原住民是那些通过获得和掌握马匹和枪支来减少军事差距的部落。对于普通的美国白人来说,“印第安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个骑马的平原印第安人挥舞着步枪的形象,就像1876年在著名的小比格霍恩战役中消灭了乔治·卡斯特将军的美国陆军营的苏族战士。我们很容易忘记,马匹和步枪最初对美洲原住民来说是未知的。它们是由欧洲人带来的,并继续改变了获得它们的印第安部落的社会。由于精通马匹和步枪,北美的平原印第安人、智利南部的阿劳卡尼亚印第安人和阿根廷的潘帕斯印第安人比任何其他美洲原住民都更长时间地抵抗入侵的白人,直到1870年代和1880年代白人政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才屈服。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西班牙人的军事装备所战胜的巨大数量劣势。在上面提到的卡哈马卡战役中,168名西班牙人击溃了一支比他们多500倍的美洲原住民军队,杀死了数千名土著居民,而西班牙人一方却没有一人阵亡。一次又一次,皮萨罗随后与印加人的战斗、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人,以及其他早期欧洲人对抗美洲原住民的战役记载都描述了这样的遭遇:几十名欧洲骑兵击溃了数千名印第安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首都库斯科进军期间,发生了四次这样的战斗:在豪哈、比尔卡斯瓦曼、比尔卡孔加和库斯科。这四次战斗分别只涉及80名、30名、110名和40名西班牙骑兵,但每次都面对着数千或数万名印第安人。
这些西班牙人的胜利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美洲原住民盟友的帮助、西班牙武器和马匹的心理新奇性,或者(如经常声称的那样)印加人误以为西班牙人是他们返回的神维拉科查。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最初成功确实吸引了当地盟友。然而,如果他们没有被西班牙人早期独立取得的毁灭性成功所说服,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应该站在可能的赢家一边,许多人就不会成为盟友。马匹、钢制武器和枪支的新奇性无疑让印加人在卡哈马卡陷入瘫痪,但卡哈马卡之后的战斗是对抗已经见过西班牙武器和马匹的印加军队的坚决抵抗。在最初征服后的六年内,印加人对西班牙人发动了两次绝望的、大规模的、精心准备的叛乱。所有这些努力都因西班牙人远为优越的武器装备而失败。
到了1700年代,枪支已经取代刀剑成为欧洲侵略者对抗美洲原住民和其他土著民族的主要武器。例如,1808年,一位名叫查理·萨维奇的英国水手携带火枪和精准枪法抵达斐济群岛。这位名副其实的萨维奇(Savage,意为野蛮)单枪匹马地打破了斐济的权力平衡。在他的众多功绩中,他划着独木舟沿河而上到达斐济的卡萨武村,在距离村庄围栏不到手枪射程的地方停下,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开火。他的受害者如此之多,以至于幸存的村民堆起尸体作为掩护,村庄旁的溪流被鲜血染红。这样的例子——枪支对抗缺乏枪支的土著民族的力量——可以无限重复。
在西班牙人征服印加的过程中,枪支只起了次要作用。当时的枪支(所谓的火绳枪)装填和射击都很困难,皮萨罗只有十几支。它们在能够开火的场合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效果。更重要的是西班牙人的钢剑、长矛和匕首,这些坚固锋利的武器屠杀了防护薄弱的印第安人。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钝棍虽然能够击打和伤害西班牙人及其马匹,但很少能杀死他们。西班牙人的钢制或锁子甲护甲,尤其是钢盔,通常能有效防御棍棒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棉甲对钢制武器毫无保护作用。
西班牙人从马匹中获得的巨大优势从目击者的记述中跃然而出。骑兵可以轻易地在印第安哨兵有时间警告后方印第安部队之前骑过他们,并能追上和杀死步行的印第安人。马匹冲锋的冲击力、机动性、它所允许的攻击速度,以及它提供的抬高且受保护的战斗平台,使步兵在空旷地带几乎毫无还手之力。马匹的效果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第一次与之作战的士兵所激发的恐惧。到1536年印加大叛乱时,印加人已经学会了如何最好地防御骑兵,即在狭窄的山口伏击和歼灭西班牙骑兵。但印加人,像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未能够在空旷地带击败骑兵。当接替阿塔瓦尔帕的印加皇帝曼科的最佳将领基索·尤潘基在1536年围攻利马的西班牙人并试图攻城时,两个西班牙骑兵中队在平地上冲锋,面对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印第安军队,在第一次冲锋中就杀死了基索和他所有的指挥官,并击溃了他的军队。类似的26名骑兵的骑兵冲锋击溃了曼科皇帝本人的精锐部队,当时他正在围攻库斯科的西班牙人。
马匹对战争的改变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们在黑海以北的草原上被驯化。马匹使拥有它们的人能够覆盖比步行远得多的距离,发动突然袭击,并在优势防御力量集结之前逃跑。因此,它们在卡哈马卡的作用体现了一种在6000年间一直保持强大威力的军事武器,直到20世纪初,并最终应用于所有大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的军事主导地位才最终结束。当我们考虑到西班牙人从马匹、钢制武器和盔甲中获得的优势,用以对抗没有金属的步兵时,我们就不应再对西班牙人在面对巨大劣势时始终赢得战斗感到惊讶了。
阿塔瓦尔帕为何会在卡哈马卡? 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出现在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内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场内战使印加帝国陷入分裂和脆弱的境地。皮萨罗很快察觉到了这些分歧并加以利用。内战的原因是天花疫情——这种疾病在西班牙殖民者抵达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通过陆路在南美印第安人中传播,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部分朝臣,随后又立即杀死了他指定的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引发了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王位争夺战。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疫情,西班牙人将面对一个统一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凸显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由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者向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传播的疾病。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腺鼠疫和其他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通过大量杀死其他大陆的人民,在欧洲征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例如,在1520年第一次西班牙进攻失败后,一场天花疫情摧毁了阿兹特克人,并杀死了短暂继承蒙特祖马的阿兹特克皇帝奎特拉瓦克。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引入的疾病在欧洲人本身到来之前就在部落之间传播,据估计杀死了前哥伦布时代95%的美洲原住民人口。北美人口最多、组织最严密的原住民社会——密西西比酋邦,就是在1492年到1600年代末期以这种方式消失的,甚至在欧洲人首次在密西西比河定居之前。1713年的天花疫情是欧洲定居者摧毁南非原住民桑人的最重要的单一步骤。1788年英国人在悉尼定居后不久,第一批使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锐减的疫情就开始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是1806年席卷斐济的疫情,由几名从”阿尔戈号”船只残骸中挣扎上岸的欧洲水手带来。类似的疫情也标志着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
然而,我并不是说疾病在历史上的作用仅限于为欧洲扩张铺平道路。疟疾、黄热病和其他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疾病,是欧洲殖民这些热带地区最重要的障碍。
皮萨罗为何会在卡哈马卡?阿塔瓦尔帕为什么没有试图征服西班牙? 皮萨罗来到卡哈马卡依靠的是欧洲的海洋技术,这种技术建造了将他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送到巴拿马的船只,然后在太平洋上从巴拿马送到秘鲁。由于缺乏这样的技术,阿塔瓦尔帕没有从南美洲向海外扩张。
除了船只本身,皮萨罗的出现还依赖于集中化的政治组织,这使西班牙能够为这些船只提供资金、建造、配备人员和装备。印加帝国也有集中化的政治组织,但这实际上对它不利,因为皮萨罗通过俘虏阿塔瓦尔帕完整地夺取了印加的指挥系统。由于印加官僚机构与其神圣的绝对君主紧密相连,在阿塔瓦尔帕死后就瓦解了。海洋技术加上政治组织,对于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扩张,以及许多其他民族的扩张同样至关重要。
使西班牙人来到秘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文字的存在。西班牙拥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通过文字传播的信息比口头传播的信息范围更广、更准确、更详细。这些信息从哥伦布的航行和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返回西班牙,使西班牙人大量涌入新大陆。信件和小册子既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必要的详细航行指南。皮萨罗的同伴克里斯托瓦尔·德·梅纳上尉发表的关于皮萨罗功绩的第一份报告,于1534年4月在塞维利亚印刷,距阿塔瓦尔帕被处决仅九个月。它成为畅销书,迅速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并使更多西班牙殖民者前来巩固皮萨罗对秘鲁的控制。
阿塔瓦尔帕为何走入陷阱? 事后看来,我们发现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走入皮萨罗明显的陷阱令人震惊。俘获他的西班牙人对自己的成功同样感到惊讶。识字能力(literacy)的后果在最终解释中占据显著位置。
直接的解释是,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意图了解甚少。他从口头获得的那点信息,主要来自一名特使,这名特使在皮萨罗的部队从海岸向内陆进军途中拜访了两天。那名特使看到西班牙人最混乱的状态,告诉阿塔瓦尔帕他们不是战士,如果给他200名印第安人,他就能把他们全部绑起来。可以理解的是,阿塔瓦尔帕从未想到西班牙人是强大的,而且会无缘无故地攻击他。
在新大陆,书写能力仅限于现代墨西哥及其北部邻近地区的少数精英阶层,这些地区远在印加帝国以北。尽管西班牙人早在1510年就开始征服距离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仅600英里的巴拿马,但似乎直到1527年皮萨罗首次登陆秘鲁海岸时,印加人才知道西班牙人的存在。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征服中美洲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印第安社会的事情一无所知。
今天的我们对阿塔瓦尔帕导致自己被俘的行为感到惊讶,而他被俘后的行为同样令人惊讶。他天真地提出了著名的赎金,以为付了赎金后,西班牙人就会释放他并离开。他无法理解皮萨罗的部队是一支旨在永久征服的力量的先锋,而不是一次孤立的突袭。
阿塔瓦尔帕并非唯一犯下这些致命误判的人。即使在阿塔瓦尔帕被俘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还欺骗了阿塔瓦尔帕的主要将领查尔库奇马,使这位指挥着一支庞大军队的将领向西班牙人投降。查尔库奇马的误判标志着印加抵抗崩溃的转折点,这一时刻几乎与阿塔瓦尔帕本人被俘一样重要。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犯下的错误甚至更加严重,他把科尔特斯当作归来的神明,允许他和他的小部队进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结果是科尔特斯俘虏了蒙特祖马,然后继续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和阿兹特克帝国。
在世俗层面上,阿塔瓦尔帕、查尔库奇马、蒙特祖马以及无数其他被欧洲人欺骗的美洲原住民领袖的误判,是由于新大陆没有活着的居民去过旧大陆,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掌握关于西班牙人的具体信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结论:阿塔瓦尔帕”应该”更加警觉,如果他的社会经历过更广泛的人类行为范式的话。皮萨罗到达卡哈马卡时,除了他在1527年和1531年审问遇到的印加臣民所获得的信息外,对印加人也一无所知。然而,虽然皮萨罗本人碰巧是文盲,但他属于一个有文字传统的文化。从书籍中,西班牙人了解到许多远离欧洲的当代文明,以及数千年的欧洲历史。皮萨罗明确地以科尔特斯成功的策略为模板来伏击阿塔瓦尔帕。
简而言之,文字使西班牙人成为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的继承者。相比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仅对西班牙人本身毫无概念,也没有任何其他海外入侵者的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面临过类似的威胁。这种经验上的鸿沟促使皮萨罗设下陷阱,而阿塔瓦尔帕则走进了陷阱。
因此,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说明了导致欧洲人殖民新大陆而非美洲原住民殖民欧洲的一系列直接因素(proximate factors)。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基于枪支、钢制武器和马匹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流行的传染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的集权政治组织;以及文字。本书的标题将作为这些直接因素的简称,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早在有人开始制造枪支和钢铁之前,这些相同因素中的其他因素就已经导致了一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所有这些直接优势更多地掌握在欧洲而非新大陆手中?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支和钢剑,骑在像马一样可怕的动物上,携带欧洲人缺乏抵抗力的疾病,发展远洋船只和先进的政治组织,并能够借鉴数千年书面历史的经验?这些不再是本章一直在讨论的直接因果关系(proximate causation)的问题,而是本书接下来两部分将要探讨的终极因果关系(ultimate causation)的问题。
作为一名青少年,我在1956年的夏天在蒙大拿州度过,为一位名叫弗雷德·赫希的老农民工作。弗雷德出生在瑞士,19世纪90年代作为青少年来到蒙大拿州西南部,并着手开发该地区最早的农场之一。在他到达时,大部分原始的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s)美洲原住民仍然生活在那里。
我的农场工友大多是粗鲁的白人,他们的日常言语充斥着咒骂,平日工作只是为了在周末把一周的工资挥霍在当地的酒馆里。然而,在这些农场工人中,有一位名叫列维的黑脚印第安部落成员,他的行为与那些粗鲁的矿工截然不同——礼貌、温和、负责任、清醒、谈吐得体。他是我长时间相处的第一位印第安人,我开始钦佩他。
因此,当某个星期天早上,列维也在星期六晚上狂饮后醉醺醺地咒骂着跌跌撞撞地走进来时,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在他的咒骂中,有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中格外突出:“该死的弗雷德·赫希,该死的把你从瑞士带来的那艘船!”这句话深刻地让我认识到印第安人对我和其他白人学童所学的美国西部英雄征服史的看法。弗雷德·赫希的家人为他感到骄傲,认为他是一位在艰苦条件下取得成功的拓荒农民。但列维的部落曾是猎人和著名战士的部落,他们的土地被移民而来的白人农民掠夺了。农民是如何战胜这些著名的战士的呢?
在现代人类的祖先与现存大猿类的祖先分离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700万年前,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完全依靠狩猎野生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来养活自己,就像19世纪的黑脚族人一样。直到最近11000年,一些民族才转向所谓的粮食生产:即驯化野生动物和植物,食用由此产生的牲畜和农作物。今天,地球上大多数人消费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或者是别人为他们生产的。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在未来十年内,仅存的几个狩猎采集者群体将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解体或消亡,从而结束我们数百万年来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坚持。
不同的民族在史前不同时期获得了粮食生产。有些民族,如澳大利亚土著,从未获得过粮食生产。在那些获得粮食生产的民族中,有些(例如古代中国人)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另一些(包括古埃及人)则是从邻居那里获得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粮食生产间接地成为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不同大陆的民族是否成为农民和牧民,或者何时成为农民和牧民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我们用接下来的六章来理解粮食生产的地理差异是如何产生之前,本章将追溯粮食生产导致所有优势的主要联系,这些优势使皮萨罗能够俘获阿塔瓦尔帕,弗雷德·赫希的人民能够剥夺列维的人民(图4.1)。
第一个联系是最直接的:更多可消费的卡路里意味着更多的人。在野生植物和动物物种中,只有一小部分对人类来说是可食用的或值得狩猎或采集的。大多数物种对我们来说作为食物是无用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一个或多个:它们难以消化(如树皮),有毒(帝王蝶和鹅膏菌),营养价值低(水母),准备起来繁琐(非常小的坚果),难以采集(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或者狩猎起来危险(犀牛)。陆地上的大部分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质)是以木材和树叶的形式存在的,其中大部分我们无法消化。
通过选择和种植那些少数我们可以食用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使它们占一英亩土地上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每英亩获得的可食用卡路里要多得多。结果,一英亩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牧民和农民—通常是狩猎采集者的10到100倍。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是粮食生产部落相对于狩猎采集部落获得的众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
在拥有家畜的人类社会中,牲畜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制品和肥料,以及拉犁。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家畜成为社会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取代了野味。例如,今天美国人往往从牛、猪、羊和鸡那里获得大部分动物蛋白,而鹿肉等野味只是罕见的美味。此外,一些大型家畜还提供奶制品,如黄油、奶酪和酸奶。被挤奶的哺乳动物包括牛、羊、山羊、马、驯鹿、水牛、牦牛以及阿拉伯骆驼和双峰骆驼。因此,这些哺乳动物在其一生中产生的卡路里是仅被屠宰和作为肉食用时的数倍。
大型家畜还以两种方式与家养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产量。首先,正如任何现代园丁或农民仍然通过经验知道的那样,施用粪肥作为肥料可以大大增加作物产量。即使在现代化学工厂生产的合成肥料可用的情况下,今天大多数社会中农作物肥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动物粪便—尤其是牛粪,但也有牦牛和羊粪。在传统社会中,粪便作为火的燃料来源也很有价值。
此外,最大的家畜与家养植物相互作用,通过拉犁来增加粮食产量,从而使人们能够耕种以前在经济上不可行的土地。这些拉犁动物是牛、马、水牛、巴厘牛和牦牛/牛的杂交种。以下是它们价值的一个例子:欧洲中部的第一批史前农民,即略早于公元前5000年兴起的所谓线纹陶文化(Linearbandkeramik culture),最初只能耕种那些轻到可以用手持挖掘棒耕作的土壤。直到一千多年后,随着牛拉犁的引入,这些农民才能够将耕作扩展到更广泛的重质土壤和坚韧草皮。同样,北美大平原的美洲原住民农民在河谷种植作物,但在广阔高地上耕种坚韧的草皮必须等到19世纪的欧洲人及其畜力犁的到来。
所有这些都是植物和动物驯化通过比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产出更多食物而直接导致人口密度增加的方式。一个更间接的方式涉及粮食生产所强制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后果。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为了寻找野生食物而频繁迁移,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由此产生的固定居所通过缩短生育间隔来促进更高的人口密度。一个迁移营地的狩猎-采集母亲只能携带一个孩子,以及她为数不多的财物。她无法承担生育下一个孩子,直到前一个学步儿童能够走得足够快以跟上部落而不拖累它。在实践中,游牧的狩猎-采集者通过哺乳期闭经(lactational amenorrhea)、性节制、杀婴和堕胎将孩子的出生间隔控制在大约四年。相比之下,定居的人们不受携带幼儿长途跋涉问题的限制,可以生育和抚养他们能够养活的尽可能多的孩子。许多农业民族的生育间隔约为两年,是狩猎-采集者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更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每英亩养活更多人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达到比狩猎-采集者高得多的人口密度。
定居生活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允许人们储存剩余食物,因为如果不留在附近看守储存的食物,储存就毫无意义。虽然一些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可能偶尔获得比他们几天内能消费的更多的食物,但这样的意外收获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因为他们无法保护它。但储存的食物对于养活非粮食生产专业人员至关重要,当然也是支撑整个城镇的这些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游牧狩猎-采集社会很少或没有这样的全职专业人员,他们首次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这类专业人员的两种类型是国王和官僚。狩猎-采集社会往往相对平等,缺乏全职官僚和世袭酋长,并且在部落或氏族层面上拥有小规模的政治组织。这是因为所有健全的狩猎-采集者都必须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获取食物。相比之下,一旦食物可以储存,政治精英就可以控制他人生产的食物,主张征税权,摆脱养活自己的需要,并全职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常以酋邦(chiefdoms)形式组织,而王国仅限于大型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政治单位比平等的狩猎者群体更能够发动持续的征服战争。一些处于特别富饶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如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尔海岸,也发展出定居社会、食物储存和初生的酋邦,但他们没有在通往王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通过征税积累的储存食物剩余可以支持除国王和官僚之外的其他全职专业人员。与征服战争最直接相关的是,它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大英帝国最终击败新西兰装备精良的原住民毛利人口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无法维持一支始终在战场上的军队,最终被18,000名全职英国军队拖垮。储存的食物还可以养活祭司,他们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工匠如金属工人,他们开发剑、枪和其他技术;以及抄写员,他们保存的信息远比能够准确记忆的要多得多。
到目前为止,我强调了作物和牲畜作为食物的直接和间接价值。然而,它们还有其他用途,例如为我们保暖和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作物和牲畜产生用于制作衣服、毯子、网和绳索的天然纤维。大多数主要的植物驯化中心不仅培育出粮食作物,还培育出纤维作物——尤其是棉花、亚麻(亚麻布的来源)和大麻。几种家养动物产出动物纤维——特别是绵羊、山羊、美洲驼和羊驼的羊毛,以及蚕的丝。在冶金发展之前,家养动物的骨骼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制品的重要原材料。牛皮被用来制作皮革。美洲许多地区最早栽培的植物之一是为非食品目的而种植的:葫芦,用作容器。
大型家畜进一步革新了人类社会,在19世纪铁路发展之前,它们成为我们主要的陆地运输方式。在动物驯化之前,陆地运输货物和人员的唯一方式是依靠人力背负。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一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型货物可以大量、快速地长距离陆地运输,人员运输也是如此。被骑乘的家畜包括马、驴、牦牛、驯鹿以及阿拉伯骆驼和双峰驼。这五个物种以及美洲驼都被用来驮运货物。牛和马被套上马车,而驯鹿和狗在北极地区拉雪橇。马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长途运输的主要工具。三种家养骆驼(阿拉伯骆驼、双峰驼和美洲驼)分别在北非和阿拉伯、中亚以及安第斯地区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植物和动物驯化对征服战争最直接的贡献来自欧亚大陆的马,它们的军事作用使其成为该大陆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正如我在第3章中提到的,马使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仅率领小股冒险者就推翻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更早的时候(约公元前4000年),当马还只能裸背骑乘时,它们可能是印欧语系使用者从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关键军事要素。这些语言最终取代了除巴斯克语外的所有早期西欧语言。后来当马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发明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始革新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的战争。例如,公元前1674年,马甚至使一个外来民族希克索斯人征服了当时没有马的埃及,并暂时确立自己为法老。
更晚些时候,在马鞍和马镫发明之后,马使匈奴人和后续几波来自亚洲草原的其他民族能够威胁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最终在公元13和14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亚洲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入卡车和坦克,马才最终被取代作为主要突击车辆和战争中的快速运输工具。阿拉伯骆驼和双峰驼在其地理范围内发挥着类似的军事作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拥有家养马(或骆驼)或改进使用它们的方法的民族,比没有它们的民族享有巨大的军事优势。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拥有家畜的人类社会中进化出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感这样的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门病菌出现,是由感染动物的非常相似的祖先病菌突变而来(第11章)。驯化动物的人类最先成为这些新进化病菌的受害者,但这些人类随后对新疾病进化出了相当大的抵抗力。当这些部分免疫的人群与之前未接触过这些病菌的其他人接触时,就会导致流行病,其中高达99%的先前未接触人群被杀死。因此,最终来自家畜的病菌在欧洲人征服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和太平洋岛民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简而言之,植物和动物驯化意味着更多的食物,因此人口密度大大增加。由此产生的粮食盈余,以及(在某些地区)基于动物的运输这些盈余的方式,是发展定居的、政治集中化的、社会分层的、经济复杂的、技术创新的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家养植物和动物的可获得性最终解释了为什么帝国、文字和钢铁武器最早在欧亚大陆发展,而在其他大陆则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马和骆驼的军事用途,以及动物源性病菌的杀伤力,完成了我们将要探索的粮食生产与征服之间的主要联系清单。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由富有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不平等冲突组成:拥有农业力量的民族与没有农业力量的民族之间,或者在不同时期获得农业力量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足为奇的是,由于生态原因,粮食生产从未在全球大片地区出现,这些原因至今仍使其在那里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例如,在北美的北极地区,史前时期既没有农业也没有畜牧业发展,而在欧亚大陆北极地区出现的唯一粮食生产要素是驯鹿养殖。粮食生产也不可能在远离灌溉水源的沙漠中自发产生,比如澳大利亚中部和美国西部的部分地区。
相反,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粮食生产直到现代才出现在一些生态上非常适宜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如今却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农业和畜牧业中心。这些令人困惑的地区中最突出的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太平洋沿岸州、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南非开普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当欧洲殖民者到达时,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如果我们在公元前4000年审视世界,也就是在粮食生产最早起源地兴起数千年之后,我们也会对其他几个现代粮仓感到惊讶,因为它们当时仍然没有粮食生产——包括美国其余所有地区、英格兰和法国大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以及赤道以南非洲的所有地区。当我们追溯粮食生产的起源时,最早的遗址提供了另一个惊喜。这些地区远非现代粮仓,它们包括今天被认为有些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部分地区,以及非洲萨赫勒地带。为什么粮食生产首先在这些看似相当边缘的土地上发展起来,而只是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出现?
粮食生产产生方式的地理差异也令人困惑。在少数地方,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当地人驯化当地植物和动物的结果。在大多数其他地方,它是以作物和牲畜的形式被引进的,而这些作物和牲畜是在别处驯化的。既然这些非独立起源地区在驯化物种到达后就适合史前粮食生产,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们没有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驯化当地植物和动物而成为农民和牧民?
在那些粮食生产确实独立兴起的地区中,为什么它出现的时间差异如此之大——例如,东亚比美国东部早数千年,而在澳大利亚东部从未出现?在史前时代被引进粮食生产的地区中,为什么到达日期也差异如此之大——例如,欧洲西南部比美国西南部早数千年?同样在这些引进粮食生产的地区中,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如美国西南部)当地的狩猎采集者自己从邻居那里采用作物和牲畜并作为农民生存下来,而在其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赤道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的引进却伴随着该地区原始狩猎采集者被入侵的粮食生产者灾难性地取代?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决定哪些民族成为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哪些成为强势群体的发展过程。
在我们希望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识别粮食生产起源的地区,它何时在那里兴起,以及某种作物或动物首次在何处何时被驯化。最明确的证据来自考古遗址中植物和动物遗骸的鉴定。大多数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在形态上与它们的野生祖先不同:例如,家养牛和羊的体型较小,家养鸡和苹果的体型较大,家养豌豆的种皮更薄更光滑,以及家养山羊的角呈螺旋扭曲状而非弯刀状。因此,在有年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驯化植物和动物的遗骸可以被识别出来,并为该地该时的粮食生产提供有力证据,而在遗址中只发现野生物种的遗骸则无法提供粮食生产的证据,这与狩猎采集相符。自然地,粮食生产者,特别是早期的粮食生产者,继续采集一些野生植物并狩猎野生动物,因此他们遗址中的食物遗骸通常既包括野生物种也包括驯化物种。
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中含碳物质进行放射性碳测年来确定粮食生产的年代。这种方法基于放射性碳14的缓慢衰变,碳14是碳的一个非常次要的组成部分,而碳是生命中无处不在的组成元素,它会衰变成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碳14在大气中不断被宇宙射线产生。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其碳14与主要同位素碳12的比例是已知且大致恒定的(大约为百万分之一)。植物碳继续形成食草动物的身体,而食草动物又形成食肉动物的身体。然而,一旦植物或动物死亡,其碳14含量每5700年就有一半衰变成碳12,直到大约40000年后碳14含量变得非常低,难以测量或区分是否受到含有碳14的少量现代物质的污染。因此,考古遗址材料的年代可以从材料的碳14/碳12比率计算出来。
放射性碳测年受到许多技术问题的困扰,其中有两个值得在这里提及。一个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放射性碳测年需要相对大量的碳(几克),远远超过小种子或骨骼中的碳含量。因此,科学家们常常不得不求助于测定在同一遗址附近发现并被认为与食物遗骸”相关”的材料的年代——也就是说,被认为是由留下食物的人同时沉积的。“相关”材料的典型选择是火堆中的木炭。
但考古遗址并不总是材料整齐密封的时间胶囊,所有材料都在同一天沉积。不同时期沉积的材料可能会混在一起,因为蠕虫、啮齿动物和其他因素会翻动地面。因此,火的木炭残留物可能最终会靠近数千年前或数千年后死亡并被食用的植物或动物遗骸。如今,考古学家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称为加速器质谱法(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的新技术来规避这个问题,该技术允许对微小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年,从而可以直接测定单个小种子、小骨头或其他食物残留物的年代。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直接新方法的最新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这些方法也有自己的问题)与基于间接旧方法的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由此产生的未解决争议中,对于本书而言,也许最重要的是关于美洲粮食生产起源日期的争议: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间接方法得出的日期早至公元前7000年,但最近的直接测年得出的日期不早于公元前3500年。
放射性碳测年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气中的碳14/碳12比率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恒定的,而是随时间略有波动,因此基于恒定比率假设计算的放射性碳年代会受到小的系统误差的影响。原则上,每个过去日期的这种误差大小可以借助形成年轮的长寿树木来确定,因为可以计数年轮以获得过去每个年轮的绝对日历日期,然后可以分析以这种方式测定年代的木材碳样本的碳14/碳12比率。通过这种方式,测量的放射性碳年代可以被”校准”,以考虑大气碳比率的波动。这种校正的效果是,对于表观(即未校准)日期在公元前约1000年至6000年之间的材料,真实(校准)日期要早几个世纪到一千年。最近,已经开始用基于另一种放射性衰变过程的替代方法对稍早的样本进行校准,得出的结论是表观日期约为公元前9000年的样本实际上可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经常通过用大写字母表示校准日期、用小写字母表示未校准日期来区分它们(例如,分别为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然而,考古文献在这方面可能会令人困惑,因为许多书籍和论文报告未校准日期为公元前,并且没有提及它们实际上是未校准的。我在本书中报告的过去15000年内事件的日期是校准日期。这解释了读者可能注意到的本书日期与一些关于早期粮食生产的标准参考书中引用的日期之间的一些差异。
一旦识别并测定了古代驯化植物或动物遗骸的年代,如何判断该植物或动物是否实际上是在该遗址附近驯化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驯化然后传播到该遗址的?一种方法是检查该作物或动物野生祖先地理分布的地图,并推断驯化一定发生在野生祖先出现的地区。例如,从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向东到印度的传统农民广泛种植鹰嘴豆,后者占当今世界鹰嘴豆产量的80%。因此,人们可能会被误导认为鹰嘴豆是在印度驯化的。但事实证明,祖先野生鹰嘴豆仅出现在土耳其东南部。鹰嘴豆实际上是在那里驯化的解释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可能驯化的鹰嘴豆最早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和附近的叙利亚北部,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直到5000多年后,鹰嘴豆的考古证据才出现在印度次大陆。
识别作物或动物驯化地点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地图上标出驯化形式在每个地点首次出现的日期。它最早出现的地点可能是其最初驯化的地点——特别是如果野生祖先也出现在那里,并且如果在其他地点首次出现的日期随着与推定的最初驯化地点距离的增加而逐渐推迟,这表明传播到了那些其他地点。例如,已知最早的栽培二粒小麦来自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新月沃土。此后不久,该作物逐渐向西出现,公元前6500年左右到达希腊,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达德国。这些日期表明二粒小麦在新月沃土驯化,祖先野生二粒小麦仅限于从以色列到伊朗西部和土耳其的地区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一结论。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会出现复杂情况,即同一种植物或动物在几个不同的地点被独立驯化。这类情况通常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同一作物或家畜标本之间的形态学、遗传学或染色体差异来检测。例如,印度的瘤牛品种具有西欧亚大陆牛品种所缺少的驼峰,遗传分析表明,现代印度牛和西欧亚大陆牛品种的祖先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分化,远早于任何地方开始驯化动物的时间。也就是说,牛在印度和西欧亚大陆是独立驯化的,时间在最近一万年内,起源于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分化的野生印度牛和西欧亚大陆牛亚种。
粮食生产是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何处、何时以及如何发展起来的?
一个极端是粮食生产完全独立产生的地区,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任何作物或动物到达之前,就驯化了许多本地作物(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动物)。目前只有五个地区的证据详细而令人信服:西南亚,也称为近东或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中国;中美洲(Mesoamerica)(该术语适用于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以及中美洲的邻近地区);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可能还包括邻近的亚马逊盆地;以及美国东部(图5.1)。这些中心中的部分或全部实际上可能包含几个邻近的中心,粮食生产在这些中心或多或少地独立产生,例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
除了这五个粮食生产确实独立产生的地区外,还有四个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Sahel)、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也是候选地区。然而,每种情况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虽然本地野生植物无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萨赫勒地带被驯化,但畜牧业可能先于农业出现在那里,而且目前还不确定这些是独立驯化的萨赫勒牛,还是新月沃地起源的家牛,其到达触发了当地植物的驯化。同样不确定的是,这些萨赫勒作物的到达是否触发了热带西非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以及西南亚作物的到达是否触发了埃塞俄比亚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至于新几内亚,那里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早期农业的证据,远早于任何邻近地区的粮食生产,但所种植的作物尚未被明确识别。
表5.1总结了这些和其他地方驯化地区的一些最著名的作物和动物,以及已知最早的驯化日期。在这九个粮食生产独立演化的候选地区中,西南亚拥有植物驯化(约公元前8500年)和动物驯化(约公元前8000年)的最早确定日期;它也拥有迄今为止最多的早期粮食生产的精确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中国的日期几乎同样早,而美国东部的日期明显晚了约6000年。对于其他六个候选地区,最早的确定日期无法与西南亚相比,但这六个其他地区的早期遗址中,能够可靠定年的太少,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真的落后于西南亚,以及(如果是的话)落后多少。
下一组地区包括那些确实驯化了至少几种本地植物或动物的地区,但粮食生产主要依赖于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和动物。这些引进的驯化物种可以被认为是”奠基”作物和动物,因为它们奠定了当地粮食生产的基础。奠基驯化物种的到达使当地人能够定居下来,从而增加了本地作物从野生植物演化的可能性,这些野生植物被采集、带回家、意外种植,后来被有意种植。
表5.1 各地区驯化物种示例
| 地区 | 驯化植物 | 驯化动物 | 最早证实的驯化日期 |
|---|---|---|---|
| 独立驯化的起源地 | |||
| 1. 西南亚 | 小麦、豌豆、橄榄 | 绵羊、山羊 | 公元前8500年 |
| 2. 中国 | 水稻、小米 | 猪、蚕 | 公元前7500年前 |
| 3. 中美洲 | 玉米、豆类、南瓜 | 火鸡 | 公元前3500年前 |
| 地区 | 主要驯化作物 | 主要驯化动物 | 起源时间 |
|---|---|---|---|
| 独立起源地区 | |||
| 4. 安第斯山脉和亚马逊地区 | 马铃薯、木薯 | 美洲驼、豚鼠 | 公元前3500年之前 |
| 5. 美国东部 | 向日葵、藜科植物 | 无 | 公元前2500年 |
| ? 6. 萨赫勒地区 | 高粱、非洲稻 | 珍珠鸡 | 公元前5000年之前 |
| ? 7. 热带西非 | 非洲山药、油棕 | 无 | 公元前3000年之前 |
| ? 8. 埃塞俄比亚 | 咖啡、画眉草 | 无 | ? |
| ? 9. 新几内亚 | 甘蔗、香蕉 | 无 | 公元前7000年? |
| 在外来基础作物到达后的本地驯化 | |||
| 10. 西欧 | 罂粟、燕麦 | 无 | 公元前6000-3500年 |
| 11. 印度河流域 | 芝麻、茄子 | 瘤牛 | 公元前7000年 |
| 12. 埃及 | 无花果、油莎草 | 驴、猫 | 公元前6000年 |
在三到四个这样的地区,到达的基础作物包来自西南亚。其中之一是西欧和中欧,那里的粮食生产始于公元前6000年至3500年间西南亚作物和动物的到来,但至少有一种植物(罂粟,可能还有燕麦和其他一些植物)随后在当地被驯化。野生罂粟仅限于地中海西部的沿海地区。在东欧和西南亚最早的农业社区遗址中没有发现罂粟种子;它们首次出现在西欧早期农业遗址中。相比之下,大多数西南亚作物和动物的野生祖先在西欧并不存在。因此,很明显粮食生产并非在西欧独立演化。相反,它是由西南亚驯化物种的到达所引发的。由此产生的西欧农业社会驯化了罂粟,随后罂粟作为作物向东传播。
另一个本地驯化似乎是在西南亚基础作物到达之后发生的地区是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公元前七千年那里最早的农业社区使用小麦、大麦和其他此前在肥沃新月地带驯化的作物,这些作物显然通过伊朗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只是在后来,源自印度次大陆本土物种的驯化物种,如瘤牛和芝麻,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社区中。在埃及也是如此,粮食生产始于公元前六千年西南亚作物的到达。埃及人随后驯化了无花果树和一种叫做油莎草的当地蔬菜。
同样的模式可能也适用于埃塞俄比亚,那里的小麦、大麦和其他西南亚作物已经种植了很长时间。埃塞俄比亚人还驯化了许多当地可获得的野生物种,以获得大多数仍局限于埃塞俄比亚的作物,但其中一种(咖啡豆)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埃塞俄比亚人是在西南亚作物包到达之前还是之后才开始种植这些本地植物的。
在这些以及其他依赖外来基础作物到达的粮食生产地区,是当地的狩猎采集者自己从邻近的农业民族那里采用了这些基础作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农民吗?还是基础作物包是由入侵的农民带来的,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繁殖上超过当地猎人,并杀死、取代或在数量上超过他们?
在埃及,前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当地狩猎采集者只是将西南亚的驯化物种以及农业和畜牧技术添加到他们自己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饮食中,然后逐渐淘汰野生食物。也就是说,在埃及启动粮食生产的是外来作物和动物,而不是外来民族。欧洲大西洋沿岸也可能是如此,那里的当地狩猎采集者显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采用了西南亚的绵羊和谷物。在南非的开普地区,当地的科伊狩猎采集者通过从非洲北部(最终来自西南亚)获得绵羊和奶牛而成为牧民(但不是农民)。同样,美国西南部的美洲原住民狩猎采集者通过获得墨西哥作物而逐渐成为农民。在这四个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本地植物或动物物种的驯化,但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人口的替代。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肯定是随着外来人口以及外来作物和动物的突然到来而开始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是因为这些到来发生在现代,涉及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他们在无数书籍中描述了发生的事情。这些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北美太平洋西北地区、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这些地区仍然被狩猎采集者占据——前三种情况下是美洲原住民,后两种情况下是澳大利亚土著或西伯利亚原住民。这些狩猎采集者被到达的欧洲农民和牧民杀死、感染、驱逐或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这些欧洲人带来了自己的作物,在到达后没有驯化任何当地野生物种(除了澳大利亚的澳洲坚果)。在南非开普地区,到达的欧洲人不仅发现了科伊桑狩猎采集者,还发现了已经拥有家畜但没有作物的科伊桑牧民。结果再次是依赖于来自其他地方的作物开始农业生产,未能驯化当地物种,以及现代人口的大规模替换。
最后,同样的模式——依赖于来自其他地方的驯化动植物突然开始粮食生产,以及突然的大规模人口替换——似乎在史前时代的许多地区重复发生。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必须在考古记录中寻找这些史前替换的证据,或从语言学证据中推断。最有据可查的案例是那些人口替换毫无疑问的案例,因为新到达的粮食生产者在骨骼上与他们所替换的狩猎采集者明显不同,而且粮食生产者不仅引入了作物和动物,还引入了陶器。后续章节将描述两个最清楚的例子:南岛语族从华南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第17章),以及班图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扩张(第19章)。
东南欧和中欧呈现出类似的图景:粮食生产(依赖于西南亚作物和动物)和陶器制作的突然开始。这种开始也可能涉及新希腊人和新德国人对旧希腊人和旧德国人的替换,就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旧有人群让位于新人群一样。然而,在欧洲,早期狩猎采集者与替换他们的农民之间的骨骼差异不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样明显。因此,欧洲人口替换的证据不那么有力或不那么直接。
从前,地球上所有人都是狩猎采集者。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了粮食生产?既然他们一定有某种理由,为什么他们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肥沃月湾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仅在3000年后才在气候和结构相似的西南欧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而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开普地区相似的地中海栖息地从未本土发展出粮食生产?为什么即使是肥沃月湾的人们也要等到公元前8500年,而不是在公元前18500年或28500年就成为粮食生产者?
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问题起初似乎都很愚蠢,因为作为狩猎采集者的缺点显而易见。科学家们过去常常引用托马斯·霍布斯的一句话来描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为”肮脏、野蛮和短暂”。他们似乎不得不辛苦工作,被每日寻找食物的需求所驱使,经常接近饥饿,缺乏诸如柔软床铺和足够衣物等基本物质舒适,并且早逝。
实际上,只有对于今天富裕的第一世界公民来说,他们自己并不实际从事粮食生产工作,食品生产(由遥远的农业企业完成)才意味着更少的体力劳动、更多的舒适、免于饥饿和更长的预期寿命。大多数农民和牧民,他们构成了世界上实际粮食生产者的绝大多数,并不一定比狩猎采集者过得更好。时间预算研究表明,他们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可能比狩猎采集者更多而不是更少。考古学家已经证明,许多地区的第一批农民比他们所取代的狩猎采集者更矮小、营养更差、患有更严重的疾病,平均死亡年龄也更年轻。如果那些最早的农民能够预见到采用粮食生产的后果,他们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在无法预见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做出了这个选择?
存在许多狩猎采集者看到邻居从事粮食生产的实际案例,但他们仍然拒绝接受其所谓的好处,而是继续保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原住民狩猎采集者与托雷斯海峡群岛(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农民进行了数千年的贸易。加州的美洲原住民狩猎采集者与科罗拉多河谷的美洲原住民农民进行贸易。此外,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人牧民与菲什河以东的班图农民进行贸易,但他们自己继续不从事农业。为什么?
还有一些与农民接触的狩猎采集者最终确实成为了农民,但只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过长的延迟之后。例如,德国北部的沿海民族直到线纹陶文化(Linearbandkeramik)的人们将粮食生产引入南部仅125英里的德国内陆地区1300年后,才采用粮食生产。为什么那些德国沿海居民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又是什么最终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一些关于粮食生产起源的误解,然后重新表述这个问题。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粮食生产的发现,也不是发明,正如我们可能首先假设的那样。通常甚至没有在粮食生产和狩猎采集之间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具体来说,在全球每个地区,第一批采用粮食生产的人显然不可能是在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或有意识地将农业作为目标而努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农业,也无法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相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粮食生产演化为在没有意识到其后果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副产品。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粮食生产确实演化了,为什么它在某些地方演化而在其他地方没有,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以及为什么不是在更早或更晚的某个日期。
另一个误解是游牧狩猎采集者和定居粮食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明显的分界。实际上,尽管我们经常做出这样的对比,但一些富饶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包括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可能的澳大利亚东南部,变得定居但从未成为粮食生产者。其他狩猎采集者,在巴勒斯坦、秘鲁海岸和日本,首先变得定居,然后很久以后才采用粮食生产。15000年前,当世界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最富饶的地区)仍然被狩猎采集者占据时,定居群体在狩猎采集者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今天要高得多,而今天仅存的少数狩猎采集者只在游牧是唯一选择的非生产性地区生存。
相反,也存在流动的粮食生产者群体。新几内亚湖泊平原的一些现代游牧民在丛林中开辟空地,种植香蕉和木瓜,然后离开几个月再次过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回来查看他们的作物,如果发现作物在生长就给花园除草,再次出发去狩猎,几个月后再回来检查,如果他们的花园有产出就定居一段时间来收获和食用。美国西南部的阿帕奇印第安人在夏季定居在较高海拔和北部地区耕作,然后在冬季撤退到南部和较低海拔地区四处寻找野生食物。非洲和亚洲的许多牧民沿着固定的季节性路线转移营地,以利用可预测的牧场季节性变化。因此,从狩猎采集到粮食生产的转变并不总是与从游牧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同时发生。
另一个在现实中变得模糊的所谓二分法是将粮食生产者视为土地的主动管理者,而将狩猎采集者仅视为土地野生产物的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一些狩猎采集者对他们的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例如,新几内亚人从未驯化西米棕榈或山地露兜树,但他们通过清除侵占的竞争性树木、保持西米沼泽中的渠道畅通,以及通过砍伐成熟的西米树来促进新西米芽的生长,从而提高了这些野生可食用植物的产量。澳大利亚土著从未达到种植薯蓣和种子植物的阶段,但他们预见到了农业的几个要素。他们通过焚烧来管理景观,以促进火灾后萌发的可食用种子植物的生长。在采集野生薯蓣时,他们切掉大部分可食用的块茎,但将薯蓣的茎和顶部重新放回地里,以便块茎能够再生。他们挖掘提取块茎的过程疏松并通气了土壤,促进了再生长。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茎和剩余附着的块茎带回家,并以类似的方式将它们放回营地的土壤中,就可以符合农民的定义了。
从狩猎采集者已经实践的那些粮食生产的前身开始,它逐步发展起来。并非所有必要的技术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也并非某一地区最终驯化的所有野生植物和动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在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独立发展粮食生产最快速的情况下,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饮食中几乎没有野生食物的饮食,也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同时采集野生食物和种植栽培食物,随着对农作物依赖的增加,各种类型的采集活动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这种转变之所以是零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生产系统是作为许多关于分配时间和精力的单独决策积累的结果而演变的。觅食的人类,就像觅食的动物一样,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使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初期的农民醒来后问自己:我今天应该花时间锄我的菜园(可预见地在几个月后产出大量蔬菜),采集贝类(可预见地今天产出少量肉),还是狩猎鹿(可能今天产出大量肉,但更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人类和动物觅食者不断地确定优先级并做出努力分配决策,即使只是无意识地。他们首先专注于最喜欢的食物,或者那些产出最高回报的食物。如果这些不可得,他们就转向越来越不喜欢的食物。
许多考虑因素进入这些决策。人们寻找食物是为了满足饥饿和填饱肚子。他们也渴望特定的食物,如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脂肪、盐、甜水果,以及简单地味道好的食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寻求通过以最少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的确定性获得最多回报的觅食方式来最大化他们的卡路里、蛋白质或其他特定食物类别的回报。同时,他们寻求最小化饥饿的风险:适度但可靠的回报比高时间平均回报率但有很大可能饿死的波动生活方式更可取。大约11,000年前第一批菜园的一个建议功能是提供一个可靠的储备粮仓,以防万一野生食物供应失败时作为保险。
相反,男性狩猎者倾向于以声望的考虑来指导自己:例如,他们宁愿每天去猎长颈鹿,每月猎到一头长颈鹿,从而获得伟大猎人的地位,也不愿通过谦卑自己每天可靠地采集坚果而在一个月内带回家两倍于长颈鹿重量的食物。人们也受到看似任意的文化偏好的指导,例如认为鱼是美味佳肴或禁忌。最后,他们的优先级受到他们对不同生活方式附加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养牛人、牧羊人和农民都互相鄙视。同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倾向于鄙视狩猎采集者为原始人,狩猎采集者鄙视农民为无知者,牧民则鄙视两者。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人们关于如何获取食物的单独决策中发挥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每个大陆上的第一批农民不可能有意识地选择农业,因为没有其他附近的农民供他们观察。然而,一旦粮食生产在大陆的某一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者就可以看到结果并做出有意识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狩猎采集者几乎完全采用了邻近的粮食生产系统;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只选择了其中的某些要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完全拒绝粮食生产,并继续保持狩猎采集者的身份。
例如,东南欧部分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迅速采用了西南亚的谷物作物、豆类作物和牲畜,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组合同时引入。这三个要素也在公元前5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迅速传播到中欧。食物生产在东南欧和中欧可能被快速且全面采用,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生产力较低,竞争力较弱。相比之下,食物生产在西南欧(法国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是零散采用的,那里先引入了绵羊,谷物随后才到来。从亚洲大陆引入密集型食物生产在日本也非常缓慢且零散,可能是因为那里基于海产品和本地植物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生产力很高。
正如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可以逐步转变为食物生产生活方式一样,一种食物生产系统也可以逐步转变为另一种。例如,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开始驯化当地植物,但他们与墨西哥印第安人有贸易联系,后者发展出了一种基于玉米、南瓜和豆类三位一体的更高产的作物系统。美国东部印第安人逐步采用了墨西哥作物,其中许多人放弃了许多本地驯化的植物;南瓜是独立驯化的,玉米在公元200年左右从墨西哥传入,但直到公元900年左右仍是次要作物,豆类在一两个世纪后才到来。甚至还发生过食物生产系统被放弃转而采用狩猎采集的情况。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瑞典南部的狩猎采集者采用了基于西南亚作物的农业,但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放弃了农业,恢复狩猎采集达400年,之后才重新开始农业。
所有这些考量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假设采用农业的决定是在真空中做出的,仿佛人们以前没有任何养活自己的手段。相反,我们必须将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视为相互竞争的替代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将某些作物或牲畜添加到狩猎采集中的混合经济也与两种”纯粹”经济竞争,并与食物生产比例更高或更低的混合经济竞争。然而,在过去的10000年里,主要结果是从狩猎采集转向食物生产。因此我们必须问:是什么因素使竞争优势从前者转向后者?
这个问题仍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争论。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原因是,在世界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原因是在食物生产兴起过程中难以理清因果关系。然而,仍可以确定五个主要的促成因素;争议主要围绕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一个因素是野生食物可获得性的下降。随着狩猎采集者依赖的资源(特别是动物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消失,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在过去13000年里变得越来越缺乏回报。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更新世末期北美和南美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物种灭绝了,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些物种也灭绝了,这要么是因为气候变化,要么是因为人类猎人的技能和数量增加。虽然动物灭绝在最终(经过长时间滞后)推动古代美洲原住民、欧亚人和非洲人转向食物生产方面的作用可以争论,但在近代岛屿上有许多无可争辩的案例。只有在第一批波利尼西亚定居者灭绝了恐鸟并大幅减少新西兰的海豹种群,并灭绝或大幅减少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海鸟和陆鸟之后,他们才加强了食物生产。例如,虽然公元500年左右殖民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带来了鸡,但鸡直到野鸟和海豚不再容易作为食物获得时才成为主要食物。同样,肥沃月湾动物驯化兴起的一个建议促成因素是野生瞪羚数量的下降,而瞪羚以前是该地区狩猎采集者的主要肉类来源。
第二个因素是,正如野生猎物的枯竭倾向于使狩猎采集的回报降低一样,可驯化野生植物可获得性的增加使通向植物驯化的步骤更有回报。例如,肥沃月湾更新世末期的气候变化极大地扩展了野生谷物栖息地的面积,可以在短时间内收获大量作物。这些野生谷物收获是肥沃月湾最早作物——谷物小麦和大麦驯化的前身。
另一个使天平从狩猎采集倾斜的因素是食物生产最终将依赖的技术的累积发展——用于收集、加工和储存野生食物的技术。如果准农民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收获、去壳和储存一吨秸秆上的小麦谷粒,他们能拿它做什么用?在公元前11000年之后,必要的方法、工具和设施在肥沃月湾迅速出现,这些是为处理新出现的大量野生谷物而发明的。
这些发明包括:用燧石刀片粘合到木质或骨质手柄上制成的镰刀,用于收割野生谷物;用来从山坡上把谷物带回家的篮子;用于去除谷壳的研钵和杵,或研磨石板;烘烤谷物使其可以储存而不发芽的技术;以及地下储藏坑,其中一些用灰泥抹平以防水。所有这些技术的证据在公元前11,000年后的新月沃地狩猎采集者遗址中大量出现。所有这些技术虽然是为开发野生谷物而发展起来的,但都是将谷物作为作物种植的先决条件。这些累积的发展构成了植物驯化无意识的第一步。
第四个因素是人口密度上升与粮食生产增长之间的双向联系。在世界上所有有充分证据的地方,考古学家都发现了与粮食生产出现相关的人口密度上升的证据。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人口密度的上升迫使人们转向粮食生产,还是粮食生产允许人口密度上升?
原则上,人们预期因果链条会双向运作。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粮食生产往往导致人口密度增加,因为它比狩猎采集每英亩产出更多可食用的卡路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收集和加工野生食物技术的改进,整个更新世晚期人类人口密度无论如何都在逐渐上升。随着人口密度上升,粮食生产变得越来越受青睐,因为它提供了养活所有这些人所需的增加的粮食产出。
也就是说,粮食生产的采用是所谓的自催化过程(autocatalytic process)的例子——一个在正反馈循环中催化自身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越来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渐上升促使人们获取更多食物,通过奖励那些无意识地采取步骤生产食物的人。一旦人们开始生产食物并定居下来,他们就可以缩短生育间隔并生产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食物。粮食生产与人口密度之间的这种双向联系解释了一个悖论:粮食生产虽然增加了每英亩可食用卡路里的数量,但却使粮食生产者的营养状况不如他们所取代的狩猎采集者。这个悖论的产生是因为人口密度的上升速度略高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
综合来看,这四个因素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新月沃地向粮食生产的过渡始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而不是公元前18,500年或28,500年左右。在后两个日期,狩猎采集仍然比初期的粮食生产有利得多,因为野生哺乳动物仍然丰富;野生谷物还不够丰富;人们还没有开发出有效收集、加工和储存谷物所需的发明;而且人口密度还不够高,无法为每英亩提取更多卡路里提供巨大的溢价。
过渡中的最后一个因素在狩猎采集者和粮食生产者之间的地理边界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粮食生产者密度更大的人口使他们能够仅凭人数优势就取代或杀死狩猎采集者,更不用说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其他优势(包括技术、病菌和职业士兵)。在最初只有狩猎采集者的地区,那些采用粮食生产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在繁殖上超过了那些没有采用的群体。
因此,在地球上大多数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狩猎采集者遇到了两种命运之一:要么被邻近的粮食生产者取代,要么只有通过自己采用粮食生产才能生存下来。在他们人数已经很多或地理条件阻碍粮食生产者移民的地方,当地狩猎采集者确实有时间在史前时代采用农业,从而作为农民生存下来。这可能发生在美国西南部、西地中海、欧洲大西洋沿岸以及日本部分地区。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热带东南亚、赤道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可能还有欧洲部分地区,狩猎采集者在史前时代被农民取代,而类似的取代在现代发生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
只有在特别强大的地理或生态障碍使粮食生产者的移民或适合当地的粮食生产技术的传播非常困难的地方,狩猎采集者才能在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坚持到现代。三个突出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的美洲原住民狩猎采集者的坚持,他们被沙漠与亚利桑那州的美洲原住民农民隔开;南非好望角的科伊桑狩猎采集者的坚持,他们处于地中海气候区,不适合附近班图农民的赤道作物;以及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狩猎采集者的坚持,他们被狭窄的海域与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者隔开。那些少数在20世纪仍然是狩猎采集者的民族逃脱了被粮食生产者取代的命运,因为他们被限制在不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特别是沙漠和北极地区。在本十年内,即使是他们也将被文明的吸引力所诱惑,在官僚或传教士的压力下定居下来,或屈服于病菌。
如果你是一位对农场种植食物感到厌倦的徒步旅行者,尝试食用野生食物会很有趣。你知道一些野生植物,如野草莓和野蓝莓,既美味又安全。它们与熟悉的作物足够相似,你可以轻松识别这些野生浆果,尽管它们比我们种植的要小得多。爱冒险的徒步旅行者会谨慎地食用蘑菇,因为知道许多种类可能致命。但即使是狂热的坚果爱好者也不会吃野生杏仁,因为几十颗野生杏仁含有的氰化物(纳粹毒气室使用的毒药)就足以杀死我们。森林中充满了许多其他被认为不可食用的植物。
然而,所有作物都源自野生植物物种。某些野生植物是如何变成作物的?这个问题在许多作物(如杏仁)方面尤其令人困惑,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是致命的或味道很差,而其他作物(如玉米)看起来与它们的野生祖先截然不同。哪个穴居女人或穴居男人曾经想到要”驯化”一种植物,又是如何实现的?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种植一种植物,从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其在基因上从野生祖先发生改变,使其对人类消费者更有用。如今,作物开发是由专业科学家进行的有意识、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他们已经了解数百种现有作物,并着手开发另一种作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种植许多不同的种子或根,选择最好的后代并种植它们的种子,应用遗传学知识开发出能够稳定遗传的优良品种,甚至可能使用最新的基因工程技术来转移特定的有用基因。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整个一个系(果树学系(Pomology))专门研究苹果,另一个系(葡萄栽培与酿酒学系(Viticulture and Enology))专门研究葡萄和葡萄酒。
但植物驯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早期农民肯定没有使用分子遗传技术来获得他们的结果。第一批农民甚至没有任何现有作物作为榜样来激励他们开发新作物。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最终会享受到美味的款待。
那么,早期农民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驯化植物的?例如,他们如何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将有毒的杏仁变成安全的杏仁?除了使其中一些变得更大或毒性更小之外,他们实际上对野生植物做了哪些改变?即使对于有价值的作物,驯化时间也大不相同:例如,豌豆在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橄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被驯化,草莓直到中世纪才被驯化,山核桃直到1846年才被驯化。许多有价值的野生植物产生数百万人珍视的食物,例如世界许多地方寻求的可食用橡子的橡树,即使在今天仍未被驯化。是什么使一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或更值得驯化?为什么橄榄树屈服于石器时代的农民,而橡树继续击败我们最聪明的农学家?
让我们从植物的角度来看驯化。就植物而言,我们只是成千上万种无意识”驯化”植物的动物物种之一。
像所有动物物种(包括人类)一样,植物必须将它们的后代传播到它们可以茁壮成长并传递父母基因的地区。幼年动物通过行走或飞行分散,但植物没有这种选择,所以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搭便车。虽然一些植物物种的种子适合被风携带或在水上漂浮,但许多其他植物通过将种子包裹在美味的果实中并通过颜色或气味宣传果实的成熟度来欺骗动物携带它们的种子。饥饿的动物摘下并吞下果实,走开或飞走,然后在远离母树的地方吐出或排出种子。种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携带数千英里。
得知植物种子可以抵抗你肠道的消化并仍然从你的粪便中发芽,这可能会让人惊讶。但任何不太拘谨的冒险读者都可以进行测试并自己证明。许多野生植物物种的种子实际上必须通过动物的肠道才能发芽。例如,一种非洲甜瓜物种非常适应被一种叫做土豚的类似鬣狗的动物吃掉,以至于该物种的大多数甜瓜生长在土豚的厕所地点。
作为想要搭便车的植物如何吸引动物的例子,考虑野草莓。当草莓种子还很年轻,还没有准备好被种植时,周围的果实是绿色的、酸的和硬的。当种子最终成熟时,浆果变成红色、甜的和柔软的。浆果颜色的变化充当吸引像画眉这样的鸟类摘下浆果并飞走的信号,最终吐出或排出种子。
自然,草莓植物并没有在种子准备好传播时(并且只有在那时)有意识地吸引鸟类。画眉也没有打算驯化草莓。相反,草莓植物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年轻草莓越绿越酸,在种子准备好之前吃浆果破坏种子的鸟类就越少;最终的草莓越甜越红,传播其成熟种子的鸟类就越多。
无数其他植物的果实也适应了被特定动物物种食用和传播。正如草莓适应了鸟类,橡子适应了松鼠,芒果适应了蝙蝠,某些莎草适应了蚂蚁。这符合我们对植物驯化定义的一部分,即通过基因修饰祖先植物使其对消费者更有用。但没有人会认真地将这一进化过程描述为驯化,因为鸟类、蝙蝠和其他动物消费者并不满足定义的另一部分:它们不会有意识地种植植物。同样,作物从野生植物进化的早期无意识阶段,包括植物以吸引人类食用和传播其果实的方式进化,但人类尚未有意识地种植它们。人类的厕所,就像土豚的厕所一样,可能是第一批无意识作物育种者的试验场。
厕所只是我们无意中播种所食用野生植物种子的众多地方之一。当我们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并带回家时,一些种子会在途中或家中洒落。一些水果在腐烂时仍含有完好的种子,未经食用就被扔进垃圾堆。作为我们实际放入口中的果实部分,草莓种子很小,不可避免地被吞咽和排泄,但其他种子大到足以被吐出来。因此,我们的痰盂和垃圾堆与厕所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农业研究实验室。
无论种子最终落在哪个这样的”实验室”,它们往往只来自可食用植物的某些个体——即那些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更喜欢食用的植物。从你采摘浆果的经历中,你知道你会挑选特定的浆果或浆果灌木。最终,当第一批农民开始有意播种时,他们必然会播种从他们选择采集的植物中获得的种子,尽管他们不理解大浆果的种子可能会长成产出更多大浆果的灌木这一遗传原理。
所以,当你在炎热潮湿的一天,在蚊子中涉入荆棘丛时,你不会为任何草莓灌木都这样做。即使是无意识地,你也会决定哪个灌木看起来最有希望,以及是否值得。你的无意识标准是什么?
当然,一个标准是大小。你更喜欢大浆果,因为为一些可怜的小浆果而被晒伤和被蚊子叮咬是不值得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作物植物的果实比它们的野生祖先大得多。我们特别熟悉超市的草莓和蓝莓与野生的相比是巨大的;这些差异仅在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
其他植物的这种大小差异可以追溯到农业的起源,当时栽培的豌豆通过人类选择进化到比野生豌豆重10倍。小野生豌豆在农业开始之前已被狩猎采集者收集了数千年,就像我们今天收集小野生蓝莓一样,然后对最吸引人的最大野生豌豆进行优先收获和种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自动地促进了一代又一代豌豆平均大小的增加。同样,超市苹果通常直径约三英寸,野生苹果只有一英寸。最古老的玉米棒仅略多于半英寸长,但公元15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农民已经培育出六英寸长的玉米棒,一些现代玉米棒长达一英尺半。
我们种植的种子与许多野生祖先之间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苦味。许多野生种子进化出苦味、难吃或实际有毒,以阻止动物食用它们。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的作用是相反的。果实美味的植物让动物传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内的种子本身必须难吃。否则,动物也会嚼碎种子,它就无法发芽。
杏仁提供了苦味种子及其在驯化下变化的一个显著例子。大多数野生杏仁种子含有一种名为苦杏仁苷(amygdalin)的强烈苦味化学物质,它(如前所述)分解后产生氰化物毒素。一份野生杏仁小吃可以杀死愚蠢到忽视苦味警告的人。既然无意识驯化的第一阶段涉及收集种子来食用,那么野生杏仁的驯化究竟是如何达到第一阶段的呢?
解释是,偶尔个别杏仁树有一个单基因突变,阻止它们合成苦味的苦杏仁苷。这些树在野外会灭绝而不留下任何后代,因为鸟类会发现并吃掉它们所有的种子。但早期农民好奇或饥饿的孩子,在他们周围啃食野生植物时,最终会品尝并注意到那些无苦味的杏仁树。(同样,今天的欧洲农民仍然能识别和欣赏偶尔出现的橡子甜而不苦的橡树。)这些无苦味的杏仁种子是古代农民唯一会种植的,起初是无意中在他们的垃圾堆中,后来有意地在他们的果园中。
早在公元前8000年,野生杏仁就已经出现在希腊的考古遗址中。到公元前3000年,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开始驯化杏仁。当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于公元前1325年左右去世时,杏仁是放置在他著名陵墓中用来滋养他来世的食物之一。利马豆、西瓜、土豆、茄子和卷心菜等许多其他常见作物的野生祖先都是苦涩或有毒的,偶尔会有甜味个体在古代徒步旅行者的厕所周围发芽。
虽然大小和美味是人类狩猎采集者选择野生植物最明显的标准,但其他标准还包括多肉或无籽果实、富含油脂的种子和长纤维。野生南瓜和南瓜的种子周围几乎没有果肉,但早期农民的偏好选择了果肉远多于种子的南瓜。栽培香蕉很早就被选育为全是果肉没有种子,从而启发现代农业科学家也开发出无籽橙子、葡萄和西瓜。无籽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选择如何完全逆转野生果实的原始进化功能——在自然界中,果实是用来传播种子的载体。
在古代,许多植物同样因其富含油脂的果实或种子而被选择。地中海世界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是橄榄,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种植以获取油脂。栽培橄榄不仅比野生橄榄更大,而且含油量更高。古代农民选择芝麻、芥菜、罂粟和亚麻等作物也是为了富含油脂的种子,而现代植物科学家对向日葵、红花和棉花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在最近棉花被开发用于榨油之前,它当然是因其纤维而被选择,用于编织纺织品。纤维(称为棉绒)是棉籽上的毛发,美洲和旧大陆的早期农民独立选择了不同种类的棉花来获得长棉绒。在亚麻和大麻这两种用于供应古代纺织品的植物中,纤维来自茎部,人们选择茎长且直的植株。虽然我们认为大多数作物是为了食物而种植的,但亚麻是我们最古老的作物之一(约在公元前7000年驯化)。它提供了亚麻布,这种布料一直是欧洲的主要纺织品,直到工业革命后被棉花和合成纤维所取代。
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野生植物进化为作物的所有变化都涉及早期农民实际上能够注意到的特征——如水果大小、苦味、多肉性、含油量和纤维长度。通过收获那些具有这些理想品质的野生植株,古代人无意识地传播了这些植物,使它们走上了驯化之路。
此外,还有至少其他四种主要类型的变化不涉及采摘者做出可见的选择。在这些情况下,采摘者要么通过收获可获得的植物而其他植物因不可见的原因无法获得而导致变化,要么通过改变作用于植物的选择条件而导致变化。
第一个这样的变化影响了野生种子传播机制(seed dispersal mechanisms)。许多植物有专门的机制来散播种子(从而防止人类有效地收集它们)。只有缺乏这些机制的突变种子才会被收获,从而成为作物的祖先。
一个清楚的例子涉及豌豆,其种子(我们吃的豌豆)被包裹在豆荚中。野生豌豆必须从豆荚中出来才能发芽。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豌豆植物进化出一个基因使豆荚爆裂,将豌豆射到地上。偶尔的突变豌豆的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突变豌豆会死在母株上的豆荚中,只有爆裂的豆荚才能传递它们的基因。但相反,人类可以收获的豆荚只有留在植株上的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生豌豆带回家吃,就立即对这种单基因突变体进行了选择。类似的不爆裂突变体在扁豆、亚麻和罂粟中也被选择了。
野生小麦和大麦的种子不是被包裹在可爆裂的豆荚中,而是生长在茎秆顶部,茎秆会自动破碎,将种子掉落到地上发芽。单基因突变可以防止茎秆破碎。在野外,这种突变对植物来说是致命的,因为种子会悬在空中,无法发芽和生根。但这些突变种子会方便地等在茎秆上被人类收获并带回家。当人类种植这些收获的突变种子时,后代中的任何突变种子又可以被农民收获和播种,而后代中的正常种子则落到地上变得无法获得。因此,人类农民将自然选择的方向逆转了180度:以前成功的基因突然变得致命,而致命的突变体变得成功。一万多年前,这种对不破碎小麦和大麦茎秆的无意识选择显然是人类对任何植物的第一次重大”改良”。这一变化标志着肥沃新月地带农业的开始。
第二种变化对古代徒步旅行者来说更加不易察觉。对于生长在气候极不可预测地区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种子都迅速同时发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幼苗可能会被一次干旱或霜冻全部杀死,导致没有种子来繁殖该物种。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进化出通过发芽抑制剂(germination inhibitors)来对冲风险的策略,这些抑制剂使种子最初处于休眠状态,并将它们的发芽分散到几年内。这样一来,即使大多数幼苗被恶劣天气杀死,仍会有一些种子留待以后发芽。
野生植物实现这一结果的常见对冲适应方式是用厚外皮或护甲包裹种子。许多具有这种适应性的野生植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亚麻和向日葵。虽然这些晚发芽的种子在野外仍有机会发芽,但想想随着农业发展会发生什么。早期农民会通过反复试验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耕作和浇水,然后播种来获得更高的产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立即发芽的种子长成的植物,其种子会被收获并在下一年播种。但许多野生种子没有立即发芽,它们没有产生收获。
野生植物中偶尔出现的变异个体缺乏厚厚的种皮或其他发芽抑制剂。所有这些变异体都会迅速发芽并产生可收获的变异种子。早期农民不会注意到这种差异,不像他们注意到并选择性收获大浆果那样。但播种/生长/收获/播种的循环会立即且无意识地选择这些变异体。与种子传播的变化一样,这些发芽抑制的变化是小麦、大麦、豌豆和许多其他作物与其野生祖先相比的特征。
早期农民看不见的最后一种主要变化类型涉及植物繁殖。作物培育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偶尔出现的变异植物个体对人类更有用(例如,因为种子更大或不那么苦),而不是正常个体。如果这些理想的变异体继续与正常植物杂交,突变将立即被稀释或丢失。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被保留给早期农民呢?
对于自我繁殖的植物,变异体会自动被保留。这对于营养繁殖(从母株的块茎或根部)或能够自我授粉的雌雄同体植物来说是正确的。但绝大多数野生植物不是以这种方式繁殖的。它们要么是无法自我授粉并被迫与其他雌雄同体个体杂交的雌雄同体(我的雄性部分授粉你的雌性部分,你的雄性部分授粉我的雌性部分),要么作为独立的雄性和雌性个体存在,就像所有正常的哺乳动物一样。前者被称为自交不亲和雌雄同体(self-incompatible hermaphrodites);后者被称为雌雄异株物种(dioecious species)。两者对古代农民来说都是坏消息,他们会因此迅速失去任何有利的变异体,却不明白为什么。
解决方案涉及另一种看不见的变化。许多植物突变影响繁殖系统本身。一些变异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能结出果实,从而产生了我们的无籽香蕉、葡萄、橙子和菠萝。一些变异雌雄同体失去了自交不亲和性,变得能够自我授粉——这一过程以许多果树为例,如李子、桃子、苹果、杏子和樱桃。一些通常具有独立雄性和雌性个体的变异葡萄也变成了自花授粉的雌雄同体。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不了解植物繁殖生物学的古代农民,仍然最终获得了可靠繁殖且值得重新种植的有用作物,而不是最初有希望的变异体,其无价值的后代被遗忘。
因此,农民不仅根据可感知的品质如大小和味道从个体植物中进行选择,还根据看不见的特征如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学进行选择。结果,不同的植物被选择出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特征。一些植物(如向日葵)被选择培育出更大的种子,而其他植物(如香蕉)则被选择培育出微小甚至不存在的种子。生菜被选择培育茂盛的叶子,牺牲了种子或果实;小麦和向日葵被选择培育种子,牺牲了叶子;南瓜被选择培育果实,牺牲了叶子。特别有启发性的案例是,单一野生植物物种为了不同目的被进行各种选择,从而产生了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就已经种植用于食用其叶子(就像现代称为瑞士甜菜的甜菜品种),然后为其可食用的根部而培育,最后(在18世纪)为其含糖量而培育(糖用甜菜)。祖先白菜植物,可能最初种植用于其含油种子,经历了更大的多样化,因为它们被各种选择用于叶子(现代卷心菜和羽衣甘蓝)、茎(球茎甘蓝)、芽(抱子甘蓝)或花茎(花椰菜和西兰花)。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野生植物在农民有意或无意选择下转化为作物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最初选择某些野生植物个体的种子带到他们的园子里,然后每年选择某些后代种子在下一年的园子里种植。但许多转化也是植物自我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词是指在自然条件下,某个物种的某些个体比同一物种的竞争个体存活得更好和/或繁殖得更成功。实际上,是差异化生存和繁殖的自然过程在进行选择。如果条件改变,不同类型的个体现在可能存活或繁殖得更好并被”自然选择”,结果是种群发生进化变化。一个经典例子是英国飞蛾的工业黑化现象:随着19世纪环境变得更脏,较深色的飞蛾个体相对于较浅色的个体变得更常见,因为停在深色、肮脏树木上的深色飞蛾比对比鲜明的浅色飞蛾更有可能逃脱捕食者的注意。
正如工业革命改变了飞蛾的环境,农业改变了植物的环境。一个经过耕作、施肥、浇水、除草的园子提供的生长条件与干燥、未施肥的山坡截然不同。植物在驯化过程中的许多变化源于这种条件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利个体类型的变化。例如,当农民在园子里密集播种时,种子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能够利用良好条件快速生长的大种子现在会比小种子更受青睐,而小种子以前在种子稀疏、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干燥、未施肥山坡上更受青睐。植物之间这种增强的竞争对种子尺寸增大以及野生植物转化为古代作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其他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比如有些物种很早就被驯化,有些直到中世纪才被驯化,而其他一些野生植物至今仍对我们的所有活动免疫?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西南亚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各种作物发展的既定顺序来推断出许多答案。
事实证明,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大约1万年前驯化的小麦、大麦和豌豆,源自提供许多优势的野生祖先。它们在野生状态下就已经可食用并能提供高产量。它们易于种植,只需播种或栽种即可。它们生长迅速,播种后几个月内就可以收获,这对于仍处于游牧狩猎者和定居村民之间边界的早期农民来说是一个巨大优势。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储存,不像后来的许多作物如草莓和生菜。它们大多是自花授粉(self-pollinating)的:也就是说,作物品种可以自我授粉并原封不动地传递自己的理想基因,而不必与对人类用处较小的其他品种杂交。最后,它们的野生祖先只需要很少的基因改变就能转化为作物——例如,小麦只需要非落粒茎秆和均匀快速发芽的突变。
下一阶段的作物发展包括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被驯化。它们包括橄榄、无花果、枣椰、石榴和葡萄。与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们的缺点是种植后至少三年才开始产出食物,十年后才能达到完全生产。因此,种植这些作物只有对于已经完全致力于定居村庄生活的人来说才可行。然而,这些早期的果树和坚果树仍然是最容易栽培的此类作物。与后来的树木驯化品种不同,它们可以直接通过扦插甚至种子种植。扦插的优势在于,一旦古代农民找到或培育出一棵高产树木,他们就可以确保它的所有后代都与它保持一致。
第三阶段涉及事实证明更难栽培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李子和樱桃。这些树木不能通过扦插种植。从种子种植它们也是浪费精力,因为即使是这些物种中杰出个体树木的后代也是高度可变的,大多会产出无价值的果实。相反,这些树木必须通过嫁接(grafting)这种困难技术来种植,该技术在农业开始很久之后才在中国发展出来。嫁接不仅在你知道原理后仍然很费力,而且原理本身只能通过有意识的实验才能发现。嫁接的发明绝不仅仅是某个游牧者在茅房里方便后来返回时惊喜地发现结出优质水果的作物那么简单。
这些晚期果树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它们的野生祖先恰恰相反,不能自花授粉。它们必须由同种但遗传上不同品种的另一株植物进行异花授粉(cross-pollination)。因此,早期农民要么必须找到不需要异花授粉的变异树木,要么必须有意识地在同一果园中种植遗传上不同的品种,或者将雌雄个体种植在附近。所有这些问题都推迟了苹果、梨、李子和樱桃的驯化,直到古典时代前后。不过,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组晚期驯化作物以更少的努力出现了,它们最初是在有意栽培的农田中作为杂草定居的野生植物。最初作为杂草出现的作物包括黑麦和燕麦、芜菁和萝卜、甜菜和韭葱,以及生菜。
我刚才描述的详细序列适用于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部分相似的序列。特别是,肥沃月湾的小麦和大麦代表了被称为谷物(cereals)或粮食(grains)的作物类别(禾本科成员),而肥沃月湾的豌豆和扁豆代表了豆类作物(pulses)(豆科成员,包括各种豆类)。谷物作物具有生长快速、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以及每公顷可产出高达一吨可食用食物的优点。因此,今天谷物占人类消耗的所有卡路里的一半以上,并包括现代世界12种主要作物中的5种(小麦、玉米、水稻、大麦和高粱)。许多谷物作物的蛋白质含量较低,但豆类作物弥补了这一不足,豆类通常含有25%的蛋白质(大豆为38%)。因此,谷物和豆类共同提供了均衡饮食的许多成分。
如表7.1(下一页)所总结的,本地谷物/豆类组合的驯化在许多地区启动了粮食生产。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肥沃月湾的小麦和大麦与豌豆和扁豆的组合,中美洲的玉米与几种豆类的组合,以及中国的水稻和小米与大豆及其他豆类的组合。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非洲的高粱、非洲稻和珍珠粟与豇豆和花生的组合,以及安第斯山脉的非谷物粮食藜麦(quinoa)与几种豆类的组合。
表7.1还显示,肥沃月湾早期驯化亚麻用于纤维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大麻、四种棉花、丝兰和龙舌兰分别在中国、中美洲、印度、埃塞俄比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提供了制作绳索和编织衣物的纤维,其中几个地区还辅以来自家养动物的羊毛。在早期粮食生产中心中,只有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没有纤维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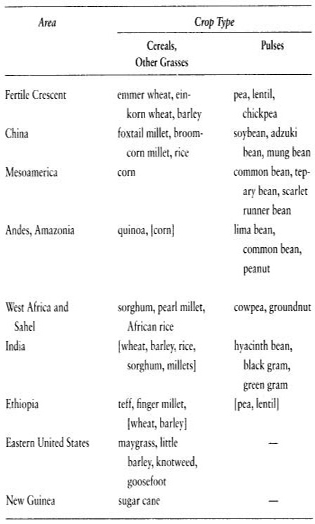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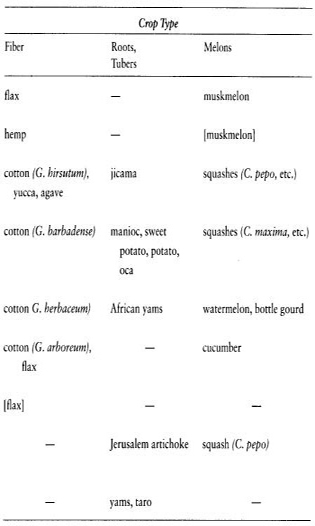
该表列出了世界各地早期农业遗址的五类作物中的主要作物。方括号内为首先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名称;未用方括号括起来的名称指本地驯化作物。省略了后来才到达或变得重要的作物,例如非洲的香蕉、美国东部的玉米和豆类,以及新几内亚的甘薯。棉花是棉属(Gossypium)的四个物种,每个物种原产于世界的特定地区;南瓜是葫芦属(Cucurbita)的五个物种。请注意,谷物、豆类和纤维作物在大多数地区启动了农业,但根茎类作物和瓜类只在某些地区具有早期重要性。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系统也存在一些主要差异。其中之一是旧大陆(Old World)的大部分农业涉及撒播种子和单一作物田,并最终使用犁耕。也就是说,种子是通过手工撒播来播种的,结果是整块田地专门种植单一作物。一旦牛、马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被驯化,它们就被套上犁,田地由畜力耕作。然而,在新大陆(New World),从未有动物被驯化来拉犁。相反,田地总是用手持的棍子或锄头耕作,种子是逐个用手种植的,而不是成把撒播。因此,大多数新大陆的田地成为了多种作物混合种植的花园,而不是单一作物田。
农业系统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如我们所见,在许多地区这些是谷物。但在其他地区,谷物的这一作用被根茎类作物取代或分担,而根茎类作物在古代肥沃月湾和中国几乎无足轻重。木薯(别名树薯)和甘薯成为热带南美洲的主食,马铃薯和oca(酢浆草)成为安第斯山脉的主食,非洲山药在非洲,印度-太平洋山药和芋头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树木作物,特别是香蕉和面包果,也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提供了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
因此,到罗马时代,今天几乎所有主要作物都已在世界某个地方被种植。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的家畜情况一样,古代狩猎采集者对当地野生植物非常熟悉,古代农民显然发现并驯化了几乎所有值得驯化的植物。当然,中世纪修道士确实开始种植草莓和覆盆子,现代植物育种家仍在改良古老作物,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次要作物,特别是一些浆果(如蓝莓、蔓越莓和猕猴桃)和坚果(澳洲坚果、山核桃和腰果)。但与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古老主食相比,这些现代添加的作物仍然不太重要。
尽管如此,我们的成功清单中仍缺少许多野生植物,尽管它们作为食物很有价值,但我们从未成功驯化过它们。其中最显著的失败案例是橡树,其橡子是加州和美国东部土著美国人的主食,也是欧洲农民在农作物歉收饥荒时期的后备食物。橡子营养价值高,富含淀粉和油脂。像许多可食用的野生食物一样,大多数橡子确实含有苦味的单宁(tannins),但橡子爱好者学会了处理单宁的方法,就像他们处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的苦味化学物质一样:要么通过研磨和浸泡橡子来去除单宁,要么从偶尔出现的低单宁突变橡树上收获橡子。
为什么我们未能驯化像橡子这样珍贵的食物来源?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驯化草莓和覆盆子?是什么使这些植物的驯化超出了掌握嫁接等高难度技术的古代农民的能力范围?
事实证明,橡树有三个不利因素。首先,它们的缓慢生长会耗尽大多数农民的耐心。播种的小麦在几个月内就能收获;种植的杏树在三四年内就能结果;但种植的橡子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产出。其次,橡树进化出适合松鼠的大小和味道的坚果,我们都见过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子。橡树是从松鼠偶尔忘记挖出的橡子中生长出来的。数十亿只松鼠每年将数百个橡子传播到几乎任何适合橡树生长的地方,我们人类根本没有机会选择能产出我们想要的橡子的橡树。同样的缓慢生长和快速松鼠问题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和土著美国人分别大量开发山毛榉和山核桃树作为野生坚果树,但也没有被驯化。
最后,也许杏仁和橡子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杏仁的苦味由单个显性基因(dominant gene)控制,而橡子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控制。如果古代农民种植来自偶尔出现的非苦味突变树的杏仁或橡子,遗传学定律表明,对于杏仁来说,生长出来的树结出的坚果中有一半也是非苦味的,但对于橡子来说,几乎所有橡子仍然是苦的。仅这一点就足以打消任何击败松鼠并保持耐心的潜在橡子种植者的热情。
至于草莓和覆盆子,我们在与画眉和其他喜欢浆果的鸟类竞争时遇到了类似的麻烦。是的,罗马人确实在他们的花园里照料野生草莓。但是,数十亿只欧洲画眉在每个可能的地方(包括罗马花园)排泄野生草莓种子,草莓仍然是画眉想要的小浆果,而不是人类想要的大浆果。只有在最近开发了防护网和温室之后,我们才终于能够击败画眉,并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重新设计草莓和覆盆子。
我们已经看到,巨大的超市草莓和微小的野生草莓之间的差异,只是区分栽培植物与其野生祖先的各种特征的一个例子。这些差异最初来自野生植物本身的自然变异。其中一些变异,如浆果大小或坚果苦味的变异,古代农民很容易注意到。其他变异,如种子传播机制(seed dispersal mechanisms)或种子休眠(seed dormancy)的变异,在现代植物学兴起之前,人类是不会认识到的。但是,无论古代徒步旅行者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选择是依赖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标准,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最终进化起初都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源于我们在野生植物个体中进行的选择,以及花园中植物个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与野外不同的个体。
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在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中,并没有从自然选择的叙述开始。相反,他的第一章是关于我们的驯化植物和动物如何通过人类的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产生的详细说明。达尔文没有讨论我们通常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鸟类,而是从讨论农民如何培育醋栗品种开始!他写道:“我在园艺著作中看到人们对园丁的高超技艺表示极大的惊讶,因为他们从如此贫乏的材料中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但这门技艺一直很简单,就最终结果而言,几乎是无意识地遵循的。它包括总是培育最知名的品种,播种其种子,当偶然出现稍好的品种时,选择它,如此循环往复。”这些通过人工选择进行作物培育的原则,至今仍是我们理解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物种起源的最易懂模型。
我们刚刚看到一些地区的人们如何开始种植野生植物物种,这一步骤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后代在历史上的地位产生了意义深远且未曾预见的后果。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农业从未在一些肥沃且高度适宜的地区独立产生,比如加利福尼亚、欧洲、温带澳大利亚和亚赤道非洲?为什么在那些确实独立产生农业的地区中,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早得多?
两种对比鲜明的解释浮现出来:当地人的问题,或者当地可获得的野生植物的问题。一方面,也许地球上几乎任何水源充足的温带或热带地区都提供了足够多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未能在其中一些地区发展的解释就在于当地人民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许地球上任何大片地区的至少一些人都会接受导致驯化的实验。那么,只有缺乏合适的野生植物才能解释为什么粮食生产没有在某些地区演化。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驯化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相应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它们的物种数量比植物少得多。世界上只有大约148种大型野生陆生草食性或杂食性哺乳动物,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可以被视为驯化的候选者。只有少量因素决定哺乳动物是否适合驯化。因此,检查一个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并测试某些地区缺乏哺乳动物驯化是否由于缺乏合适的野生物种,而不是由于当地人民,是很直接的。
这种方法应用于植物会困难得多,因为野生开花植物的物种数量巨大——200,000种,这些植物主宰着陆地上的植被,并提供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作物。我们不可能希望检查甚至像加利福尼亚这样有限地区的所有野生植物物种,并评估其中有多少可以被驯化。但我们现在将看到如何绕过这个问题。
当人们听说有这么多开花植物物种时,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样的:当然,地球上有这么多野生植物物种,任何气候足够温和的地区肯定有足够多的物种为作物开发提供大量候选者。
但接着想想,绝大多数野生植物因为明显的原因不适合:它们是木本的,不产生可食用的果实,它们的叶子和根也不可食用。在200,000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被人类食用,其中只有几百种或多或少被驯化了。即使在这几百种作物中,大多数只是我们饮食的次要补充,本身不足以支持文明的兴起。仅仅十几个物种就占现代世界所有作物年产量的80%以上。这十几个重量级作物是谷物小麦、玉米、水稻、大麦和高粱;豆类大豆;根茎或块茎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源甘蔗和甜菜;以及水果香蕉。仅谷物作物现在就占世界人口消费热量的一半以上。世界上只有这么少的主要作物,所有这些都是数千年前驯化的,许多世界地区完全没有任何具有突出潜力的野生本土植物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我们在现代未能驯化哪怕一种主要的新食用植物,这表明古代人民可能真的已经探索了几乎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植物。
然而,世界上一些未能驯化野生植物的情况仍然难以解释。最明显的案例涉及在一个地区被驯化但在另一个地区未被驯化的植物。因此,我们可以确信,确实有可能将野生植物发展成有用的作物,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该野生物种没有在某些地区被驯化。
一个典型的令人困惑的例子来自非洲。重要的谷物高粱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驯化,该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高粱作为野生植物也分布在南部非洲,但在2000年前班图农民从赤道以北的非洲带来整套作物包之前,南部非洲既没有种植高粱,也没有种植任何其他植物。为什么南部非洲的土著人没有自己驯化高粱?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人们未能在西欧和北非的野生亚麻分布区驯化亚麻,也未能在巴尔干南部的野生一粒小麦分布区驯化一粒小麦。由于这两种植物是肥沃月湾的最早八种作物之一,它们大概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驯化的。一旦这些植物随着肥沃月湾的整套粮食生产包传来,肥沃月湾以外野生分布区的那些地区就立即采用它们进行种植。那么,为什么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们没有主动开始种植它们呢?
同样,肥沃月湾最早驯化的四种水果的野生分布范围都远远超出东地中海地区,而它们似乎首次在东地中海地区被驯化: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向西分布到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非洲,而椰枣则延伸到整个北非和阿拉伯地区。这四种显然是所有野生水果中最容易驯化的。为什么肥沃月湾以外的人们未能驯化它们,只是在它们已经在东地中海被驯化并作为作物传来后才开始种植它们?
其他引人注目的例子涉及野生物种,这些物种在从未自发产生粮食生产的地区没有被驯化,尽管这些野生物种有在其他地方被驯化的近亲。例如,橄榄(Olea europea)在东地中海被驯化。在热带和南部非洲、南亚和东澳大利亚还有大约40种其他橄榄物种,其中一些与Olea europea关系密切,但没有一种被驯化过。同样,虽然欧亚大陆驯化了一种野生苹果和一种野生葡萄,但北美有许多相关的野生苹果和葡萄物种,其中一些在现代已与源自欧亚野生对应物的作物杂交,以改良这些作物。那么,为什么美洲原住民没有自己驯化那些明显有用的苹果和葡萄呢?
这样的例子可以不断列举。但这种推理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植物驯化不是狩猎采集者驯化单一植物,然后继续以游牧生活方式生活的问题。假设北美野生苹果如果印第安狩猎采集者定居下来并种植它们,真的会进化成一种了不起的作物。但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不会放弃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定居在村庄里,开始照料苹果园,除非有许多其他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可供利用,使定居的粮食生产生活能够与狩猎采集生活竞争。
简而言之,我们如何评估整个当地植物群的驯化潜力?对于那些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美洲原住民来说,问题真的在于印第安人还是在于苹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将比较三个地区,它们在独立驯化中心中处于相反的极端。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一个地区——肥沃月湾,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也是现代世界几种主要作物和几乎所有主要驯化动物的起源地。另外两个地区——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确实驯化了当地作物,但这些作物品种很少,只有一种获得了全球重要性,由此产生的粮食包未能支持人类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广泛发展,不像肥沃月湾那样。根据这一比较,我们将问:肥沃月湾的植物群和环境是否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具有明显优势?
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事实是西南亚被称为肥沃月湾的地区(因其高地在地图上呈新月形而得名:见图8.1)的早期重要性。该地区似乎是一系列发展的最早地点,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无论好坏)文明。所有这些发展反过来又源于密集的人口、储存的粮食盈余,以及由作物种植和畜牧业形式的粮食生产兴起所支持的非农业专家。粮食生产是肥沃月湾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创新。因此,任何理解现代世界起源的尝试都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肥沃月湾的驯化植物和动物给它带来了如此强大的领先优势。
幸运的是,就农业起源而言,肥沃月湾是全球研究最深入、理解最透彻的地区。对于在肥沃月湾或其附近驯化的大多数作物,野生植物祖先已被确认;通过遗传和染色体研究证明了其与作物的密切关系;其野生地理分布范围已知;其驯化过程中的变化已被识别,并且通常在单基因水平上得到理解;这些变化可以在连续的考古记录层中观察到;驯化的大致地点和时间也已知晓。我不否认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作为早期驯化地点也具有优势,但这些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作物发展,在肥沃月湾可以更详细地说明。
肥沃月湾的一个优势是它位于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干燥。这种气候筛选出能够在漫长旱季中存活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的植物物种。许多肥沃月湾植物,特别是谷物和豆类物种,以一种对人类有用的方式进行了适应:它们是一年生植物(annual plants),这意味着植物本身在旱季枯萎死亡。
在仅仅一年的生命周期内,一年生植物不可避免地保持为小型草本植物。它们中的许多将大部分能量用于产生大种子,这些种子在旱季保持休眠状态,然后在雨季来临时准备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很少浪费能量制造不可食用的木材或纤维茎,如树木和灌木的主体。但许多大种子,特别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可供人类食用。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12种主要作物中的6种。相比之下,如果你住在森林附近并向窗外望去,你看到的植物物种往往是树木和灌木,它们的大部分身体你无法食用,并且它们投入可食用种子的能量要少得多。当然,潮湿气候地区的一些森林树木确实会产生大的可食用种子,但这些种子不适应在漫长旱季中存活,因此也不适合人类长期储存。
肥沃月湾植物群的第二个优势是,许多肥沃月湾作物的野生祖先已经很丰富且高产,形成大片分布,其价值对狩猎采集者来说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植物学家从这些野生谷物的自然分布中收集种子的实验研究——就像一万多年前狩猎采集者一定在做的那样——表明,每公顷可获得近一吨种子的年收成,每消耗一千卡工作能量可产出50千卡食物能量。通过在种子成熟时的短时间内收集大量野生谷物,并储存起来作为全年的食物,肥沃月湾的一些狩猎采集民族甚至在开始种植植物之前就已经定居在永久性村庄中。
由于肥沃月湾谷物在野生状态下就如此高产,在栽培过程中几乎不需要对它们进行额外的改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的那样,主要变化——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的自然系统的瓦解——一旦人类开始在田地里种植种子,就会自动且迅速地进化。我们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野生祖先看起来与作物本身如此相似,以至于祖先的身份从未受到质疑。由于这种驯化的容易性,大种子一年生植物不仅在肥沃月湾,而且在中国和萨赫勒地区都是最早或最早之一开发的作物。
将小麦和大麦的快速进化与玉米的故事进行对比,玉米是新大陆的主要谷物作物。玉米的可能祖先,一种被称为类蜀黍(teosinte)的野生植物,在种子和花结构上看起来与玉米如此不同,以至于植物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激烈争论其作为祖先的角色。类蜀黍作为食物的价值不会给狩猎采集者留下深刻印象:它在野生状态下的产量低于野生小麦,它产生的种子远少于最终从中培育出的玉米,并且它将种子包裹在不可食用的坚硬外壳中。为了使类蜀黍成为有用的作物,它必须在生殖生物学上经历剧烈变化,大幅增加对种子的投入,并失去那些岩石般坚硬的种子外壳。考古学家仍在激烈争论美洲的作物开发需要多少个世纪或千年才能使古代玉米棒从微小尺寸发展到人类拇指大小,但似乎很明显,随后又需要数千年才能达到现代尺寸。小麦和大麦的直接优势与类蜀黍带来的困难之间的对比,可能是新大陆和欧亚大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肥沃月牙地区植物群的第三个优势是,它包含了很高比例的雌雄同体”自花授粉植物”——也就是那些通常自我授粉,但偶尔会进行异花授粉的植物。回想一下,大多数野生植物要么是定期异花授粉的雌雄同体植物,要么由独立的雄性和雌性个体组成,必然依赖另一个个体进行授粉。这些生殖生物学事实让早期农民感到困扰,因为一旦他们找到了一株高产的变异植物,它的后代就会与其他植株杂交,从而失去遗传优势。因此,大多数作物都属于少数几类野生植物:要么是通常自我授粉的雌雄同体植物,要么通过营养繁殖进行无性繁殖(例如,通过根茎在基因上复制母株)。因此,肥沃月牙地区植物群中自花授粉植物的高比例帮助了早期农民,因为这意味着野生植物群中有很高比例的植物具有便于人类利用的生殖生物学特性。
自花授粉植物对早期农民来说也很方便,因为它们偶尔会进行异花授粉,从而产生新品种供人们选择。这种偶尔的异花授粉不仅发生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也发生在相关物种之间,产生种间杂交品种。肥沃月牙地区自花授粉植物中的一个这样的杂交品种——面包小麦,成为了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作物。
在肥沃月牙地区最早驯化的八种重要作物中,全部都是自花授粉植物。其中三种自花授粉谷物——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小麦提供了高蛋白含量的额外优势,达到8-14%。相比之下,东亚和新世界最重要的谷物作物——分别是水稻和玉米——蛋白质含量较低,造成了重大的营养问题。
这些是肥沃月牙地区植物群为第一批农民提供的一些优势:它包含了异常高比例的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然而,肥沃月牙地区的地中海气候带向西延伸,覆盖了南欧和北非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世界上其他四个地区也有类似的地中海气候带: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图8.2)。然而,这些其他地中海气候带不仅未能与肥沃月牙地区竞争成为早期粮食生产地;它们根本就没有产生本土农业。西欧亚大陆的这个特定地中海气候带享有什么优势?
事实证明,它,特别是其肥沃月牙部分,相对于其他地中海气候带至少拥有五个优势。首先,西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中海气候带。因此,它拥有高度多样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物种,高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智利相对较小的地中海气候带。其次,在地中海气候带中,西欧亚大陆经历的季节间和年际气候变化最大。这种变化促进了植物群中特别高比例的一年生植物的进化。这两个因素的结合——物种的高度多样性和一年生植物的高比例——意味着西欧亚大陆的地中海气候带是一年生植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地理学家马克·布鲁姆勒对野生草类分布的研究说明了这种植物学财富对人类的意义。在世界上数千种野生草类中,布鲁姆勒统计了种子最大的56种,即自然界作物的精华:种子重量至少是草类物种中位数10倍的草类物种(见表8.1)。几乎所有这些都原产于地中海气候带或其他季节性干旱环境。此外,它们绝大多数集中在肥沃月牙地区或西欧亚大陆地中海气候带的其他部分,为初期农民提供了巨大的选择:世界上56种优质野生草类中约有32种!具体来说,肥沃月牙地区最早的两种重要作物大麦和二粒小麦,在这前56种中种子大小分别排名第3和第13位。相比之下,智利的地中海气候带只提供了两种这样的物种,加利福尼亚和南非各一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则一种也没有。仅这一事实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肥沃月牙地区地中海气候带的第三个优势是,它在短距离内提供了广泛的海拔和地形。其海拔范围从地球上最低点(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靠近德黑兰),确保了相应的环境多样性,因此作为潜在作物祖先的野生植物具有高度多样性。这些山脉毗邻适合灌溉农业的平缓低地,包括河流、洪泛平原和沙漠。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西南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南非和西欧的地中海气候带,提供的海拔、栖息地和地形范围较窄。
表8.1 世界大种子草类物种分布
| 地区 | 物种数量 |
|---|---|
| 西亚、欧洲、北非 | 33 |
| 地中海气候带 | 32 |
| 英格兰 | 1 |
| 东亚 | 6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4 | |
| 美洲 | 11 | |
| 北美洲 | 4 | |
| 中美洲 | 5 | |
| 南美洲 | 2 | |
| 澳大利亚北部 | 2 | |
| 总计: | 56 |
Mark Blumler的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和以色列地中海型草原中的种子重量与环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92年)的表12.1列出了世界上56种可获得数据的最重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不包括竹子)。这些物种的谷物重量从10毫克到超过40毫克不等,大约是世界上所有禾本科植物物种中位数值的10倍。这56个物种占世界禾本科植物物种的不到1%。该表显示,这些优质禾本科植物绝大多数集中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地区。
新月沃地的海拔范围意味着收获季节是错开的:高海拔地区的植物产籽时间略晚于低海拔地区的植物。因此,狩猎采集者可以沿着山坡向上移动,在谷物种子成熟时进行采收,而不是在单一海拔地区被集中的收获季节所压垮,那里所有谷物同时成熟。当栽培开始时,第一批农民很容易就能取生长在山坡上、依赖不可预测降雨的野生谷物的种子,并将这些种子种植在潮湿的谷底,在那里它们会可靠地生长,减少对降雨的依赖。
新月沃地在短距离内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第四个优势——它不仅拥有宝贵作物的祖先,还拥有驯化大型哺乳动物的祖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的其他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适合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物种。相比之下,四种大型哺乳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被驯化,可能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除狗之外的任何其他动物都要早。这些物种至今仍是世界上五种最重要的驯化哺乳动物中的四种(第9章)。但它们的野生祖先在新月沃地的不同部分最为常见,结果这四个物种在不同地方被驯化:绵羊可能在中部地区,山羊要么在东部高海拔地区(伊朗扎格罗斯山脉),要么在西南部地区(黎凡特),猪在中北部地区,牛在西部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尽管如此,即使这四种野生祖先的丰富区域有所不同,但所有四种都生活在足够近的距离内,以至于它们在驯化后很容易从新月沃地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整个地区最终都拥有了所有四个物种。
新月沃地的农业是通过早期驯化八种作物而启动的,这些作物被称为”奠基作物”(因为它们在该地区可能也是在世界上奠定了农业基础)。这八种奠基作物是谷物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豆类扁豆、豌豆、鹰嘴豆和苦野豌豆;以及纤维作物亚麻。在这八种作物中,只有两种,亚麻和大麦,在新月沃地和安纳托利亚之外的野生范围较广。其中两种奠基作物的野生分布范围非常小,鹰嘴豆仅限于土耳其东南部,二粒小麦仅限于新月沃地本身。因此,新月沃地的农业可以通过驯化当地可用的野生植物而产生,而无需等待从其他地方驯化的野生植物衍生作物的到来。相反,八种奠基作物中的两种只能在新月沃地被驯化,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野生分布。
由于这些适合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的可获得性,新月沃地的早期人类可以迅速组装一个强大而平衡的生物组合,用于集约化粮食生产。该组合包括三种谷物,作为主要碳水化合物来源;四种豆类,含有20-25%的蛋白质,以及四种家畜,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由小麦的丰富蛋白质含量补充;以及亚麻作为纤维和油的来源(称为亚麻籽油:亚麻籽约含40%的油)。最终,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开始数千年后,这些动物也开始被用于产奶、产毛、耕作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第一批农民的作物和动物满足了人类的基本经济需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物、牵引力和运输。
肥沃月湾早期粮食生产的最后一个优势在于,它可能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比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地中海西部)要少。西南亚几乎没有大河,海岸线也很短,提供的水生资源相对贫乏(以河流和沿海鱼类及贝类的形式)。作为肉类来源被狩猎的重要哺乳动物物种之一——瞪羚,最初生活在巨大的兽群中,但被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度捕猎,数量减少到很低的水平。因此,粮食生产组合很快就变得优于狩猎采集组合。基于谷物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使得那些狩猎采集者倾向于农业和畜牧业。在肥沃月湾,从狩猎采集到粮食生产的过渡发生得相对较快:直到公元前9000年,人们还没有作物和家养动物,完全依赖野生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一些社会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养动物。
中美洲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该地区只提供了两种可驯化的动物(火鸡和狗),它们的肉产量远低于牛、羊、山羊和猪;而玉米作为中美洲的主粮,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很难驯化,发展可能也很缓慢。因此,中美洲的驯化可能直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才开始(日期仍然非常不确定);这些最初的发展是由仍然是游牧狩猎采集者的人们进行的;定居村庄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在那里出现。
在所有这些关于肥沃月湾在粮食生产早期兴起方面优势的讨论中,我们不必援引肥沃月湾人民自身的任何所谓优势。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任何人认真提出过该地区人民的任何所谓独特生物学特征可能对其粮食生产组合的效力有所贡献。相反,我们已经看到,肥沃月湾的气候、环境、野生植物和动物的许多独特特征共同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由于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本土产生的粮食生产组合效力要弱得多,那么解释是否在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然而,在转向这些地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两个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世界上任何粮食生产从未独立发展或导致效力较弱组合的地区。首先,狩猎采集者和初期农民是否真的很了解当地所有可用的野生物种及其用途,还是他们可能忽略了有价值作物的潜在祖先?其次,如果他们确实了解当地的植物和动物,他们是否利用这些知识来驯化最有用的可用物种,还是文化因素阻止他们这样做?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称为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研究人们对其环境中野生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这类研究特别集中在世界上少数幸存的狩猎采集民族,以及仍然严重依赖野生食物和天然产品的农耕民族。研究通常表明,这些民族是行走的自然史百科全书,用他们当地语言为多达一千种或更多植物和动物物种命名(用他们的当地语言),并详细了解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征、分布和潜在用途。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价值并被遗失,直到人们变成无法区分野草和野生豆类的现代超市购物者。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的33年里,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探索时,我一直在那里与仍然广泛使用野生植物和动物的新几内亚人一起度过我的野外时间。有一天,当我和福雷部落的同伴们在丛林中挨饿,因为另一个部落阻挡了我们返回补给基地的路线时,一个福雷人带着一大背包他找到的蘑菇回到营地,开始烤它们。终于有晚餐了!但随后我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同伴解释说,我读过一些蘑菇有毒的文章,我听说即使是美国专业蘑菇采集者也因难以区分安全和危险的蘑菇而死亡,虽然我们都很饿,但不值得冒这个险。此时我的同伴们生气了,让我闭嘴,听他们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在我多年来向他们询问数百种树木和鸟类的名称之后,我怎么能侮辱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不同蘑菇的名称?只有美国人才会愚蠢到把有毒蘑菇和安全蘑菇混淆。他们继续向我讲授29种可食用蘑菇物种,每个物种在福雷语中的名称,以及应该在森林的什么地方寻找它。这一种,叫作tánti,长在树上,它很美味,完全可以食用。
每当我带新几内亚人去他们岛屿的其他地方时,他们总是会和遇到的其他新几内亚人讨论当地的植物和动物,并且会收集可能有用的植物带回家乡村庄尝试种植。我在新几内亚的经历与其他地方研究传统民族的民族生物学家的经历相似。然而,所有这些民族要么至少从事一些粮食生产,要么是世界上曾经的狩猎采集社会部分文化融合后的最后残余。在粮食生产兴起之前,当地球上所有人仍然完全依赖野生物种获取食物时,对野生物种的了解可能更加详细。最初的农民继承了这些知识,这些知识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通过数万年对自然的观察积累而来的,他们生活在与自然世界密切依存的关系中。因此,有潜在价值的野生物种几乎不可能逃过最初农民的注意,这似乎是极其不可能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古代狩猎采集者和农民是否同样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民族生物学知识来选择要采集并最终种植的野生植物。一个检验来自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谷边缘的一个考古遗址,名为特尔阿布胡雷拉。在公元前10,000到9000年之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可能已经常年居住在村庄中,但他们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农作物种植直到下一个千年才开始。考古学家戈登·希尔曼、苏珊·科莱奇和大卫·哈里斯从该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烧焦的植物遗骸,可能代表居民从其他地方采集并带到遗址的野生植物的废弃垃圾。科学家们分析了700多个样本,每个样本平均包含500多颗可识别的种子,属于70多个植物物种。结果发现,村民们收集的植物种类繁多(157个物种!),这些植物通过它们烧焦的种子被识别出来,更不用说其他现在无法识别的植物了。
那些天真的村民是否收集了他们发现的每一种种子植物,带回家,在大多数物种上毒害自己,只从少数几个物种中获得营养呢?不,他们没有那么愚蠢。虽然157个物种听起来像是不加选择的收集,但附近野生生长的许多其他物种并未出现在烧焦的遗骸中。这157个被选中的物种分为三类。其中许多物种的种子无毒且可以立即食用。其他一些,如豆类和芥菜科植物,虽然种子有毒,但毒素很容易去除,留下可食用的种子。少数种子属于传统上用作染料或药物来源的物种。那些157个选中物种中未出现的许多野生物种,都是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包括环境中所有毒性最强的杂草物种。
因此,特尔阿布胡雷拉的狩猎采集者并没有浪费时间和危害自己不加选择地收集野生植物。相反,他们显然像现代新几内亚人一样熟悉当地的野生植物,并利用这些知识只选择并带回最有用的种子植物。但这些采集的种子将构成植物驯化无意识的第一步的材料。
我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古代人民显然如何有效利用他们的民族生物学知识,来自公元前第九个千年的约旦河谷,那里最早农作物种植的时期。河谷最初驯化的谷物是大麦和二粒小麦,它们至今仍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作物之一。但是,就像特尔阿布胡雷拉一样,附近肯定生长着数百种其他含种子的野生植物物种,其中一百多种在植物驯化兴起之前应该是可食用和被采集的。是什么使大麦和二粒小麦成为第一批作物呢?那些最初的约旦河谷农民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植物学文盲吗?还是大麦和二粒小麦实际上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当地野生谷物中最好的?
两位以色列科学家奥弗·巴尔-约瑟夫和莫迪凯·基斯列夫通过研究今天仍在河谷中野生生长的野草物种来解决这个问题。撇开种子小或不好吃的物种不谈,他们挑选出23种味道最好、种子最大的野草。不出所料,大麦和二粒小麦在那份名单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21个候选物种同样有用。在这23种中,大麦和二粒小麦被证明在许多标准上是最好的。二粒小麦的种子最大,大麦是第二大。在野外,大麦是23个物种中4种最丰富的物种之一,而二粒小麦的丰富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大麦还有一个优势,即它的遗传学和形态学允许它快速进化出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种子传播和萌发抑制方面的有用变化。然而,二粒小麦有补偿性的优点:它比大麦更容易收集,而且在谷物中它的种子不粘附在壳上是不寻常的。至于其他21个物种,它们的缺点包括种子较小,在许多情况下丰富度较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多年生植物而不是一年生植物,因此它们在驯化过程中进化缓慢。
因此,约旦河谷的第一批农民从当地可用的23种最佳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其中最好的2种。当然,种植后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seed dispersal and germination inhibition)方面的进化变化是那些早期农民行为的意外后果。但他们最初选择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来采集、带回家并种植,这是有意识的选择,基于容易观察到的标准:种子大小、适口性和丰度。
约旦河谷的这个例子,就像阿布胡雷拉遗址的例子一样,说明了第一批农民利用他们对当地物种的详细了解来为自己谋利。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了解远超除少数现代专业植物学家之外的所有人,他们几乎不可能遗漏任何同样适合驯化的有用野生植物物种。
我们现在可以研究世界上两个地区(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当地农民在更高产的作物从其他地方传入时实际做了什么,这两个地区都有本土但与肥沃新月地带相比明显不足的粮食生产系统。如果结果表明由于文化或其他原因这些作物没有被采用,我们仍会有挥之不去的疑虑。尽管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推理,我们仍然不得不怀疑当地的野生植物群中可能存在某种有价值作物的潜在祖先,但当地农民因为类似的文化因素而未能开发利用。这两个例子还将详细展示一个对历史至关重要的事实: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本土作物并非同样高产。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岛,位于澳大利亚以北靠近赤道的位置。由于其热带位置以及地形和栖息地的巨大多样性,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尽管作为岛屿不如热带大陆地区丰富。人类在新几内亚生活至少已有4万年历史——远长于美洲,略长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在西欧的生活时间。因此,新几内亚人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当地的动植物群。他们是否有动力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呢?
我已经提到,粮食生产的采用涉及粮食生产和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并不足以消除发展粮食生产的动力。特别是,现代新几内亚猎人遭受着野生猎物匮乏这一严重劣势的困扰:没有比100磅重的不能飞的鸟类(食火鸡)和50磅重的袋鼠更大的本土陆生动物。沿海的新几内亚低地居民确实能获得大量鱼类和贝类,内陆的一些低地居民今天仍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主要依靠野生西米棕榈为生。但在新几内亚高地没有人仍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所有现代高地居民都是农民,只用野生食物来补充饮食。当高地居民进入森林狩猎时,他们会带上园圃种植的蔬菜来养活自己。如果他们不幸耗尽了这些储备,即使他们对当地可获得的野生食物有详细了解,也会饿死。由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无法维持,因此所有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大多数低地居民今天都是拥有复杂粮食生产系统的定居农民就不足为奇了。传统的新几内亚农民将高地大片原本是森林的地区改造成围栏、排水、精心管理的田地系统,养活着稠密的人口。
考古证据表明,新几内亚农业的起源很古老,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那些早期,新几内亚周围的所有陆地仍然完全被狩猎采集者占据,所以这种古老的农业一定是在新几内亚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从那些早期田地中还没有发现明确的作物遗存,但它们很可能包括一些在欧洲殖民时期在新几内亚种植的相同作物,这些作物现在已知是从野生新几内亚祖先在当地驯化而来的。这些本地驯化物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世界领先的作物——甘蔗,其今天的年产量几乎等于第二和第三大作物(小麦和玉米)的总和。其他确定起源于新几内亚的作物包括一组被称为澳洲蕉(Australimusa)的香蕉、橄榄树(Canarium indicum)和巨型沼泽芋,以及各种可食用的草茎、根和绿色蔬菜。面包果树和根茎作物山药和(普通)芋头也可能是新几内亚的驯化物,尽管这一结论仍不确定,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并不局限于新几内亚,而是从新几内亚分布到东南亚。目前我们缺乏证据来解决它们是在东南亚驯化(如传统假设)、还是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甚至仅在新几内亚驯化的问题。
然而,事实证明新几内亚的生物群系存在三个严重的局限性。首先,新几内亚没有驯化任何谷物作物,而肥沃月弯、萨赫勒和中国则驯化了几种至关重要的谷物。新几内亚反而强调根茎作物和树木作物,这将其他湿润热带地区(亚马逊、热带西非和东南亚)农业系统的趋势推向了极端,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强调根茎作物,但至少成功培育出了两种谷物(亚洲稻和一种叫做薏苡的大籽亚洲谷物)。新几内亚未能发展出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野生原材料的明显缺乏:全球56种最大籽粒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没有一种原产于那里。
其次,新几内亚的动物群中完全没有可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现代新几内亚唯一的家畜——猪、鸡和狗,是在过去几千年内从东南亚经由印度尼西亚传入的。因此,虽然新几内亚低地居民从捕鱼中获取蛋白质,但新几内亚高地农民却遭受严重的蛋白质缺乏,因为提供他们大部分热量的主食作物(芋头和甘薯)蛋白质含量很低。例如,芋头的蛋白质含量仅为1%,比白米还要差得多,远低于肥沃月弯的小麦和豆类(蛋白质含量分别为8-14%和20-25%)。
新几内亚高地的儿童有高容量但蛋白质缺乏饮食所特有的腹部肿胀现象。无论老少,新几内亚人经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其他地方能获得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的人们不会费心去吃这些。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传统新几内亚高地社会普遍存在食人现象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以前,新几内亚可用的根茎作物不仅在蛋白质方面有限,在热量方面也有限,因为它们在今天许多新几内亚人居住的高海拔地区生长不良。然而,几个世纪前,一种最初源自南美洲的新根茎作物——甘薯,传到了新几内亚,可能是经由菲律宾,西班牙人将其引入那里。与芋头和其他可能更古老的新几内亚根茎作物相比,甘薯可以在更高海拔地区种植,生长更快,每英亩耕地和每小时劳动的产量也更高。甘薯到来的结果是高地人口激增。也就是说,尽管人们在甘薯引入之前已经在新几内亚高地从事农业数千年,但当地可用的作物限制了他们能达到的人口密度,以及他们能占据的海拔高度。
简而言之,新几内亚为肥沃月弯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对比。与肥沃月弯的狩猎采集者一样,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者确实独立发展出了粮食生产。然而,他们的本土粮食生产受到当地缺乏可驯化谷物、豆类和动物的限制,受到由此导致的高地蛋白质缺乏的限制,以及当地可用根茎作物在高海拔地区的局限性的限制。然而,新几内亚人自己对他们可获得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的了解程度,不亚于当今地球上的任何民族。可以预期,他们已经发现并测试了任何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他们完全有能力识别有用的新增作物,这一点从他们在甘薯到来时热情采用就可以看出。同样的教训今天在新几内亚再次得到验证,那些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牲畜(或在文化上愿意采用它们)的部落,正在以牺牲那些没有这种获取途径或意愿的部落为代价而扩张。因此,新几内亚本土粮食生产的限制与新几内亚人民无关,而完全与新几内亚的生物群系和环境有关。
我们另一个本土农业明显受当地植物群限制的例子来自美国东部。与新几内亚一样,该地区支持对当地野生植物的独立驯化。然而,美国东部的早期发展比新几内亚要清楚得多:最早农民种植的作物已被确定,当地驯化的日期和作物序列也已知晓。在其他作物从别处传入之前,美洲原住民就定居在美国东部的河谷,并基于当地作物发展出了集约化粮食生产。因此,他们处于可以利用最有前途的野生植物的位置。他们实际上种植了哪些植物?由此产生的当地作物组合与肥沃月弯的创始作物组合相比如何?
事实证明,美国东部的创始作物是在公元前2500-1500年期间驯化的四种植物,比肥沃月弯的小麦和大麦驯化晚了整整6000年。一种当地的南瓜品种提供了小容器,并产出可食用的种子。其余三种创始作物仅为其可食用的种子而种植(向日葵、一种叫做藜的菊科植物近缘种,以及一种叫做藜属植物的菠菜远缘亲属)。
但四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植物远远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粮食生产体系(food production package)。在2000年里,这些奠基作物(founder crops)仅作为次要的膳食补充,而美国东部的原住民继续主要依赖野生食物,特别是野生哺乳动物和水禽、鱼类、贝类和坚果。直到公元前500-200年期间,又有三种种子作物(胡枝子、五月草和小麦草)被驯化之后,农业才开始在他们的饮食中占据主要地位。
现代营养学家会赞赏美国东部这七种作物。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17-32%,而小麦为8-14%,玉米为9%,大麦和白米甚至更低。其中两种作物——向日葵和豕草,油脂含量也很高(45-47%)。豕草尤其会成为营养学家的终极梦想,因为它含有32%的蛋白质和45%的油脂。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再食用这些梦幻食物了呢?
可惜的是,尽管有营养优势,这些美国东部作物在其他方面存在严重劣势。藜、胡枝子、小麦草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大麦种子的十分之一。更糟糕的是,豕草是豚草的风媒传粉近亲,而豚草是臭名昭著的花粉热致病植物。和豚草一样,豕草的花粉在大量生长时会引起花粉热。如果这还不足以打消你成为豕草种植者的热情,那么你要知道它有一种令某些人反感的强烈气味,而且处理它会引起皮肤刺激。
墨西哥作物最终在公元1年后通过贸易路线开始进入美国东部。玉米大约在公元200年到达,但在许多世纪里它的作用一直很次要。最后,在公元900年左右出现了一种适应北美短夏季的新玉米品种,而大约在公元1100年豆类的到来完成了墨西哥的作物三合一(trinity)——玉米、豆类和南瓜。美国东部的农业大大加强,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沿岸发展出人口稠密的酋邦。在一些地区,原有的本地驯化作物与生产力高得多的墨西哥三合一一起保留下来,但在其他地区,三合一完全取代了它们。没有欧洲人见过豕草生长在印第安人的花园里,因为在欧洲殖民美洲开始时(公元1492年),它作为作物已经消失了。在所有这些古老的美国东部特色作物中,只有两种(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与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竞争,并且至今仍在种植。我们现代的橡子南瓜和夏南瓜就源自数千年前驯化的美国南瓜。
因此,与新几内亚的情况一样,美国东部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先验地看,这个地区似乎很可能支持高产的本土农业。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可靠的适度降雨,以及今天维持丰富农业的适宜气候。其植物区系物种丰富,包括多产的野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当地的原住民确实发展了基于本地驯化作物的农业,确实在村庄中养活了自己,甚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左右发展出了文化繁荣期(霍普韦尔文化,中心位于今天的俄亥俄州)。因此,他们有几千年的时间来开发最有用的可用野生植物作为潜在作物,无论这些植物应该是什么。
然而,霍普韦尔繁荣期在肥沃月牙地带村庄生活兴起近9000年后才出现。尽管如此,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作物三合一的组合才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人口繁荣,即所谓的密西西比繁荣期,产生了墨西哥以北美洲原住民所达到的最大城镇和最复杂的社会。但这次繁荣来得太晚,无法让美国的原住民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殖民灾难做好准备。仅基于美国东部作物的粮食生产不足以引发这次繁荣,原因很容易具体说明。该地区可用的野生谷物远不如小麦和大麦有用。美国东部的原住民没有驯化任何本地可用的野生豆类、纤维作物、水果或坚果树。除了可能在美洲其他地方驯化的狗之外,他们根本没有驯化任何动物。
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东部的原住民并没有忽视他们周围野生物种中的潜在主要作物。即使是20世纪的植物育种家,拥有现代科学的全部力量,在开发北美野生植物方面也收效甚微。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将山核桃驯化为坚果树,将蓝莓驯化为水果,并且通过将一些欧亚水果作物(苹果、李子、葡萄、覆盆子、黑莓、草莓)与北美野生近缘种杂交来改良它们。然而,这些少数成功对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远不如公元900年后墨西哥玉米对美国东部原住民饮食习惯的改变那样深远。
对东部美国驯化作物最了解的当地原住民,在墨西哥三大作物到来时,通过放弃或减少种植本地作物的方式,对这些作物做出了评判。这一结果也表明,原住民并不受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他们完全能够识别好的植物。因此,如同在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本土粮食生产的局限性并非源于原住民本身,而完全取决于美洲的生物群和环境。
我们现在已经考察了三个对比鲜明地区的例子,在这些地区粮食生产都是本土产生的。肥沃月湾处于一个极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则处于另一个极端。肥沃月湾的人们更早地驯化了当地植物。他们驯化了更多的物种,驯化了生产力更高或更有价值的物种,驯化了范围更广的作物类型,更快地发展了集约化粮食生产和密集的人口,因此以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政治组织和更多的流行病进入现代世界,并用这些流行病感染其他民族。
我们发现,肥沃月湾、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之间的这些差异,直接源于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不同组合,而非这些民族本身的局限性。当来自其他地方的高产作物到来时(新几内亚的红薯、美国东部的墨西哥三大作物),当地人民迅速利用它们,强化粮食生产,人口大幅增长。推而广之,我认为那些完全没有本土发展出粮食生产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西欧等——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方面,可能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提供的更少,后两者至少产生了有限的粮食生产。实际上,Mark Blumler在本章提到的关于当地可获得的大种子野生禾本植物的全球调查,以及下一章将介绍的关于当地可获得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全球调查,一致表明所有这些本土粮食生产不存在或有限的地区,在可驯化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方面都存在不足。
回想一下,粮食生产的兴起涉及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之间的竞争。因此人们可能会想,所有这些粮食生产缓慢或不存在的案例,是否可能是由于当地用于狩猎和采集的资源异常丰富,而不是由于适合驯化的物种异常可得。事实上,本土粮食生产出现较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的大多数地区,为狩猎采集者提供的资源异常贫乏而非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非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在冰河时代末期已经灭绝。在这些地区,粮食生产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甚至比肥沃月湾还要少。因此,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失败或局限性不能归因于丰富狩猎机会的竞争。
为避免这些结论被误解,我们应该在本章结尾对两点加以警告,以免夸大:人们接受更好作物和牲畜的准备程度,以及当地可获得的野生动植物所施加的限制。这种准备程度和限制都不是绝对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当地人民采用在其他地方驯化的高产作物的例子。我们的广泛结论是,人们能够识别有用的植物,因此如果存在更好的适合驯化的当地植物,他们可能会认出来,并且不会因文化保守主义或禁忌而受阻。但必须为这句话添加一个重要限定:“从长远来看,在大范围内。”任何了解人类社会的人都可以举出无数社会拒绝本可提高生产力的作物、牲畜和其他创新的例子。
当然,我不赞同这样一个明显的谬论:每个社会都会迅速采用对其有用的每一项创新。事实是,在包含数百个相互竞争的社会的整个大陆和其他大片地区,一些社会会更开放地接受创新,而另一些则更抵制。那些确实采用新作物、牲畜或技术的社会,可能因此能够更好地养活自己,并在繁衍、迁移、征服或消灭抵制创新的社会方面胜出。这是一个重要现象,其表现远远超出采用新作物的范围,我们将在第13章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的另一个警告涉及当地可获得的野生物种对粮食生产兴起设置的限制。我并不是说,在所有那些到现代为止实际上还没有本土产生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在任何时间范围内都永远不可能出现。今天注意到澳大利亚原住民以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身份进入现代世界的欧洲人,常常假设原住民会永远这样下去。
为了理解这个谬误,让我们设想一位来自外太空的访客在公元前3000年降落到地球。这位外星人会观察到美国东部没有粮食生产,因为那里的粮食生产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才开始。如果这位公元前3000年的访客得出结论说,美国东部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所带来的限制永远排除了那里进行粮食生产的可能性,那么随后一千年的事件将证明这位访客错了。即使是在公元前9500年而不是公元前8500年访问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访客,也可能被误导,认为新月沃地永久不适合粮食生产。
也就是说,我的论点并不是说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欧以及所有其他没有本土粮食生产的地区缺乏可驯化的物种,如果没有外来的驯化物种或民族到来,这些地区将会无限期地仅由狩猎采集者占据。相反,我指出各地区在可驯化物种的可用储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在当地粮食生产开始的日期上也相应有所不同,而且截至现代,一些肥沃地区尚未独立产生粮食生产。
澳大利亚,据说是最”落后”的大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也就是大陆上最适合粮食生产的水源充足地区,近几千年来原住民(Aboriginal)社会似乎一直在沿着一条最终会导致本土粮食生产的轨迹演化。他们已经建造了冬季村落。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建造鱼陷阱、渔网甚至长运河来集约化管理环境以进行鱼类生产。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殖民澳大利亚并中止那条独立的轨迹,澳大利亚原住民可能在几千年内就会成为粮食生产者,照料驯化鱼类的池塘,种植驯化的澳大利亚山药和小粒草本植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章标题中隐含的问题了。我问的是,北美印第安人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原因是在于印第安人还是在于苹果。
我并不是说苹果在北美永远不可能被驯化。回想一下,从历史上看,苹果是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也是欧亚大陆最后被驯化的主要果树之一,因为它们的繁殖需要困难的嫁接(grafting)技术。即使在新月沃地和欧洲,直到古希腊时期,也就是欧亚粮食生产开始兴起8000年之后,才有大规模栽培苹果的证据。如果美洲原住民以同样的速度发明或获得嫁接技术,他们最终也会驯化苹果——大约在公元5500年左右,也就是北美驯化兴起(公元前2500年左右)之后约8000年。
因此,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也不在于苹果。就苹果驯化的生物学先决条件而言,北美印第安农民与欧亚农民相似,北美野生苹果也与欧亚野生苹果相似。实际上,本章读者现在在超市购买的一些苹果品种,就是最近通过欧亚苹果与北美野生苹果杂交培育出来的。相反,美洲原住民没有驯化苹果的原因在于可供美洲原住民利用的全套野生植物和动物物种。这套物种适度的驯化潜力导致了北美粮食生产的晚期起步。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相似的;每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都有其不可驯化的独特原因。
如果你觉得以前读过类似的东西,你是对的。只需做一些改动,你就会得到托尔斯泰伟大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著名开篇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其不幸的独特原因。”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获得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取得成功:性吸引、金钱观念的一致、子女管教、宗教信仰、姻亲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即使婚姻具备了幸福所需的所有其他要素,在任何一个关键方面的失败都可能毁掉这段婚姻。
这个原则可以扩展到理解婚姻之外的许多其他生活问题。我们倾向于寻求简单的单因素成功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要的事情,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可能导致失败的独立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解释了动物驯化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即许多看似适合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物种,如斑马和野猪,从未被驯化,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全部来自欧亚大陆。在前两章讨论了为什么这么多看似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从未被驯化之后,我们现在要处理家养哺乳动物的相应问题。我们之前关于苹果或印第安人的问题变成了关于斑马或非洲人的问题。
在第四章中,我们回顾了大型家养哺乳动物对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诸多方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提供了肉类、奶制品、肥料、陆地运输、皮革、军事突击工具、犁的牵引力和羊毛,以及杀死以前未接触过的人群的病菌。
此外,当然,小型家养哺乳动物以及家养鸟类和昆虫对人类也很有用。许多鸟类被驯化用于获取肉类、蛋类和羽毛:中国的鸡、欧亚大陆部分地区的各种鸭和鹅、中美洲的火鸡、非洲的珍珠鸡,以及南美洲的麝香鸭。狼在欧亚大陆和北美被驯化成为我们的狗,用作狩猎伙伴、哨兵、宠物,在某些社会中还作为食物。被驯化作为食物的啮齿动物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欧洲的兔子、安第斯山脉的豚鼠、西非的巨鼠,以及可能在加勒比岛屿上被驯化的一种叫做硬毛鼠的啮齿动物。雪貂在欧洲被驯化用于猎兔,猫在北非和西南亚被驯化用于捕猎啮齿类害虫。在19世纪和20世纪才被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为毛皮而饲养的狐狸、水貂和龙猫,以及作为宠物饲养的仓鼠。甚至一些昆虫也被驯化了,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蜜蜂和中国的桑蚕蛾,分别用于蜂蜜和丝绸。
这些小动物因此提供了食物、衣物或温暖。但它们都不能拉犁或拉车,都不能载人,除了狗以外都不能拉雪橇或成为战争机器,而且它们作为食物的重要性都不及大型家养哺乳动物。因此,本章的其余部分将仅限于讨论大型哺乳动物。
驯化哺乳动物的重要性依赖于数量惊人地少的大型陆生食草动物物种。(只有陆生哺乳动物被驯化了,原因很明显,水生哺乳动物在现代海洋世界设施发展之前很难维持和繁殖。)如果将”大型”定义为”体重超过100磅”,那么在20世纪之前只有14个这样的物种被驯化(见表9.1的列表)。在这古老的14种中,有9种(“次要九种”,见表9.1)仅在全球有限的地区成为人们的重要牲畜:阿拉伯骆驼、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同一祖先物种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白肢野牛。只有5个物种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普遍和重要。这五大哺乳动物驯化物种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这个清单乍一看似乎有明显的遗漏。汉尼拔的军队用来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非洲象呢?今天在东南亚仍被用作役畜的亚洲象呢?不,我没有忘记它们,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大象被驯服过,但从未被驯化过。汉尼拔的大象过去是,亚洲役用象现在是,只是被捕获和驯服的野生大象;它们不是在圈养中繁殖的。相比之下,驯化动物被定义为在圈养中选择性繁殖,从而与其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供控制动物繁殖和食物供应的人类使用的动物。
也就是说,驯化涉及将野生动物转变为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各方面都与它们的野生祖先不同。这些差异源于两个过程:人类选择那些比同一物种的其他个体对人类更有用的个体动物,以及动物对人类环境中运作的自然选择力量的自动进化响应,相比于野生环境。我们在第7章已经看到,所有这些陈述也适用于植物驯化。
驯化动物与其野生祖先的差异包括以下方面。许多物种的体型发生了变化:牛、猪和绵羊在驯化过程中变小了,而豚鼠变大了。绵羊和羊驼被选择以保留羊毛并减少或失去毛发,而牛则被选择以获得高产奶量。几种家养动物的大脑和感觉器官比它们的野生祖先更小、更不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祖先依赖的更大大脑和更发达的感觉器官来逃避野生捕食者。
表9.1 古老的十四种大型食草家养哺乳动物
绵羊。野生祖先:西亚和中亚的亚洲盘羊。现在遍布全球。
山羊。野生祖先:西亚的野山羊。现已遍布全球。
牛。野生祖先:现已灭绝的原牛(aurochs),曾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非。现已遍布全球。
猪。野生祖先:野猪,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非。现已遍布全球。实际上是杂食动物(经常食用动植物食物),而古代十四种中的其他13种则更严格地属于食草动物。
马。野生祖先:现已灭绝的俄罗斯南部野马;同一物种的不同亚种以蒙古的普氏野马(Przewalski’s horse)的形式存活到现代。现已遍布全球。
次要九种
阿拉伯(单峰)骆驼。野生祖先:现已灭绝,曾生活在阿拉伯及邻近地区。仍主要局限于阿拉伯和北非,但在澳大利亚有野化种群。
双峰驼。野生祖先:现已灭绝,生活在中亚。仍主要局限于中亚。
美洲驼和羊驼。这些似乎是同一物种的明显分化品种,而非不同物种。野生祖先:安第斯山脉的原驼。仍主要局限于安第斯山脉,虽然在北美也有一些作为驮畜饲养。
驴。野生祖先:北非的非洲野驴,可能曾在西南亚邻近地区存在。最初作为家畜仅限于北非和欧亚大陆西部,最近也在其他地方使用。
驯鹿。野生祖先:欧亚大陆北部的驯鹿。作为家畜仍主要局限于该地区,虽然现在阿拉斯加也有一些使用。
水牛。野生祖先生活在东南亚。作为家畜仍主要在该地区使用,虽然许多也在巴西使用,还有一些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逃逸到野外。
牦牛。野生祖先: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野牦牛。作为家畜仍局限于该地区。
巴厘牛。野生祖先:东南亚的爪哇野牛(banteng)(原牛的近亲)。作为家畜仍局限于该地区。
大额牛。野生祖先:印度和缅甸的白肢野牛(gaur)(原牛的另一近亲)。作为家畜仍局限于该地区。
要理解驯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只需比较狼(家犬的野生祖先)与众多犬种。一些狗比狼大得多(大丹犬),而另一些则小得多(北京犬)。一些更纤细,适合赛跑(灵缇犬),而另一些则腿短,不适合赛跑(腊肠犬)。它们的毛发形态和颜色差异巨大,有些甚至无毛。波利尼西亚人和阿兹特克人培育了专门用于食用的犬种。比较腊肠犬和狼,如果你事先不知道,你甚至不会怀疑前者是由后者演化而来的。
古代十四种的野生祖先在全球分布不均。南美洲只有一个这样的祖先,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根本没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本土家养哺乳动物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今天游客访问非洲的主要原因就是观赏其丰富多样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古代十四种中13种的野生祖先(包括主要五种的全部)都局限于欧亚大陆。(如本书其他地方,我使用”欧亚大陆”一词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北非,从生物地理学角度以及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来看,北非与欧亚大陆的联系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更紧密。)
当然,这13个野生祖先物种并非在整个欧亚大陆一起出现。没有任何地区拥有全部13种,并且一些野生祖先相当局限于特定地区,例如牦牛,在野生状态下仅限于西藏和邻近高原地区。然而,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确实有相当多的这13个物种生活在同一地区:例如,西南亚就有七个野生祖先物种。
野生祖先物种在各大陆之间的这种极不均衡分布,成为欧亚人而非其他大陆人民最终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重要原因。我们如何解释古代十四种在欧亚大陆的集中?
表9.2 可驯化的哺乳动物候选物种
| 欧亚大陆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美洲 | 澳大利亚 | |
|---|---|---|---|---|
| 候选物种 | 72 | 51 | 24 | 1 |
| 已驯化物种 | 13 | 0 | 1 | 0 |
| 候选物种驯化百分比 | 18% | 0% | 4% | 0% |
“候选物种”被定义为平均体重超过100磅的陆生、草食性或杂食性野生哺乳动物。
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欧亚大陆拥有最多的大型陆生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无论它们是否成为驯化物种的祖先。让我们将”驯化候选物种”定义为任何平均体重超过100磅(45公斤)的陆生草食性或杂食性哺乳动物(不以肉食为主的物种)。表9.2显示,欧亚大陆拥有最多的候选物种,共72个物种,正如它在许多其他植物和动物类群中也拥有最多物种一样。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板块,而且生态多样性极高,栖息地从广阔的热带雨林、温带森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苔原带。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候选物种较少,有51个物种,正如它在大多数其他植物和动物类群中的物种也较少一样——因为它比欧亚大陆更小,生态多样性也更低。非洲的热带雨林面积小于东南亚,而且在纬度37度以外完全没有温带栖息地。正如我在第1章中讨论的,美洲以前可能拥有几乎与非洲一样多的候选物种,但美洲大部分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包括马、大部分骆驼和其他如果幸存下来很可能被驯化的物种)在大约13,000年前灭绝了。澳大利亚作为最小和最孤立的大陆,一直拥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物种远少于欧亚大陆、非洲或美洲。正如美洲一样,在澳大利亚,除了红袋鼠之外,所有这些少数候选物种都在人类首次殖民该大陆时灭绝了。
因此,欧亚大陆成为大型哺乳动物驯化主要地点的部分原因是,它是一开始就拥有最多野生哺乳动物候选物种的大陆,而且在过去40,000年中失去的候选物种最少。但表9.2中的数字提醒我们,这并不是全部解释。同样真实的是,实际被驯化的候选物种百分比在欧亚大陆最高(1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则特别低(51个候选物种中没有一个被驯化!)。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大量非洲和美洲哺乳动物物种从未被驯化,尽管它们有欧亚大陆的近缘种或对应物种被驯化了。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马被驯化了,而非洲的斑马却没有?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猪,而不是美洲的西猯或非洲的三种真正野猪?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五种野牛(原牛、水牛、牦牛、白肢野牛、爪哇野牛),而不是非洲水牛或美洲野牛?为什么是亚洲摩弗伦绵羊(我们家养绵羊的祖先),而不是北美大角羊?
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这些民族,尽管他们极其多样化,是否都存在一些欧亚民族所没有的驯化文化障碍?例如,非洲丰富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资源,可以通过狩猎获取,是否使非洲人不必费力饲养家畜?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不是!这种解释被五类证据所反驳:非欧亚民族快速接受欧亚驯化动物、人类普遍的养宠物倾向、古代十四种动物的快速驯化、其中一些动物的反复独立驯化,以及现代进一步驯化努力的有限成功。
首先,当欧亚大陆的主要五种家畜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时,它们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被最多样化的非洲民族所采用。这些非洲牧民因此获得了相对于非洲狩猎采集者的巨大优势,并迅速取代了他们。特别是获得了牛和羊的班图农民从他们在西非的家园扩散出来,在短时间内占领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取代了以前的狩猎采集者。即使没有获得农作物,大约2,000年前获得了牛和羊的科伊桑人也在南非大部分地区取代了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家马进入西非改变了那里的战争方式,将该地区变成了一系列依赖骑兵的王国。唯一阻止马匹向西非以外传播的因素是采采蝇携带的锥虫病。
同样的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重复出现,每当缺乏适合驯化的本土野生哺乳动物物种的民族最终有机会获得欧亚家畜时。欧洲马匹被南北美洲的美洲原住民热切采用,在马匹从欧洲定居点逃脱后的一代人时间内就实现了。例如,19世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以熟练的骑马战士和野牛猎人而闻名,但他们直到17世纪末才获得马匹。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的绵羊同样改变了纳瓦霍印第安人的社会,并导致了纳瓦霍人因之闻名的精美羊毛毯子的编织等成果。在欧洲人带着狗定居塔斯马尼亚的十年内,以前从未见过狗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开始大量繁殖狗用于狩猎。因此,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数千个文化多样的土著民族中,没有普遍的文化禁忌阻碍动物驯化。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大陆上的某些本地野生哺乳动物物种可以被驯化,那么一些澳大利亚人、美洲人和非洲人本应该驯化它们并从中获得巨大优势,就像他们从欧亚大陆家畜中受益一样——当这些动物出现时,他们立即接受了它们。例如,考虑生活在野生斑马和水牛分布范围内的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为什么至少没有一个非洲狩猎采集部落驯化这些斑马和水牛,从而在欧亚马和牛到来之前就统治其他非洲人?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欧亚大陆以外缺乏本地哺乳动物驯化的原因在于当地可获得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当地人民。
第二类支持同样解释的证据来自宠物。饲养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并驯服它们,构成了驯化的初始阶段。但几乎所有大陆上的所有传统人类社会都有饲养宠物的报告。被如此驯服的野生动物种类远多于最终被驯化的种类,其中包括一些我们难以想象作为宠物的物种。
例如,在我工作的新几内亚村庄,我经常看到人们养袋鼠、负鼠和各种鸟类作为宠物,从捕蝇鸟到鱼鹰。这些捕获的动物大多最终被吃掉,但有些只是作为宠物饲养。新几内亚人甚至定期捕捉野生食火鸡(一种类似鸵鸟的大型不会飞的鸟)的雏鸟,养大后作为美味食用——尽管圈养的成年食火鸡极其危险,时不时会使村民开膛破肚。一些亚洲民族驯服老鹰用于狩猎,尽管这些强大的宠物偶尔也会杀死它们的人类驯养者。古埃及人和亚述人以及现代印度人驯服猎豹用于狩猎。古埃及人的绘画显示,他们还驯服了(不足为奇)瞪羚和角马等有蹄哺乳动物、鹤等鸟类、更令人惊讶的长颈鹿(可能很危险),以及最令人惊讶的鬣狗。尽管明显危险,非洲象在罗马时代被驯服,亚洲象今天仍在被驯服。也许最不可能的宠物是欧洲棕熊(与美洲灰熊是同一物种),日本阿伊努人定期捕捉幼熊,驯养它们,然后在仪式典礼中杀死并食用。
因此,许多野生动物物种达到了通往驯化的动物-人类关系序列的第一阶段,但只有少数从该序列的另一端成为家畜。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差异:“看起来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过被驯化的机会,(少数)……很久以前就被驯化了,但大多数失败者,有时只在一个小细节上失败,注定永远保持野性。”
驯化日期提供了第三条证据线,证实了高尔顿的观点,即早期畜牧民族迅速驯化了所有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所有我们有考古证据的驯化日期的物种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被驯化的——也就是说,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出现的定居农牧社会的最初几千年内。如表9.3所总结的,大型哺乳动物驯化时代始于绵羊、山羊和猪,终于骆驼。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没有重要的新增。
当然,确实有些小型哺乳动物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才首次被驯化。例如,兔子直到中世纪才被驯化作为食物,小鼠和大鼠直到20世纪才被驯化用于实验室研究,仓鼠直到1930年代才被驯化作为宠物。驯化小型哺乳动物的持续发展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有数千种野生物种作为候选,而且它们对传统社会的价值太小,不值得花费精力饲养。但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实际上在4500年前就结束了。到那时,世界上所有148种候选大型物种肯定已经过无数次测试,结果只有少数通过了测试,没有其他合适的物种了。
第四条证据表明某些哺乳动物物种比其他物种更适合驯化,这来自同一物种的重复独立驯化。基于我们遗传物质中称为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部分的遗传证据最近证实了长期以来的怀疑,印度的有峰驼牛和欧洲无峰牛源自两个独立的野生祖先牛种群,这些种群在数十万年前就已分化。也就是说,印度人驯化了当地印度亚种的野生原牛,西南亚人独立驯化了他们自己的西南亚原牛亚种,北非人可能独立驯化了北非原牛。
同样,狼在美洲被独立驯化成狗,可能在欧亚大陆的几个不同地区也是如此,包括中国和西南亚。现代猪源自中国、西欧亚和可能其他地区的独立驯化序列。这些例子再次强调,同样少数几种合适的野生物种吸引了许多不同人类社会的注意。
现代驯化努力的失败提供了最后一类证据,证明过去未能驯化大量野生候选物种是由于这些物种本身的缺陷,而不是古代人类的不足。今天的欧洲人是地球上最悠久的动物驯化传统之一的继承者——这一传统始于约10,000年前的西南亚。自15世纪以来,欧洲人遍布全球,遇到了欧洲没有的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欧洲定居者,比如我在新几内亚遇到的那些养着宠物袋鼠和负鼠的人,已经驯服或把许多当地哺乳动物当作宠物,就像土著人民一样。移居到其他大陆的欧洲牧民和农民也认真尝试驯化一些当地物种。
| 物种 | 日期(公元前) | 地点 |
|---|---|---|
| 狗 | 10,000 | 西南亚、中国、北美 |
| 绵羊 | 8,000 | 西南亚 |
| 山羊 | 8,000 | 西南亚 |
| 猪 | 8,000 | 中国、西南亚 |
| 牛 | 6,000 | 西南亚、印度、(?)北非 |
| 马 | 4,000 | 乌克兰 |
| 驴 | 4,000 | 埃及 |
| 水牛 | 4,000 | 中国? |
| 美洲驼/羊驼 | 3,500 | 安第斯山脉 |
| 双峰驼 | 2,500 | 中亚 |
| 单峰驼 | 2,500 | 阿拉伯 |
对于其他四种已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驯鹿、牦牛、白肢野牛(gaur)和爪哇野牛(banteng)——目前关于驯化日期的证据还很少。所示的日期和地点仅仅是迄今为止确证的最早的;驯化实际上可能更早开始,并且在不同的地点。
在19世纪和20世纪,至少有六种大型哺乳动物——大羚羊(eland)、麋鹿(elk)、驼鹿(moose)、麝牛(musk ox)、斑马和美洲野牛——成为特别有组织的驯化项目的对象,由现代科学动物育种者和遗传学家执行。例如,大羚羊——非洲最大的羚羊——一直在乌克兰的阿斯卡尼亚-诺瓦动物园以及英格兰、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肉质和产奶量的选育;苏格兰阿伯丁的罗维特研究所(Rowett Research Institute)经营了一个麋鹿(英国术语中的红鹿)实验农场;俄罗斯的佩乔拉-伊雷奇国家公园(Pechero-Ilych National Park)经营了一个驼鹿实验农场。然而,这些现代努力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虽然野牛肉偶尔出现在一些美国超市,虽然驼鹿在瑞典和俄罗斯被骑乘、挤奶并用来拉雪橇,但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足够的经济价值来吸引许多牧场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在非洲本土驯化大羚羊的尝试——在那里它的抗病性和气候耐受性会给它带来比易受非洲疾病影响的引进欧亚野生种群更大的优势——并没有流行起来。
因此,无论是数千年来接触候选物种的土著牧民,还是现代遗传学家,都没有成功地从大型哺乳动物中培育出古代十四种(Ancient Fourteen)之外的有用驯化动物,而古代十四种最迟在4,500年前就已被驯化。然而,如果科学家今天愿意的话,无疑可以为许多物种实现驯化定义中关于控制繁殖和食物供应的那部分。例如,圣地亚哥动物园和洛杉矶动物园现在正在对最后幸存的加州秃鹫(California condors)实施比任何驯化物种更严格的繁殖控制。所有个体秃鹫都已进行了遗传鉴定,一个计算机程序决定哪只雄性应该与哪只雌性交配,以实现人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大化遗传多样性从而保护这种濒危鸟类)。动物园正在为许多其他受威胁物种进行类似的繁育计划,包括大猩猩和犀牛。但动物园对加州秃鹫的严格选育并没有产生经济上有用产品的前景。动物园在犀牛方面的努力也是如此,尽管犀牛提供了超过三吨的肉。正如我们现在将看到的,犀牛(以及大多数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对驯化提出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总共,在世界上148种大型野生陆生草食哺乳动物——驯化的候选者——中,只有14种通过了测试。为什么其他134种失败了?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谈到那些”注定永远野生”的其他物种时,指的是哪些条件?
答案来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要被驯化,候选野生物种必须具备许多不同的特征。缺少任何一项必需特征都会导致驯化努力失败,就像它会导致建立幸福婚姻的努力失败一样。作为斑马/人类配对和其他不匹配配对的婚姻顾问,我们可以认识到至少六组驯化失败的原因。
每次动物吃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化为消费者生物量的效率远低于100%:通常约为10%。也就是说,需要大约10,000磅玉米才能养出一头1,000磅的牛。如果你想养出1,000磅的肉食动物,你必须用100,000磅玉米养出的10,000磅食草动物来喂养它。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许多物种(如考拉)在植物选择上过于挑剔,不适合作为农场动物。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低效率,没有哺乳类肉食动物被驯化用于食用。(不,这不是因为它们的肉质坚韧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肉食性野生鱼类,我个人可以证明狮子汉堡的美味。)最接近例外的是狗,最初被驯化作为哨兵和狩猎伙伴,但在阿兹特克墨西哥、波利尼西亚和古代中国培育和饲养狗品种作为食物。然而,定期吃狗肉一直是缺乏肉类的人类社会的最后手段:阿兹特克人没有其他家养哺乳动物,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人只有猪和狗。拥有家养食草哺乳动物的人类社会没有费心吃狗,除非作为不常见的美味(如今天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此外,狗不是严格的肉食动物而是杂食动物: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你心爱的宠物狗真的是肉食动物,只需阅读狗粮袋上的成分列表。阿兹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饲养的用于食用的狗是用蔬菜和垃圾高效育肥的。
为了值得饲养,家养动物还必须快速生长。这排除了大猩猩和大象,尽管它们是素食动物,具有令人钦佩的不挑食的食物偏好,并且代表大量肉类。哪个潜在的大猩猩或大象牧场主会等待15年让他的畜群达到成年体型?想要役用大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在野外捕获并驯服它们要便宜得多。
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他人注视下做爱;一些潜在有价值的动物物种也不喜欢。这就是几千年来驯化猎豹努力失败的原因,尽管我们有强烈的动机这样做,猎豹是所有陆地动物中最快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古埃及人、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珍视驯服的猎豹作为狩猎动物,远远优于狗。印度的一位莫卧儿皇帝养了一千只猎豹。但尽管许多富有的王子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在野外捕获的驯服猎豹。王子们在圈养中繁殖猎豹的努力失败了,直到1960年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实现了他们第一次成功的猎豹出生。在野外,几只猎豹兄弟会追逐一只雌性几天,这种长距离的粗暴求偶似乎是让雌性排卵或变得性感受的必要条件。猎豹通常拒绝在笼子里进行这种精心设计的求偶仪式。
类似的问题挫败了繁殖骆马(vicuña)的计划,骆马是一种安第斯野生骆驼,其羊毛被誉为所有动物中最好和最轻的。古代印加人通过将野生骆马赶入围栏、剪毛然后活着释放它们来获得骆马羊毛。想要这种奢侈羊毛的现代商人不得不采用同样的方法或者干脆杀死野生骆马。尽管有金钱和声望的强烈激励,所有在圈养中繁殖骆马以生产羊毛的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包括骆马在交配前漫长而精心设计的求偶仪式,这种仪式在圈养中受到抑制;雄性骆马彼此之间的激烈不容忍;以及它们对全年觅食领地和单独的全年睡眠领地的要求。
自然地,几乎任何足够大的哺乳动物物种都能够杀死人类。人们被猪、马、骆驼和牛杀死过。然而,一些大型动物的性情要凶恶得多,而且比其他动物更无可救药地危险。杀死人类的倾向使许多原本看似理想的驯化候选者丧失了资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味,灰熊重达1,700磅,它们主要是素食者(尽管也是强大的猎人),它们的素食饮食非常广泛,它们以人类垃圾为食(从而在黄石国家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大问题),而且它们生长相对较快。如果它们在圈养中表现良好,灰熊将是一种极好的肉类生产动物。日本的阿伊努人通过定期饲养灰熊幼崽作为仪式的一部分进行了实验。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认为在一岁时杀死并吃掉幼崽是明智的。饲养灰熊更长时间将是自杀性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成年灰熊被驯服过。
另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合适但因同样明显的原因而被淘汰的候选动物是非洲水牛。它能迅速成长到一吨重,并成群生活,群体内有完善的等级制度(dominance hierarchy),这一特性的优点将在下文讨论。但非洲水牛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最难以预测的大型哺乳动物。任何疯狂到试图驯化它的人要么在尝试中丧生,要么被迫在水牛长得太大、太凶之前将其杀死。同样,河马作为四吨重的食草动物,如果不是如此危险的话,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家畜。它们每年杀死的人数比任何其他非洲哺乳动物都多,甚至超过狮子。
很少有人会对这些臭名昭著的凶猛候选动物被淘汰感到惊讶。但还有其他一些候选动物,其危险性并不为人所知。例如,八种野生马科动物(equids)(马及其近亲)在性情上差异很大,尽管这八种动物在基因上如此接近,以至于它们可以杂交并产生健康的(尽管通常不育的)后代。其中两种,马和北非野驴(驴的祖先),被成功驯化了。与北非野驴关系密切的是亚洲野驴,也被称为中亚野驴(onager)。由于它的家园包括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西方文明和动物驯化的摇篮——古代人民一定对中亚野驴进行过广泛的驯化实验。我们从苏美尔人和后来的描绘中知道,中亚野驴经常被猎捕,也被捕获并与驴和马杂交。一些古代描绘的用于骑乘或拉车的类马动物可能指的就是中亚野驴。然而,从罗马人到现代动物园管理员,所有关于它们的记述都谴责它们暴躁的脾气和咬人的恶习。因此,尽管在其他方面与驴的祖先相似,中亚野驴从未被驯化。
非洲的四种斑马更糟糕。驯化的努力曾发展到用它们拉车的程度:19世纪的南非曾试图将它们用作役畜,古怪的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Walter Rothschild)曾驾驶着斑马拉的马车穿过伦敦街头。可惜,斑马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极其危险。(这并不否认许多个体马匹也很凶,但斑马和中亚野驴的凶性要一致得多。)斑马有咬人不松口的恶习。因此每年伤害美国动物园管理员的数量甚至超过老虎!斑马也几乎不可能用绳索套住——即使是那些在马术竞技中靠套马赢得冠军的牛仔也做不到——因为它们总能看着套索飞向自己,然后把头躲开。
因此,给斑马上鞍或骑乘几乎不可能(如果有的话也极少),南非人对驯化斑马的热情也消退了。大型潜在危险哺乳动物不可预测的攻击性行为,也是最初很有希望的现代驯化麋鹿和大羚羊(eland)实验未能取得更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易惊慌的倾向。大型草食性哺乳动物物种对来自捕食者或人类的危险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有些物种神经质、速度快,一旦察觉威胁就会立即逃跑。其他物种则较慢、不那么紧张,寻求群体保护,受到威胁时会坚守阵地,直到必要时才跑。大多数鹿和羚羊物种(驯鹿是明显的例外)属于前一种类型,而绵羊和山羊属于后一种。
自然,神经质的物种很难圈养。如果把它们放进围栏,它们可能会惊慌失措,要么因惊吓而死,要么在试图逃跑时撞围栏撞死。例如瞪羚就是如此,在新月沃地的某些地区,瞪羚数千年来一直是最常被猎捕的猎物物种。该地区最早的定居民族没有比瞪羚更有机会驯化的哺乳动物物种了。但没有任何一种瞪羚被驯化过。试想一下,要放牧一种会突然狂奔、盲目撞墙、能跳近30英尺高、能以每小时50英里速度奔跑的动物!
社会结构。几乎所有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其野生祖先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社会特征:它们群居;群体成员之间保持完善的等级制度;群体占据重叠的活动范围而非相互排斥的领地。例如,野马群由一匹种马、最多六匹母马及其幼驹组成。母马A支配母马B、C、D和E;母马B服从A但支配C、D和E;C服从B和A但支配D和E;依此类推。当马群迁移时,成员保持固定的顺序:种马在后;地位最高的母马在前,后面跟着她的幼驹,按年龄排序,最小的在最前;在她后面是其他母马,按等级排序,每匹母马后面跟着她的幼驹,按年龄排序。这样,许多成年个体可以在群体中共存,不会持续打斗,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等级。
这种社会结构是驯化的理想条件,因为人类实际上接管了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群居马匹会像跟随地位最高的雌性一样跟随人类领导者。羊群、山羊群、牛群和原始犬类(狼)有着相似的等级制度。当幼年动物在这样的群体中成长时,它们会对经常在附近看到的动物产生印记(imprint)。在野生条件下,这些是它们同种的成员,但圈养的幼年群居动物也会看到附近的人类,并同样对人类产生印记。
这样的社会性动物适合放牧。由于它们彼此容忍,可以被聚集在一起。由于它们本能地跟随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并且会将人类印记为该领导者,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牧羊人或牧羊犬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表现良好,因为它们习惯于在野外密集聚集的群体中生活。
相比之下,大多数独居领地性动物物种的成员无法被放牧。它们不能容忍彼此,不会对人类产生印记,也没有本能的服从性。谁见过一排猫(在野外独居且具有领地性)跟随人类或允许自己被人类放牧?每个爱猫人士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本能地服从人类。猫和雪貂是唯一被驯化的领地性哺乳动物物种,因为我们驯化它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将它们作为食物大规模饲养,而是将它们作为独居的捕猎者或宠物。
虽然大多数独居领地性物种因此没有被驯化,但反过来说,并非大多数群居物种都能被驯化。大多数不能,原因有几个。
首先,许多物种的群体没有重叠的活动范围,而是对其他群体保持排他性的领地。将两个这样的群体圈养在一起,就像将两只独居物种的雄性圈养在一起一样不可能。
其次,许多一年中部分时间群居的物种在繁殖季节具有领地性,它们会打斗,不能容忍彼此的存在。这适用于大多数鹿和羚羊物种(驯鹿除外),这也是非洲著名的所有社会性羚羊物种无法被驯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人们对非洲羚羊的第一印象是”延伸至地平线的庞大密集群体”,但实际上这些群体中的雄性在繁殖时会划分领地并激烈争斗。因此,这些羚羊无法像绵羊、山羊或牛那样在拥挤的圈养环境中饲养。领地行为同样与凶猛的性格和缓慢的生长速度相结合,将犀牛排除在农场之外。
最后,许多群居物种,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没有明确的支配等级,也没有本能地准备好对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产生印记(因此也就无法错误印记到人类身上)。结果,虽然许多鹿和羚羊物种已经被驯服(想想所有那些真实的小鹿斑比故事),但人们从未见过这些驯服的鹿和羚羊像绵羊一样成群被驱赶。这个问题也阻碍了北美大角羊的驯化,大角羊与亚洲盘羊(我们家养绵羊的祖先)属于同一属。大角羊在大多数方面都适合我们,也与盘羊相似,除了一个关键点:它们缺乏盘羊的刻板行为,即一些个体对其承认支配地位的其他个体表现出服从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最初,动物驯化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某些物种被驯化而其近亲却没有被驯化的看似任意性。事实证明,除了少数候选者外,所有候选者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Anna Karenina principle)淘汰了。人类和大多数动物物种构成不幸的婚姻,原因有很多:动物的饮食、生长速度、交配习性、性格、恐慌倾向以及社会组织的几个不同特征。只有一小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最终与人类建立了幸福的婚姻,因为它们在所有这些独立方面都具有兼容性。
欧亚大陆的人们恰好继承了比其他大陆的人们多得多的可驯化大型野生哺乳食草动物物种。这一结果及其对欧亚社会的所有重大优势,源于哺乳动物地理、历史和生物学的三个基本事实。首先,欧亚大陆因其广阔的面积和生态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候选物种。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但不包括欧亚大陆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的大规模灭绝浪潮中失去了大部分候选物种——可能是因为前者大陆的哺乳动物不幸在我们进化史上突然而晚地首次接触人类,那时我们的狩猎技能已经高度发达。最后,在欧亚大陆上,幸存候选物种中适合驯化的比例高于其他大陆。对从未被驯化的候选物种(如非洲的大型群居哺乳动物)的研究揭示了使它们每一个都不合格的特定原因。因此,托尔斯泰会认同另一位早期作者圣马太在另一个语境中提供的见解:“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在第10章的世界地图上(图10.1),比较各大陆的形状和方向。你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差异。美洲南北跨度(9000英里)远大于东西跨度:最宽处仅3000英里,在巴拿马地峡处窄至仅40英里。也就是说,美洲的主轴是南北走向的。非洲也是如此,尽管程度没那么极端。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是东西走向的。大陆主轴方向的这些差异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
本章将讨论我所看到的这些差异所带来的巨大且有时是悲剧性的后果。主轴方向影响了农作物和家畜的传播速度,也可能影响了文字、轮子和其他发明的传播。地理的这一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过去500年间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欧亚人的截然不同的经历。
粮食生产的传播对于理解枪炮、病菌和钢铁兴起中的地理差异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在前几章中考虑的粮食生产的起源一样。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全球范围内独立产生粮食生产的地区不超过九个,可能只有五个。然而,在史前时代,除了这几个起源地区之外,粮食生产已经在许多其他地区建立起来。所有这些其他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粮食生产,是由于农作物、家畜以及种植它们的知识的传播,在某些情况下,也是由于农民和牧民自身的迁徙。
粮食生产的主要传播路线包括:从西南亚传播到欧洲、埃及和北非、埃塞俄比亚、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从萨赫勒和西非传播到东非和南非;从中国传播到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美洲传播到北美。此外,即使在粮食生产的起源地区,也通过增加来自其他起源地区的农作物、家畜和技术而得到了丰富。
正如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合粮食生产的起源一样,粮食生产传播的难易程度在世界各地也大不相同。一些在生态上非常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史前时代根本没有获得粮食生产,尽管史前粮食生产地区就在附近。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和畜牧业都未能从美国西南部传播到美洲原住民的加利福尼亚,或从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传播到澳大利亚;以及农业未能从南非的纳塔尔省传播到南非的开普省。即使在所有那些粮食生产确实在史前时代传播的地区中,传播的速度和时间也有很大差异。一个极端是沿东西轴线的快速传播:从西南亚向西传播到欧洲和埃及,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平均速度约为每年0.7英里);以及从菲律宾向东传播到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另一个极端是沿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到美国西南部,速度不到每年0.5英里;玉米和豆类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才在美国东部具有生产力,速度不到每年0.3英里;以及骆马从秘鲁向北传播到厄瓜多尔,速度为每年0.2英里。如果玉米不是像我在这些计算中保守假设的那样,以及一些考古学家现在假设的那样,在公元前3500年才在墨西哥驯化,而是像大多数考古学家过去假设的(许多人仍然这样认为)那样更早驯化,那么这些差异可能会更大。
农作物和家畜传播的完整性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再次意味着它们传播的障碍有强有弱。例如,虽然西南亚的大部分原始农作物和家畜确实向西传播到欧洲,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但安第斯地区的两种家畜(骆马/羊驼和豚鼠)在前哥伦布时期从未到达中美洲。这种令人惊讶的失败亟待解释。毕竟,中美洲确实发展出了密集的农业人口和复杂的社会,所以毫无疑问,安第斯家畜(如果有的话)对于食物、运输和羊毛来说是有价值的。除了狗以外,中美洲完全没有本土哺乳动物来满足这些需求。然而,一些南美农作物确实成功到达了中美洲,如木薯、红薯和花生。什么样的选择性障碍让这些农作物通过,却筛掉了骆马和豚鼠?
这种地理上传播难易程度差异的一个更微妙的表现是被称为抢先驯化(preemptive domestication)的现象。我们的农作物所来源的大多数野生植物物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遗传差异,因为不同地区的野生祖先种群中建立了不同的突变。同样,将野生植物转变为农作物所需的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新突变或不同的选择过程来实现,以产生等效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检查一种在史前时代广泛存在的农作物,并询问其所有品种是否显示出相同的野生突变或相同的转化突变。这种检查的目的是试图弄清楚该农作物是仅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还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
如果对新世界主要的古代作物进行这样的遗传分析,其中许多作物被证明包含两个或更多这些可选的野生变种,或两个或更多这些可选的转化突变(transforming mutations)。这表明该作物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地区独立驯化,该作物的某些品种继承了一个地区的特定突变,而同一作物的其他品种则继承了另一个地区的突变。在此基础上,植物学家得出结论:利马豆(Phaseolus lunatus)、普通豆(Phaseolus vulgaris)和Capsicum annuum / chinense组的辣椒都至少在两个独立的场合被驯化,一次在中美洲,一次在南美洲;南瓜Cucurbita pepo和种子植物藜属(goosefoot)也至少独立驯化了两次,一次在中美洲,一次在美国东部。相比之下,大多数古代西南亚作物只表现出一种可选的野生变种或可选的转化突变,表明该特定作物的所有现代品种仅源自一次驯化。
如果同一种作物在其野生分布范围的几个不同地区被重复且独立地驯化,而不仅仅是在单一地区驯化一次,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看到,植物驯化涉及对野生植物的改造,使它们通过更大的种子、不那么苦的味道或其他特性而对人类更有用。因此,如果已经有了高产作物,早期农民肯定会继续种植它,而不是从头开始采集其尚未如此有用的野生近缘种并重新驯化它。因此,仅有一次驯化的证据表明,一旦野生植物被驯化,该作物就会迅速传播到整个野生植物分布范围内的其他地区,从而排除了对同一植物进行其他独立驯化的需要。然而,当我们发现同一野生祖先在不同地区独立驯化的证据时,我们推断该作物传播得太慢,无法阻止其在其他地方的驯化。西南亚以单次驯化为主,但美洲频繁出现多次驯化的证据,可能因此提供了更微妙的证据,表明作物从西南亚传播比在美洲更容易。
作物的快速传播可能不仅阻止同一野生祖先物种在其他地方的驯化,也可能阻止相关野生物种的驯化。如果你已经在种植好的豌豆,那么从头开始再次驯化同一野生祖先豌豆当然毫无意义,但驯化与已驯化豌豆物种对农民来说几乎等同的密切相关野生豌豆物种也毫无意义。西南亚所有的创始作物(founder crops)都阻止了其在整个欧亚大陆西部任何近缘种的驯化。相比之下,新世界呈现出许多等同且密切相关,但仍然不同的物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被驯化的情况。例如,当今世界种植的棉花95%属于棉花物种Gossypium hirsutum,它在史前时代在中美洲被驯化。然而,史前南美洲农民反而种植相关的棉花Gossypium barbadense。显然,中美洲棉花到达南美洲非常困难,以至于在史前时代未能阻止那里驯化不同的棉花物种(反之亦然)。辣椒、南瓜、苋菜(amaranths)和藜属(chenopods)是其他作物,其中不同但相关的物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被驯化,因为没有一个物种能够传播得足够快以阻止其他物种。
因此,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现象汇聚到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传播比在美洲更容易,也可能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容易。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适宜地区;其传播速度和选择性的差异;以及最早驯化作物是否阻止同一物种的再驯化或近缘种驯化的差异。美洲和非洲有什么特点使得粮食生产的传播比在欧亚大陆更困难?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考察粮食生产从西南亚(肥沃月牙地带)的快速传播。粮食生产在那里产生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之前,它的离心波出现在西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其他地区,距离肥沃月牙地带越来越远,向西和向东。在本页上,我重绘了遗传学家丹尼尔·佐哈里(Daniel Zohary)和植物学家玛丽亚·霍普夫(Maria Hopf)汇编的引人注目的地图(图10.2),其中他们说明了这一波浪如何在公元前6500年到达希腊、塞浦路斯和印度次大陆,公元前6000年后不久到达埃及,公元前5400年到达中欧,公元前5200年到达西班牙南部,公元前3500年左右到达英国。在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粮食生产都是由在肥沃月牙地带启动它的同一套驯化植物和动物中的一些开始的。此外,肥沃月牙地带的组合(package)在某个尚不确定的日期向南渗透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然而,埃塞俄比亚也培育了许多本土作物,我们还不知道是这些作物还是到达的肥沃月牙地带作物启动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生产。
当然,并非这个作物组合的所有部分都传播到了所有那些边远地区:例如,埃及太温暖,单粒小麦无法在那里生长。在一些边远地区,这个组合的各个元素在不同时间到达:比如在西南欧洲,绵羊先于谷物到达。一些边远地区继续驯化了一些自己的本地作物,如西欧的罂粟和可能是埃及的西瓜。但边远地区的大部分粮食生产最初都依赖于肥沃月湾的驯化作物。它们的传播很快就伴随着其他起源于肥沃月湾或其附近的创新的传播,包括轮子、文字、金属加工技术、挤奶、果树以及啤酒和葡萄酒的生产。
为什么同一个植物组合在整个西欧亚大陆启动了粮食生产?是因为同一组植物在许多地区的野外都有生长,在那里被发现有用,就像在肥沃月湾一样,并被独立驯化了吗?不,这不是原因。首先,肥沃月湾的许多奠基作物甚至在西南亚之外的野外根本不存在。例如,除了大麦之外,八种主要奠基作物中没有一种在埃及野生生长。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提供了一个与肥沃月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相似的环境。因此,在后者流域运作良好的作物组合在尼罗河流域也运作得足够好,从而触发了本土埃及文明的壮观崛起。但为这一壮观崛起提供食物的作物最初在埃及是不存在的。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是由以最初原产于肥沃月湾而非埃及的作物为食的人建造的。
其次,即使对于那些野生祖先确实存在于西南亚之外的作物,我们也可以确信,欧洲和印度的作物大多是从西南亚获得的,而不是本地驯化的。例如,野生亚麻向西分布到英国和阿尔及利亚,向东分布到里海,而野生大麦甚至向东分布到西藏。然而,对于肥沃月湾的大多数奠基作物,今天世界上所有栽培品种都只共享野生祖先中多种染色体排列中的一种;或者它们只共享一个单一的突变(在许多可能的突变中),通过这个突变,栽培品种在人类所需的特征上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例如,所有栽培豌豆都共享相同的隐性基因,这个基因防止成熟的栽培豌豆荚自发爆开并散出豌豆,就像野生豌豆荚所做的那样。
显然,肥沃月湾的大多数奠基作物在肥沃月湾首次驯化后,从未在其他地方被再次驯化。如果它们被反复独立驯化,它们就会以不同的染色体排列或不同的突变形式展现出那些多重起源的遗产。因此,这些是我们上面讨论的先发驯化(preemptive domestication)现象的典型例子。肥沃月湾作物组合的快速传播预先阻止了任何其他可能的尝试,无论是在肥沃月湾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去驯化相同的野生祖先。一旦作物变得可用,就不再需要从野外采集它,从而使它再次走上驯化之路。
大多数奠基作物的祖先都有野生近缘种,在肥沃月湾和其他地方,它们也适合驯化。例如,豌豆属于豌豆属(Pisum),该属由两个野生物种组成:Pisum sativum,即被驯化以产出我们的园豌豆的那种,以及Pisum fulvum,从未被驯化。然而,Pisum fulvum的野生豌豆味道不错,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干的,而且在野外很常见。同样,小麦、大麦、小扁豆、鹰嘴豆、豆类和亚麻除了被驯化的那些之外,都有许多野生近缘种。其中一些相关的豆类和大麦确实在美洲或中国被独立驯化,远离肥沃月湾的早期驯化地点。但在西欧亚大陆,几个可能有用的野生物种中只有一个被驯化了——可能是因为那一个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很快就停止采集其他野生近缘种,只吃这种作物。再次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这种作物的快速传播预先阻止了任何可能的进一步尝试去驯化其近缘种,以及重新驯化其祖先。
答案部分取决于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位于同一纬度上相互向东和向西分布的地区共享完全相同的日照时长及其季节性变化。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倾向于共享相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模式以及栖息地或生物群系(biomes)(植被类型)。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都位于大约相同的纬度,但相继向东或向西相距4000英里,它们彼此之间在气候上比各自与仅在正南方1000英里处的地点更相似。在所有大陆上,被称为热带雨林的栖息地类型仅限于赤道南北约10度纬度以内,而地中海灌木栖息地(如加利福尼亚的灌木丛和欧洲的马基群落)位于约30到40度纬度之间。
但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抗病性都精确地适应了这些气候特征。日照长度、温度和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构成了刺激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植株开花结果的信号。每个植物种群通过自然选择,在基因上被编程为对其进化所处的季节性模式的信号做出适当响应。这些模式随纬度变化很大。例如,赤道地区全年日照长度恒定,但在温带纬度,日照长度从冬至到夏至逐月增加,然后在一年的后半段再次减少。生长季节——即温度和日照长度适合植物生长的月份——在高纬度地区最短,向赤道方向逐渐延长。植物也适应了其所在纬度普遍存在的疾病。
如果植物的基因程序与其种植地的纬度不匹配,那就糟糕了!想象一下,一个加拿大农民愚蠢地种植了一种适应在更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品种。这株不幸的玉米植株按照其适应墨西哥的基因程序,会准备在三月份抽出嫩芽,结果却发现自己仍然埋在10英尺厚的雪下。即使这株植物的基因被重新编程,使其在更适合加拿大的时间——比如六月下旬——发芽,它仍然会因其他原因陷入困境。它的基因会告诉它以悠闲的速度生长,这种速度只足以让它在五个月内成熟。这在墨西哥温和的气候中是一个完全安全的策略,但在加拿大却是一个灾难性的策略,会保证植株在长出任何成熟玉米棒之前就被秋霜杀死。这株植物也会缺乏对北方气候疾病的抗性基因,却无用地携带着对南方气候疾病的抗性基因。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低纬度植物难以适应高纬度条件,反之亦然。因此,大多数新月沃地作物在法国和日本生长良好,但在赤道地区生长不良。
动物也适应与纬度相关的气候特征。在这方面我们是典型的动物,通过内省我们就能了解这一点。我们中的一些人无法忍受寒冷的北方冬季及其短暂的白昼和特有的病菌,而另一些人则无法忍受炎热的热带气候及其特有的疾病。在近几个世纪,来自凉爽北欧的海外殖民者更愿意移民到气候同样凉爽的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并在赤道附近的肯尼亚和新几内亚的凉爽高地定居。被派往炎热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死于疟疾等疾病,而热带人民已经对这些疾病进化出了一些基因抗性。
这就是新月沃地的驯化物种向西和向东传播如此迅速的部分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所传播到的地区的气候。例如,一旦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从匈牙利平原传入中欧,它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从波兰西到荷兰的广大地区第一批农民的遗址(以其特有的线性装饰陶器为标志)几乎是同时代的。到基督时代,源自新月沃地的谷物已经在从爱尔兰大西洋海岸到日本太平洋海岸长达8000英里的范围内生长。这段欧亚大陆的东西向延伸是地球上最长的陆地距离。
因此,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使新月沃地作物能够迅速在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纬度带上启动农业,并丰富了在东亚独立产生的农业。反过来,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相同纬度首次驯化的欧亚作物也能够传播回新月沃地。今天,当种子通过船只和飞机运输到全球各地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餐食是地理上的大杂烩。一顿典型的美国快餐店餐食包括鸡肉(首次驯化于中国)和土豆(来自安第斯山脉)或玉米(来自墨西哥),用黑胡椒(来自印度)调味,并配上一杯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然而,早在2000年前,罗马人也在用他们自己的大杂烩食物滋养自己,这些食物大多起源于别处。在罗马作物中,只有燕麦和罂粟原产于意大利。罗马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基础作物包,辅以榅桲(quince)(起源于高加索地区);小米和孜然(驯化于中亚);黄瓜、芝麻和柑橘类水果(来自印度);以及鸡、稻米、杏、桃和谷子(最初来自中国)。尽管罗马的苹果至少原产于西欧亚大陆,但它们是通过在中国发展并从那里向西传播的嫁接技术种植的。
虽然欧亚大陆提供了世界上同纬度最宽的陆地带,因此成为驯化物种快速传播最显著的例子,但还有其他例子。与肥沃月牙地区农业包传播速度相媲美的是一个亚热带农业包的东向传播,这个农业包最初在华南地区组装完成,在到达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后又得到了补充。在1,600年内,这个包含作物(包括香蕉、芋头和山药)和家畜(鸡、猪和狗)的农业包向东传播了超过5,000英里,进入热带太平洋,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作物在非洲广阔的萨赫勒地带的东西向传播,但古植物学家尚未研究出具体细节。
相比欧亚大陆东西向传播的便利性,非洲南北轴线的传播困难形成了鲜明对比。肥沃月牙地区的大多数原始作物很快到达埃及,然后向南传播到埃塞俄比亚凉爽的高地,但没有继续向南传播。南非的地中海气候本应非常适合这些作物,但埃塞俄比亚和南非之间2,000英里的热带条件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业是通过驯化萨赫勒地带和热带西非本土的野生植物(如高粱和非洲山药)而启动的,这些植物适应了低纬度地区的温暖气温、夏季降雨和相对恒定的日照长度。
同样,肥沃月牙地区家畜向南通过非洲的传播被气候和疾病所阻止或减缓,特别是由采采蝇携带的锥虫病。马从未在赤道以北的西非王国以南地区站稳脚跟。牛、绵羊和山羊的推进在塞伦盖蒂平原的北部边缘停滞了2,000年,而新型的人类经济和牲畜品种正在发展之中。直到公元1-200年,在肥沃月牙地区驯化牲畜大约8,000年后,牛、绵羊和山羊才最终到达南非。热带非洲作物在非洲向南传播也遇到了自己的困难,与那些肥沃月牙地区的牲畜几乎同时随黑人农民(班图人)到达南非。然而,这些热带非洲作物从未能够跨越南非的菲什河,在那里被它们不适应的地中海条件所阻止。
结果就是过去两千年南非历史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进程。南非的一些科伊桑土著民族(也称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获得了牲畜,但仍然没有农业。他们在菲什河东北部被拥有农业的黑人农民所取代并在数量上被超越,而黑人的南向传播在那条河处停止了。只有当欧洲定居者在1652年从海上到达,带来了他们的肥沃月牙作物包时,农业才能在南非的地中海地带繁荣发展。所有这些民族的碰撞产生了现代南非的悲剧:科伊桑人被欧洲病菌和枪支迅速消灭;欧洲人和黑人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另一个世纪的种族压迫;以及现在,欧洲人和黑人在前科伊桑人土地上寻求新的共存模式的努力。
同样,将欧亚大陆传播的便利性与美洲南北轴线的困难进行对比。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距离——比如说,墨西哥高地和厄瓜多尔之间——只有1,200英里,与欧亚大陆上巴尔干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巴尔干为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作物和牲畜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并在肥沃月牙地区农业包组装完成后的2,000年内作为一个整体包接收了这些驯化物种。这种快速传播先发制人地排除了在巴尔干驯化这些物种及相关物种的机会。墨西哥高地和安第斯山脉同样适合彼此的许多作物和家畜。少数作物,特别是墨西哥玉米,确实在前哥伦布时代传播到了另一个地区。
但其他作物和家畜未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传播。墨西哥凉爽的高地本应为饲养骆驼、豚鼠和马铃薯提供理想条件,这些都是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凉爽的高地驯化的。然而,这些安第斯特产的北向传播被中美洲炎热的中间低地完全阻止了。在安第斯山脉驯化骆驼5,000年后,奥尔梅克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以及墨西哥所有其他本土社会仍然没有驮畜,除了狗之外也没有任何可食用的家养哺乳动物。
相反,墨西哥的家养火鸡和美国东部的家养向日葵本可能在安第斯山脉繁衍生息,但它们向南传播却被中间的热带气候所阻止。仅仅700英里的南北距离就使墨西哥的玉米、南瓜和豆类在墨西哥驯化后的数千年里无法到达美国西南部,而墨西哥的辣椒和藜科植物在史前时代更是从未到达那里。在玉米于墨西哥被驯化后的数千年里,它未能向北传播到北美东部,因为那里气候较冷、生长季节较短。在公元1年到公元2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玉米终于出现在美国东部,但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次要的作物。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在适应北方气候的耐寒玉米品种被培育出来之后,以玉米为基础的农业才促进了北美最复杂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这一短暂的繁荣随着哥伦布带来和之后到来的欧洲病菌而终结。
回想一下,大多数肥沃月湾作物经遗传学研究证明仅源自单一驯化过程,由此产生的作物传播如此迅速,以至于它抢先阻止了同一物种或相关物种的任何其他初期驯化。相比之下,许多看似广泛分布的美洲原住民作物被证明由相关物种组成,甚至是同一物种的基因不同品种,在中美洲、南美洲和美国东部独立驯化。在苋菜、豆类、藜科植物、辣椒、棉花、南瓜和烟草中,密切相关的物种在地理上相互替代。在菜豆、利马豆、辣椒(Capsicum annuum / chinense)和南瓜(Cucurbita pepo)中,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相互替代。这些多次独立驯化的遗产可能进一步证明了作物沿美洲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
因此,非洲和美洲是主要具有南北轴线并导致传播缓慢的两个最大陆块。在世界其他某些地区,缓慢的南北传播在较小规模上也很重要。这些其他例子包括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和南印度之间作物交流的蜗牛般缓慢、粮食生产从华南缓慢传播到马来半岛,以及热带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在史前时代未能分别到达现代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的农田地区。这两个澳大利亚角落现在是该大陆的粮仓,但它们位于赤道以南2000多英里。那里的农业不得不等待来自遥远欧洲的、适应欧洲凉爽气候和短生长季节的作物随欧洲船只到来。
我一直在讨论纬度——通过看一眼地图就能轻易评估,因为它是气候、生长条件和粮食生产传播便利性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纬度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且并非总是相同纬度的相邻地方具有相同的气候(尽管它们必然有相同的日照时长)。地形和生态障碍在某些大陆比其他大陆更为明显,是传播的局部重要障碍。
例如,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之间的作物传播非常缓慢且有选择性,尽管这两个地区处于相同纬度。这是因为德克萨斯州和南部大平原的大部分中间地区干旱且不适合农业。欧亚大陆内部的一个相应例子涉及肥沃月湾作物的东部边界,这些作物迅速向西传播到大西洋,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没有遇到主要障碍。然而,在印度更东边,从以冬季降雨为主转向以夏季降雨为主,促使农业更加延迟地延伸到印度东北部的恒河平原,涉及不同的作物和农业技术。再往东,中国的温带地区因中亚沙漠、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组合而与具有相似气候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隔离。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最初发展独立于肥沃月湾相同纬度的发展,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物。然而,即使是中国和欧亚大陆西部之间的这些障碍,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也至少被部分克服,当时西亚的小麦、大麦和马到达了中国。
同样,2000英里南北移动作为障碍的效力也因当地条件而异。肥沃月湾的粮食生产向南传播了这个距离到达埃塞俄比亚,班图的粮食生产从非洲大湖区迅速向南传播到纳塔尔,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中间地区具有相似的降雨模式并适合农业。相比之下,从印度尼西亚向南到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作物传播完全不可能,而从墨西哥到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更短距离的传播却很缓慢,因为中间地区是不利于农业的沙漠。危地马拉以南的中美洲缺乏高海拔高原,以及墨西哥以南特别是巴拿马的中美洲极度狭窄,在抑制墨西哥高地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的作物和牲畜交流方面,至少与纬度梯度同样重要。
大陆在轴线方向上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的传播,也影响了其他技术和发明的扩散。例如,大约公元前3000年,车轮在西南亚或其附近发明后,在几个世纪内迅速向西和向东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在史前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车轮却从未向南传播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公元前1500年在肥沃月牙地带西部发展起来的字母书写原理,在大约一千年内向西传播到迦太基,向东传播到印度次大陆,但在史前时代繁荣了至少2000年的中美洲书写系统却从未到达安第斯山脉。
自然,车轮和文字并不像农作物那样与纬度和日照长度直接相关。相反,这种联系是间接的,特别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后果产生联系。最早的车轮是用牛拉车运输农产品的一部分。早期文字仅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供养的精英阶层使用,它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如皇家宣传、货物清单和官僚记录)。一般来说,那些密集交换农作物、牲畜和与粮食生产相关技术的社会,更有可能参与其他交流。
美国的爱国歌曲《美丽的美国》歌颂我们广阔的天空,我们金色的谷物波浪,从海洋到闪亮的海洋。实际上,这首歌颠倒了地理现实。与非洲一样,在美洲,本土作物和家畜的传播因天空受限和环境障碍而减缓。在北美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从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亚,或者从埃及到南非,从未有本土谷物的波浪延伸,而小麦和大麦的金色波浪却在欧亚大陆广阔的天空下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与美洲原住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相比,欧亚农业的更快传播,在欧亚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迅速扩散中发挥了作用(本书下一部分将展示)。
提出所有这些差异并不是要声称广泛分布的作物值得称赞,或者它们证明了早期欧亚农民的卓越智慧。相反,它们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的方向与美洲或非洲的比较。历史的命运围绕着这些轴线旋转。
我们现在已经追溯了粮食生产如何在少数几个中心兴起,以及它如何以不同的速度从那里传播到其他地区。这些地理差异构成了对亚力问题的重要根本答案,即为什么不同的民族最终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财富。然而,粮食生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原因。在一对一的战斗中,一个赤裸的农民不会比一个赤裸的狩猎采集者有任何优势。
相反,农民力量的部分解释在于粮食生产能够支持更密集的人口:十个赤裸的农民在战斗中肯定比一个赤裸的狩猎采集者有优势。另一部分是,农民和狩猎采集者都不是赤裸的,至少在比喻意义上不是。农民往往会呼出更恶劣的病菌,拥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总体上拥有更强大的技术,并生活在由能够更好地发动征服战争的有文化的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之下。因此,接下来的四章将探讨粮食生产这一根本原因如何导致病菌、文字、技术和集权政府这些直接原因。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的一个医院病例令人难忘地说明了牲畜和农作物与病菌之间的联系。当我的朋友还是一名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时,他被叫到一间病房去处理一对因神秘疾病而压力重重的夫妇。这对夫妇彼此之间以及与我朋友的沟通困难也无济于事。丈夫是一个瘦小、胆怯的男人,患有由不明微生物引起的肺炎,英语能力有限。充当翻译的是他美丽的妻子,她担心丈夫的病情,对陌生的医院环境感到恐惧。我的朋友也因为一周的医院工作,以及试图找出可能导致这种奇怪疾病的不寻常风险因素而感到压力重重。压力使我的朋友忘记了他所学到的关于患者保密性的一切: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要求这位女士问她的丈夫是否有任何可能导致感染的性经历。
当医生看着时,丈夫的脸涨得通红,整个人蜷缩起来显得更加瘦小,试图消失在床单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出几个字。他的妻子突然愤怒地尖叫起来,身体挺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还没等医生阻止,她抓起一个沉重的金属瓶,用全力砸向丈夫的头部,然后冲出了房间。医生花了一段时间才让她丈夫苏醒过来,又花了更长时间才从这个男人蹩脚的英语中弄清楚,他说了什么让妻子如此愤怒。答案慢慢浮现:他承认最近在回家族农场时多次与羊发生性关系;也许那就是他感染这种神秘微生物的原因。
这件事听起来离奇而独特,似乎没有什么更广泛的意义。实际上,它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巨大课题: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我们中很少有人像这位病人那样从肉体上爱羊。但我们大多数人从精神上喜爱我们的宠物,比如狗和猫。作为一个社会,从我们饲养的大量牲畜数量来看,我们显然对羊和其他家畜有着过分的喜爱。例如,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时,澳大利亚的17,085,400人对羊如此推崇,以至于他们饲养了161,600,000只羊。
我们中的一些成年人,以及更多的儿童,会从宠物那里感染传染病。通常这些疾病只是造成一些麻烦,但少数已经演变成更严重的东西。在我们近代历史中人类的主要杀手——天花、流感、结核病、疟疾、鼠疫、麻疹和霍乱——都是从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尽管导致我们流行病的大多数微生物现在矛盾地几乎只局限于人类。因为疾病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杀手,它们也是历史的决定性塑造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死于战争传播的微生物的受害者比死于战伤的还要多。所有那些颂扬伟大将军的军事史都过度简化了一个打击自负的真相:过去战争的赢家并不总是拥有最好将军和武器的军队,而往往只是那些携带最恶毒病菌传播给敌人的军队。
病菌在历史中作用的最残酷例子来自1492年哥伦布航行开始的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尽管死于残暴的西班牙征服者之手的美洲原住民数量众多,但他们远远比不上死于残暴的西班牙微生物的受害者。为什么美洲和欧洲之间恶性病菌的交换如此不平等?为什么美洲原住民的疾病没有反过来摧毁西班牙入侵者,传播回欧洲,并消灭欧洲95%的人口?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许多其他土著民族被欧亚病菌摧毁的情况中,以及欧洲征服者在非洲和亚洲热带地区遭受摧毁的情况中。
因此,关于人类疾病的动物起源的问题,隐藏在人类历史最广泛的模式背后,也隐藏在当今人类健康的一些最重要问题背后。(想想艾滋病,这种爆炸性传播的人类疾病似乎是从非洲野生猴子体内的病毒演化而来的。)本章将首先探讨什么是”疾病”,以及为什么一些微生物演化得”让我们生病”,而大多数其他生物物种不会让我们生病。我们将研究为什么我们许多最熟悉的传染病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比如我们当前的艾滋病流行和中世纪的黑死病(腺鼠疫)流行。然后我们将探讨现在局限于我们的微生物的祖先如何从它们原来的动物宿主转移到人类身上。最后,我们将看到对我们传染病的动物起源的洞察如何帮助解释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那重大的、几乎单向的病菌交换。
自然地,我们倾向于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思考疾病:我们能做什么来拯救自己并杀死微生物?让我们消灭这些恶棍,不要管[它们]的动机是什么!然而,在一般生活中,人必须了解敌人才能打败他,这在医学上尤其如此。
因此,让我们先暂时抛开我们人类的偏见,从微生物的角度来考虑疾病。毕竟,微生物和我们一样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微生物从以奇怪的方式让我们生病中获得了什么进化优势,比如给我们生殖器溃疡或腹泻?为什么微生物会演化得杀死我们?这似乎特别令人困惑和弊大于利,因为杀死宿主的微生物也杀死了自己。
基本上,微生物像其他物种一样进化。进化选择那些最有效地繁殖后代并帮助它们传播到合适生存地点的个体。对于微生物来说,传播可以用数学定义为每个原始患者感染的新受害者数量。这个数字取决于每个受害者保持感染新受害者能力的时间,以及微生物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
微生物已经演化出多种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到人的方式。传播得更好的病菌会留下更多后代,最终被自然选择所青睐。我们的许多疾病”症状”实际上代表了一些该死的聪明微生物修改我们身体或行为的方式,使我们被征召来传播微生物。
病菌传播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被动地等待传递给下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些微生物采用的策略,它们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比如沙门氏菌,我们通过食用已经被感染的鸡蛋或肉类而感染;引起旋毛虫病(trichinosis)的蠕虫,它通过等待我们杀死猪并在未充分烹饪的情况下食用而从猪传播到人类;以及引起异尖线虫病(anisakiasis)的蠕虫,喜爱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偶尔会因食用生鱼而感染。这些寄生虫从被吃掉的动物传播到人,但在新几内亚高地引起笑病(kuru)的病毒过去则是从一个被吃掉的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它通过食人行为传播,当高地的婴儿在玩弄他们的母亲刚从等待烹饪的已故kuru受害者身上切下的生脑时,舔了手指,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有些微生物不会等待旧宿主死亡并被吃掉,而是搭便车附着在昆虫的唾液中,这些昆虫叮咬旧宿主后飞走寻找新宿主。这种免费搭乘可能由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提供,它们分别传播疟疾、鼠疫、斑疹伤寒或昏睡病。被动传播中最肮脏的伎俩是微生物从母亲传给胎儿,从而在婴儿出生时就已感染。通过这种伎俩,引起梅毒、风疹以及现在的艾滋病的微生物提出了伦理困境,相信宇宙根本公正的人们不得不拼命应对。
其他病菌则主动采取行动,可以说是亲力亲为。它们以加速传播的方式改变宿主的解剖结构或习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梅毒等性病引起的开放性生殖器溃疡是一种可恶的侮辱。然而,从微生物的角度来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装置,用来利用宿主的帮助将微生物接种到新宿主的体腔中。天花引起的皮肤病变同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传播微生物(有时非常间接,比如当美国白人为了消灭”好战的”美洲原住民而送给他们天花患者曾经使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时)。
更加积极的策略是流感、普通感冒和百日咳(pertussis)微生物采用的,它们诱导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从而向潜在的新宿主发射一团微生物云。同样,霍乱细菌在受害者体内引起大量腹泻,将细菌输送到潜在新受害者的供水系统中,而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则通过老鼠的尿液传播。在改变宿主行为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狂犬病病毒,它不仅进入被感染狗的唾液,还驱使狗陷入疯狂撕咬的状态,从而感染许多新受害者。但就病菌自身的体力努力而言,奖项仍然归于钩虫和血吸虫等蠕虫,它们从水或土壤中主动钻入宿主皮肤,而它们的幼虫曾在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中排泄到水或土壤中。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是”疾病症状”。从病菌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传播病菌的巧妙进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生病”符合病菌的利益。但是为什么病菌会进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我毁灭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来看,这只是宿主症状促进微生物有效传播的意外副产品(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是的,未经治疗的霍乱患者可能最终会因每天产生数加仑的腹泻液而死亡。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只要患者还活着,霍乱细菌就会从被大量传播到下一批受害者的供水系统中获益。只要每个受害者平均感染超过一个新受害者,细菌就会传播,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亡。
现在让我们回到考虑我们自己的自私利益:保持生存和健康,最好的办法是杀死该死的病菌。我们对感染的一个常见反应是发烧。同样,我们习惯于将发烧视为”疾病症状”,好像它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不起任何作用。但体温调节受我们的基因控制,不是偶然发生的。少数微生物对热比我们自己的身体更敏感。通过升高体温,我们实际上试图在自己被烤熟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们的另一个常见反应是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白细胞和其他细胞主动寻找并杀死外来微生物。我们逐渐针对感染我们的特定微生物建立起的特异性抗体(antibodies)使我们在治愈后不太可能再次感染。正如我们从经验中都知道的,有些疾病,如流感和普通感冒,我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终可能再次感染这种疾病。但对于其他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风疹、百日咳和现已被战胜的天花—一次感染刺激产生的抗体会赋予我们终身免疫力。这就是疫苗接种的原理:通过给我们接种死亡或减弱的微生物菌株来刺激我们的抗体产生,而无需经历疾病的实际体验。
遗憾的是,一些聪明的微生物不会轻易屈服于我们的免疫防御。有些微生物已经学会通过改变其分子片段(即所谓的抗原(antigens))来欺骗我们,而我们的抗体正是识别这些抗原。流感病毒不断进化或产生新的毒株,带有不同的抗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两年前得过流感并不能保护你免受今年到来的不同毒株的感染。疟疾和昏睡病在快速改变抗原的能力上甚至更加狡猾。而所有病原体中最狡猾的是艾滋病病毒,它甚至在寄生于单个患者体内时就能进化出新的抗原,从而最终压垮患者的免疫系统。
我们最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它会一代一代地改变我们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疾病,总有一些人在基因上比其他人更具抵抗力。在流行病期间,那些携带抗病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类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反复暴露于特定病原体的人类群体中,携带抗病基因的个体比例会越来越高——仅仅是因为那些不幸的、没有这些基因的个体更不可能存活下来将基因传给后代。
你可能又在想,这安慰不了人。这种进化反应对那些在基因上易感而濒临死亡的个体没有任何帮助。但这确实意味着,整个人类群体会对病原体获得更好的保护。这些基因防御的例子包括镰状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化基因分别为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提供的(有代价的)对抗疟疾、结核病和细菌性腹泻的保护。
简而言之,我们与大多数物种的互动,以蜂鸟为例,不会让我们或蜂鸟”生病”。我们和蜂鸟都不必进化出针对彼此的防御机制。这种和平关系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传播它们的后代,也不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食物。蜂鸟进化成以花蜜和昆虫为食,它们用自己的翅膀找到这些食物。
但微生物进化成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为食,而且它们没有翅膀让它们在原宿主死亡或产生抗性后到达新宿主的身体。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进化出诡计让它们在潜在宿主之间传播,而这些诡计中的许多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疾病症状”。我们也进化出了自己的反制手段,病菌则以进化出反-反制手段作为回应。我们和病原体现在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进化竞赛,失败者的代价是死亡,而自然选择扮演着裁判的角色。现在让我们考虑这场竞赛的形式:闪电战还是游击战?
假设我们统计某个地理区域内某种特定传染病的病例数,并观察这些数字如何随时间变化。不同疾病的结果模式差异很大。对于某些疾病,如疟疾或钩虫病,受影响地区在任何年份的任何月份都会出现新病例。而所谓的流行病(epidemic diseases)则会长时间没有病例,然后出现一波病例,之后又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病例。
在这些流行病中,流感是大多数美国人亲身熟悉的疾病,某些年份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糟糕的年份(但对流感病毒来说是好年份)。霍乱疫情发生的间隔更长,1991年秘鲁霍乱疫情是20世纪第一次到达新大陆的霍乱疫情。尽管今天的流感和霍乱疫情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流行病曾经要可怕得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流感疫情,它夺走了2100万人的生命。黑死病(鼠疫(bubonic plague))在1346年至1352年间杀死了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某些城市的死亡率高达70%。19世纪80年代初,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萨斯喀彻温省修建时,该省的土著美国人此前很少接触白人及其病菌,死于结核病的比例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年9%。
那些以流行病而非稳定细流形式侵袭我们的传染病具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能快速高效地从感染者传播给附近的健康人,结果是整个人群在短时间内都暴露于病原体。其次,它们是”急性”疾病:在短时间内,你要么死亡,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中幸运康复的人会产生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对疾病的复发免疫,可能终生免疫。最后,这些疾病往往仅限于人类;导致这些疾病的微生物往往不会生活在土壤或其他动物中。所有这四个特征都适用于美国人认为的熟悉的儿童急性流行病,包括麻疹、风疹、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这四种特征的组合容易导致疾病大流行的原因很容易理解。简化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微生物的快速传播和症状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群中的每个人都会很快被感染,不久之后要么死亡,要么康复并获得免疫力。没有人还活着可以继续被感染。但由于微生物除了在活人体内无法生存,这种疾病就会消失,直到新一批婴儿长到易感年龄——并且直到有感染者从外部到来引发新的流行。
这类疾病如何以流行病形式发生的经典例证是麻疹在被称为法罗群岛的大西洋孤立岛屿上的历史。1781年,一场严重的麻疹流行到达法罗群岛,然后消失了,使岛屿在1846年之前一直没有麻疹,直到一名受感染的木匠乘船从丹麦抵达。在三个月内,几乎整个法罗群岛人口(7,782人)都感染了麻疹,然后要么死亡要么康复,使麻疹病毒再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研究表明,在任何少于50万人的人口中,麻疹都可能消失。只有在更大的人口中,疾病才能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而持续存在,直到最初受感染地区有足够多的婴儿出生,麻疹才能回到那里。
法罗群岛麻疹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地其他我们熟悉的急性传染病。为了维持自身,它们需要数量足够多、密度足够大的人口,以便在疾病本该衰退时有大量新的易感儿童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类似疾病也被称为人群疾病。
显然,人群疾病无法在狩猎采集者和刀耕火种农民的小群体中维持自身。正如亚马逊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现代经验所证实的那样,几乎整个部落可能被外来访客带来的流行病消灭——因为部落中没有人对这种微生物有任何抗体。例如,1902年冬天,捕鲸船Active号上的一名水手带来的痢疾流行,导致56名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中的51人死亡,这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南安普顿岛上的非常孤立的群体。此外,麻疹和我们的其他一些”儿童”疾病更容易杀死受感染的成年人而不是儿童,而部落中所有成年人都是易感的。(相比之下,现代美国人很少在成年时感染麻疹,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在儿童时期要么得过麻疹,要么接种过疫苗。)在杀死大部分部落成员后,流行病就消失了。部落的小人口规模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无法维持从外部引入的流行病,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永远无法进化出自己的流行病来回馈给访客。
但这并不是说小型人口就没有任何传染病。它们确实有感染,但只有某些类型。有些是由能够在动物或土壤中维持自身的微生物引起的,结果是疾病不会消失,而是持续存在以感染人类。例如,黄热病病毒由非洲野生猴子携带,因此总能感染非洲农村人口,并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传播到新大陆,感染新世界的猴子和人类。
小型人口的其他感染还包括麻风病和雅司病等慢性疾病。由于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杀死受害者,受害者仍然活着作为微生物的宿主来感染部落的其他成员。例如,我在1960年代工作过的新几内亚高地的卡里穆伊巴西姆地区,居住着几千人的孤立人口,遭受世界上麻风病发病率最高的困扰——约40%!最后,小型人口也容易受到我们不会产生免疫力的非致命感染,结果是同一个人在康复后可能再次被感染。这种情况发生在钩虫和许多其他寄生虫身上。
所有这些类型的疾病,是小型孤立人口的特征,必定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是我们在进化史的早期数百万年中能够进化和维持的疾病,当时人类总人口很少且分散。这些疾病也与我们最亲近的野生亲属——非洲大猿——的疾病相同或相似。相比之下,我们之前讨论的人群疾病只能随着大规模、高密度人口的积累而出现。这种积累始于大约10,000年前农业的兴起,然后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兴起而加速。事实上,许多熟悉的传染病的首次证实日期令人惊讶地晚近:天花约在公元前1600年(从埃及木乃伊上的痘痕推断),腮腺炎在公元前400年,麻风病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在1959年。
刚才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农业支撑的人口密度远高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平均高出10到100倍。此外,狩猎采集者经常转移营地,留下他们堆积着微生物和寄生虫幼虫的粪堆。但农民是定居的,生活在自己的污水中,从而为微生物提供了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饮用水的捷径。
一些农业人口让自己的粪便细菌和寄生虫更容易感染新的受害者,方法是收集他们的粪便和尿液,并将其作为肥料撒在人们工作的田地上。灌溉农业和养鱼业为携带血吸虫病的蜗牛和当我们涉水穿过粪便污染的水时钻入我们皮肤的吸虫提供了理想的生存条件。定居的农民不仅被自己的粪便包围,还被传播疾病的啮齿动物包围,这些动物被农民储存的食物吸引。非洲农民开辟的森林空地也为传播疟疾的蚊子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栖息地。
如果说农业的兴起对我们的微生物来说是一个福音,那么城市的兴起则是更大的福音,因为更密集的人口在更糟糕的卫生条件下溃烂。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终实现自我维持:在此之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的持续移民对于弥补城市居民因人群疾病而持续死亡是必要的。另一个福音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路线有效地将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人口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微生物繁殖地。正是在那时,天花最终到达罗马,作为安东尼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在公元165年至180年间杀死了数百万罗马公民。
同样,腺鼠疫首次作为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出现在欧洲(公元542-43年)。但直到公元1346年,当与中国的陆路贸易新路线为来自中亚鼠疫流行区的跳蚤感染毛皮沿着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快速运输到欧洲提供便利时,鼠疫才开始以黑死病流行病的形式全面袭击欧洲。今天,我们的喷气式飞机使即使是最长的洲际航班也比任何人类传染病的持续时间更短。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在1991年停靠秘鲁利马时,能够在同一天将数十名霍乱感染者送到距离利马3000多英里的我所在的洛杉矶市。美国人世界旅行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移民到美国的增长,正在将我们变成另一个大熔炉——这一次,是我们以前认为只会在遥远国家引起异国疾病的微生物的大熔炉。
因此,当人类人口变得足够庞大和集中时,我们达到了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终于可以演化并维持仅限于我们自己物种的人群疾病。但这个结论提出了一个悖论:这些疾病在此之前不可能存在!相反,它们必须作为新疾病演化而来。那些新疾病从哪里来?
最近,从疾病致病微生物本身的分子研究中出现了证据。对于许多导致我们独特疾病的微生物,分子生物学家现在可以识别出微生物的近亲。这些也被证明是人群传染病的病原体——但是被限制在我们的家畜和宠物的各种物种中!在动物中,流行病也需要大量、密集的种群,并不会影响任何动物:它们主要局限于提供必要大种群的社会性动物。因此,当我们驯化社会性动物,如牛和猪时,它们已经受到流行病的折磨,等待着被转移给我们。
例如,麻疹病毒与引起牛瘟的病毒关系最密切。那种令人讨厌的流行病影响牛和许多野生反刍哺乳动物,但不影响人类。麻疹反过来不影响牛。麻疹病毒与牛瘟病毒的密切相似性表明,后者从牛转移到人类,然后通过改变其特性以适应我们而演化成麻疹病毒。考虑到许多农民生活和睡在牛及其粪便、尿液、呼吸、疮和血液附近,这种转移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我们与牛的亲密关系自我们驯化它们以来已经持续了9000年——有足够的时间让牛瘟病毒发现我们就在附近。如表11.1所示,我们其他熟悉的传染病同样可以追溯到我们动物朋友的疾病。
鉴于我们与我们喜爱的动物的接近,我们一定不断受到它们微生物的轰炸。这些入侵者被自然选择筛选,其中只有少数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人类疾病。对当前疾病的快速调查让我们追溯出从动物前体演化成专门化人类疾病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例子是我们时不时地直接从宠物和家畜身上感染的几十种疾病。它们包括从猫身上感染的猫抓病,从狗身上感染的钩端螺旋体病,从鸡和鹦鹉身上感染的鹦鹉热,以及从牛身上感染的布鲁氏菌病。我们同样容易从野生动物身上感染疾病,比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感染的兔热病。所有这些微生物仍然处于演化成专门的人类病原体(pathogen)的早期阶段。它们仍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甚至从动物传播给我们的情况也不常见。
| 人类疾病 | 具有最相近病原体的动物 |
|---|---|
| 麻疹 | 牛(牛瘟) |
| 结核病 | 牛 |
| 天花 | 牛(牛痘)或其他携带相关痘病毒的家畜 |
| 流感 | 猪和鸭 |
| 百日咳 | 猪、狗 |
| 恶性疟疾 | 鸟类(鸡和鸭?) |
在第二阶段,一种原本的动物病原体演化到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并引发流行病的程度。然而,这种流行病会因为多种原因而消亡,比如被现代医学治愈,或者因为周围所有人都已被感染并获得免疫或死亡而停止传播。例如,一种名为奥尼昂尼昂热的未知发热病于1959年在东非出现,继而感染了数百万非洲人。它可能源于猴子身上的病毒,并通过蚊子传播给人类。患者迅速康复并对进一步的感染产生免疫这一事实帮助这种新疾病迅速消亡。对美国人来说更切近的例子是布拉格堡热,这是1942年夏天在美国爆发的一种新的钩端螺旋体病,很快就消失了。
另一个因不同原因消失的致命疾病是新几内亚的笑病,它通过食人习俗传播,由一种慢性病毒引起,从未有人康复过。库鲁病正在走向灭绝新几内亚2万人口的福雷部落,直到1959年左右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建立终止了食人习俗,从而终止了库鲁病的传播。医学史上充满了听起来不像今天已知的任何疾病的记载,但这些疾病曾经引发可怕的流行病,然后神秘地消失了,就像它们来时一样神秘。在1485年至1552年间席卷并恐吓欧洲的”英国汗热病”,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法国的”皮卡第汗热病”,只是在现代医学设计出识别致病微生物的方法之前就消失的众多流行病中的两个例子。
我们主要疾病演化的第三阶段由那些确实在人类中建立起来、尚未(还未?)消亡、可能或可能不会成为人类主要杀手的原动物病原体代表。拉沙热的未来仍然非常不确定,它由可能源自啮齿动物的病毒引起。拉沙热于1969年首次在尼日利亚被观察到,它引起的致命疾病传染性极强,以至于如果出现哪怕一例病例,尼日利亚的医院就会被关闭。更为确立的是莱姆病,它由我们从老鼠和鹿携带的蜱虫叮咬中获得的螺旋体引起。尽管美国首次已知的人类病例最近在1962年才出现,莱姆病已经在我国许多地区达到流行病的程度。艾滋病源自猴子病毒,首次在人类中记录约在1959年,其未来(从病毒的角度来看)甚至更加稳固。
这种演化的最后阶段由仅限于人类的主要的、长期存在的流行病代表。这些疾病必定是远远更多试图从动物跳到我们身上的病原体的演化幸存者——而且大多数都失败了。
在这些阶段中,当动物的专属疾病转变为人类的专属疾病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一种转变涉及中间媒介(vector)的改变:当依赖某种节肢动物媒介传播的微生物转换到新宿主时,该微生物可能被迫寻找新的节肢动物。例如,斑疹伤寒最初通过鼠蚤在老鼠之间传播,这在一段时间内足以将斑疹伤寒从老鼠传播给人类。最终,斑疹伤寒微生物发现人体虱提供了一种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播的更有效方法。现在美国人大多已经除虱,斑疹伤寒发现了进入我们体内的新途径:感染北美东部的飞鼠,然后传播给阁楼里有飞鼠的人。
简而言之,疾病代表着进行中的演化(evolution),微生物通过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适应新的宿主和媒介。但与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提供了不同的免疫防御、虱子、粪便和化学物质。在这个新环境中,微生物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繁殖方式。在几个有启发性的案例中,医生或兽医实际上已经能够观察到微生物演化出这些新方式。
最经过充分研究的案例涉及粘液瘤病袭击澳大利亚兔子时发生的情况。粘液瘤病毒原产于巴西野生兔种,已被观察到会在欧洲家兔中引起致命流行病,而欧洲家兔是不同的物种。因此,1950年该病毒被有意引入澳大利亚,希望清除这片大陆上的欧洲兔灾害——这些兔子在19世纪被愚蠢地引入。第一年,粘液瘤病毒在受感染兔子中产生了令人满意的(对澳大利亚农民而言)99.8%的死亡率。不幸的是,对农民来说,死亡率在第二年下降到90%,最终降至25%,彻底根除澳大利亚兔子的希望落空了。问题在于粘液瘤病毒进化以服务于自身利益,这既不同于我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兔子的利益。病毒发生了变化,杀死的兔子更少,并允许致命感染的兔子在死亡前存活更长时间。结果,致命性较低的粘液瘤病毒将病毒后代传播给更多兔子,而不是最初的高毒性粘液瘤病毒。
关于人类的类似例子,我们只需考虑梅毒令人惊讶的进化过程。今天,我们对梅毒的两个直接联想是生殖器溃疡和发展非常缓慢的疾病,导致许多未经治疗的受害者在多年后才死亡。然而,当梅毒于1495年在欧洲首次被明确记录时,其脓疱通常覆盖从头部到膝盖的身体,导致人们面部肉体脱落,并在几个月内导致死亡。到1546年,梅毒已经进化成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疾病症状。显然,就像粘液瘤病毒一样,那些进化为让受害者存活更长时间的梅毒螺旋体,从而能够将其螺旋体后代传播给更多受害者。
致命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通过欧洲人征服和减少新大陆人口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死于欧亚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远多于死于欧洲枪炮和剑的人。这些病菌通过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及其领导人,并削弱幸存者的士气,破坏了印第安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带着600名西班牙人登陆墨西哥海岸,征服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仅损失三分之二的兵力就逃脱,并成功战斗回到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最初的天真。但当科尔特斯的下一次进攻到来时,阿兹特克人不再天真,以最顽强的精神逐街战斗。给西班牙人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它于1520年随一名来自西属古巴的受感染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产生的流行病杀死了近一半的阿兹特克人,包括库伊特拉瓦克皇帝。阿兹特克幸存者因这种神秘疾病而士气低落,这种疾病杀死印第安人但放过西班牙人,仿佛在宣传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到1618年,墨西哥最初约2000万的人口已经暴跌至约160万。
皮萨罗在1531年带着168人登陆秘鲁海岸征服数百万人的印加帝国时,也有类似的残酷运气。幸运的是对皮萨罗而言,不幸的是对印加人而言,天花大约在1526年通过陆路到达,杀死了大部分印加人口,包括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指定的继承人。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王位空缺的结果是瓦伊纳·卡帕克的另外两个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卷入了内战,皮萨罗利用这场内战征服了分裂的印加人。
当我们美国人想到1492年存在的人口最多的新大陆社会时,只有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社会往往会浮现在我们脑海中。我们忘记了北美也在最合乎逻辑的地方——密西西比河谷——支持着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社会,这里包含了我们今天一些最好的农田。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征服者对这些社会的毁灭没有直接贡献;提前传播的欧亚病菌做了一切。当埃尔南多·德索托于1540年成为第一个穿越美国东南部的欧洲征服者时,他遇到了两年前被遗弃的印第安城镇遗址,因为居民死于流行病。这些流行病是从被访问海岸的西班牙人感染的沿海印第安人传播的。西班牙人的微生物在西班牙人自己之前就传播到了内陆。
德索托仍然能够看到一些沿密西西比河下游排列的人口密集的印第安城镇。在他的探险结束后,欧洲人很长时间没有再次到达密西西比河谷,但欧亚微生物现在已经在北美建立并不断传播。到下一次欧洲人出现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时,也就是1600年代后期的法国定居者,几乎所有那些大型印第安城镇都已消失。它们的遗迹是密西西比河谷的大型土堆遗址。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当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许多建造土堆的社会仍然基本完整,它们在1492年至欧洲人系统探索密西西比河之间崩溃了(可能是由于疾病)。
当我年轻时,美国学童被教导北美最初只居住着大约一百万印第安人。这个较低的数字有助于为白人征服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大陆提供正当理由。然而,考古发掘以及对最早到达我们海岸的欧洲探险家留下的描述的仔细研究,现在表明印第安人的初始数量约为2000万。对整个新大陆而言,在哥伦布到达后的一两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口的减少估计高达95%。
主要的杀手是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的旧大陆病菌,因此他们对这些病菌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抗性(genetic resistance)。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在杀手排行榜上争夺首位。仿佛这些还不够,白喉、疟疾、腮腺炎、百日咳、鼠疫、结核病和黄热病紧随其后。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亲眼目睹了病菌到来时发生的毁灭。例如,1837年,拥有我们大平原上最精细文化之一的曼丹印第安部落,从一艘从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上行的汽船上感染了天花。一个曼丹村庄的人口在几周内从2000人骤降至不到40人。
虽然有十多种源自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在新大陆建立,但也许没有一种主要杀手从美洲传到欧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梅毒,其起源地区仍存在争议。当我们回想起大规模、密集的人口是我们群体传染病(crowd infectious diseases)进化的先决条件时,这种病菌交换的单向性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如果对前哥伦布时期新大陆人口的最新评估是正确的,它并不远低于当时的欧亚大陆人口。一些新大陆城市如特诺奇蒂特兰当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为什么特诺奇蒂特兰没有等待西班牙人的可怕病菌呢?
一个可能的促成因素是,密集人口的兴起在新大陆比旧大陆晚一些。另一个因素是,美洲三个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谷——从未像罗马时代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那样,通过定期快速贸易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微生物繁殖地。然而,这些因素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新大陆显然最终根本没有致命的群体流行病。(从1000年前去世的秘鲁印第安人木乃伊中报告发现了结核病DNA,但所使用的鉴定程序无法区分人类结核病和在野生动物中广泛存在的密切相关病原体——牛分枝杆菌)。
相反,当我们停下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时,致命群体流行病未能在美洲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变得清晰了。它们可能从什么微生物进化而来?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群体疾病是从被驯化的欧亚大陆群居动物的疾病进化而来的。虽然欧亚大陆存在许多这样的动物,但美洲只有五种动物被驯化: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南美热带地区的麝香鸭,以及整个美洲的狗。
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新大陆家畜的极度匮乏反映了野生原材料的匮乏。大约在13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美洲约80%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灭绝了。与牛和猪相比,留给美洲原住民的少数家畜不太可能成为群体疾病的来源。麝香鸭和火鸡不生活在大群中,它们也不是我们有太多身体接触的可爱物种(如小羊羔)。豚鼠可能为我们的疾病目录贡献了类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锥虫感染,但这并不确定。最初,最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源自美洲驼(或羊驼)的人类疾病,人们很容易认为美洲驼是欧亚大陆牲畜的安第斯等价物。然而,作为人类病原体的来源,美洲驼有四个不利因素:它们的饲养群体比绵羊、山羊和猪的群体小;它们的总数从未接近欧亚大陆家畜种群的数量,因为美洲驼从未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之外;人们不喝(也不会因此感染)美洲驼奶;美洲驼不养在室内,与人类没有密切联系。相反,新几内亚高地的人类母亲经常哺育小猪,猪和牛经常被养在农民的小屋里。
动物源性疾病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旧世界与新世界的碰撞。欧亚病菌在摧毁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太平洋岛民、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南非的科伊桑人(Khoisan peoples)(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此前未曾接触过欧亚病菌的民族,累计死亡率从50%到100%不等。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抵达时的约800万人,到1535年降至零。1875年,麻疹随一位从澳大利亚访问归来的斐济酋长抵达斐济,并杀死了当时约四分之一的斐济人(在此之前,大多数斐济人已经死于从1791年欧洲人首次到访开始的流行病)。1779年库克船长带来的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感,随后是1804年的一场大型伤寒流行病以及无数”小型”流行病,使夏威夷人口从1779年的约50万人减少到1853年的84,000人,这一年天花终于抵达夏威夷,杀死了幸存者中的约10,000人。这些例子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
然而,病菌并非仅仅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世界和澳大利亚没有等待欧洲人的本土流行病,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肯定有。遍布热带旧世界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以及热带非洲的黄热病是(现在仍然是)最臭名昭著的热带杀手。它们对欧洲人殖民热带地区构成了最严重的障碍,并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直到欧洲瓜分新世界开始近400年后才完成。此外,一旦疟疾和黄热病确实通过欧洲船只运输传播到美洲,它们也成为殖民新世界热带地区的主要障碍。一个熟悉的例子是这两种疾病在阻止法国努力,以及几乎阻止最终成功的美国努力建造巴拿马运河中所起的作用。
牢记所有这些事实,让我们试着重新认识病菌在回答亚力问题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比他们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发展出了巨大优势。但仅凭这一优势并不能完全解释最初如此少的欧洲移民如何取代了美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大部分原住民人口。如果没有欧洲给其他大陆的险恶礼物——从欧亚人与家畜的长期亲密接触中演化出的病菌,这一切可能不会发生。
十九世纪的作者倾向于将历史解释为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关键标志包括农业、冶金、复杂技术、中央集权政府和文字的发展。其中,文字在传统上是地理分布最受限的:直到伊斯兰教和欧洲殖民者的扩张之前,它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赤道以南的非洲以及整个新世界(除了中美洲的一小部分)都不存在。由于这种受限的分布,以文明自豪的民族总是将文字视为使他们高于”野蛮人”或”未开化者”的最明显区别。
知识带来力量。因此,文字为现代社会带来力量,它使得以更高的准确性、更大的数量和细节,从更遥远的土地和更久远的时代传播知识成为可能。当然,一些民族(特别是印加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成功管理了帝国,而”文明”民族并不总是能击败”野蛮人”,正如面对匈奴人的罗马军队所认识到的那样。但欧洲对美洲、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征服说明了典型的近代结果。
文字与武器、微生物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一起,作为现代征服的推动力量。组织殖民舰队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通过文字传达的。舰队根据先前探险准备的地图和书面航行指南确定航线。先前探险的书面记录激发了后来的探险,描述了等待征服者的财富和肥沃土地。这些记录教会了后续探险者预期什么样的条件,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由此产生的帝国是在文字的帮助下管理的。虽然在无文字社会中所有这些类型的信息也通过其他方式传播,但文字使传播变得更容易、更详细、更准确、更有说服力。
那么,既然文字有如此巨大的价值,为什么只有一些民族而非其他民族发展出了文字呢?例如,为什么传统的狩猎采集者都没有演化或采用文字?在岛屿帝国中,为什么米诺斯克里特岛产生了文字,而波利尼西亚的汤加却没有?文字在人类历史上独立演化了多少次,在什么情况下,用于什么目的?在那些确实发展出文字的民族中,为什么有些比其他民族早得多?例如,今天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识字,但大多数伊拉克人却不识字:为什么文字却在伊拉克出现得早了近四千年?
文字从起源地的传播也提出了重要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从新月沃地传播到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却没有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文字系统是通过被复制而传播的,还是现有系统仅仅激发了邻近民族发明自己的系统?如果有一个适用于某种语言的文字系统,你如何为不同的语言设计系统?每当人们试图理解人类文化许多其他方面的起源和传播时,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比如技术、宗教和食物生产。对这些关于文字的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这些问题通常可以通过书面记录本身以独特的细节得到回答。因此,我们将追溯文字的发展,不仅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还因为它为文化史提供的一般见解。
文字系统的三种基本策略在一个书面符号所表示的语音单位大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单个基本音,要么是整个音节,要么是整个单词。其中,今天大多数民族采用的是字母表(alphabet),理想情况下为语言的每个基本音(音位/phoneme)提供一个独特的符号(称为字母)。实际上,大多数字母表只包含约20或30个字母,而大多数语言的音位比它们的字母表的字母数量多。例如,英语用仅仅26个字母转录约40个音位。因此,大多数按字母书写的语言,包括英语,被迫将几个不同的音位分配给同一个字母,并用字母组合来表示某些音位,例如英语的双字母组合sh和th(分别在俄语和希腊字母表中用单个字母表示)。
第二种策略使用所谓的语标(logogram),意思是一个书面符号代表一个完整的单词。这是中文书写的许多符号和主要日语书写系统(称为汉字/kanji)的功能。在字母书写传播之前,大量使用语标的系统更为常见,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字形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第三种策略,对本书大多数读者来说最不熟悉,为每个音节使用一个符号。实际上,大多数这样的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syllabary)只为一个辅音后跟一个元音的音节(像单词”fa-mi-ly”的音节)提供独特的符号,并采用各种技巧通过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类型的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很常见,例如迈锡尼希腊的线形文字B。一些音节文字今天仍然存在,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用于电报、银行对账单和盲文的假名(kana)音节文字。
我有意将这三种方法称为策略而非书写系统。没有任何实际的书写系统专门使用一种策略。中文书写不是纯粹的语标书写,英语书写也不是纯粹的字母书写。像所有字母书写系统一样,英语使用许多语标,如数字、$、%和+:即由任意符号组成,不是由语音元素构成,代表整个单词。“音节”线形文字B有许多语标,而”语标”埃及象形文字包括许多音节符号以及每个辅音的实际字母表。
从零开始发明文字系统肯定比借用和改编一个系统困难得多。最早的书吏(scribe)必须确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原则。例如,他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将连续的话语分解为语音单位,无论这些单位被视为单词、音节还是音位。他们必须学会通过我们在语音音量、音调、速度、重音、短语分组以及个人发音特点方面的所有正常变化来识别相同的声音或语音单位。他们必须决定书写系统应该忽略所有这些变化。然后他们必须设计用符号表示声音的方法。
不知何故,最早的书吏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而没有任何最终结果的例子来指导他们的努力。这项任务显然如此困难,以至于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次人们完全独立地发明了文字。两次无可争议的独立文字发明是由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完成的,以及墨西哥印第安人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完成的(图12.1);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公元前1300年之前)也可能是独立产生的。此后发展出文字的可能所有其他民族都借用、改编或至少受到现有系统的启发。
我们能够追溯到最详细细节的独立发明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苏美尔楔形文字(cuneiform)(图12.1)。在它成型之前的数千年里,新月沃地的一些农耕村庄的人们一直在使用各种简单形状的陶土标记(token)进行记账,比如记录羊的数量和谷物的数量。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最后几个世纪,记账技术、格式和符号的发展迅速催生了第一个书写系统。其中一项技术创新是使用扁平的陶土泥板作为方便的书写表面。最初,泥土是用尖头工具刮划的,后来逐渐被芦苇触笔(stylus)取代,用于整齐地在泥板上压印标记。格式方面的发展包括逐渐采用一些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惯例:书写应该组织成规则的行或列(苏美尔人使用横行,就像现代欧洲人一样);行应该按照恒定的方向阅读(苏美尔人从左到右,就像现代欧洲人一样);行应该从泥板的顶部向底部阅读,而不是反过来。
但关键的变化涉及到几乎所有书写系统都面临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如何设计出约定俗成的可见标记来表示实际的spoken sounds(口语声音),而不仅仅是想法或与发音无关的词语。这个解决方案的早期阶段已经被发现,特别是在从前苏美尔城市乌鲁克遗址中发掘出的数千块陶土泥板中,乌鲁克位于现代巴格达东南约200英里的幼发拉底河畔。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符号是所指对象的可识别图画(例如,鱼或鸟的图画)。自然地,这些图形符号主要由数字加上可见物体的名词组成;由此产生的文本仅仅是电报式速记的会计报告,缺乏语法元素。逐渐地,符号的形式变得更加抽象,特别是当尖头书写工具被芦苇触笔取代后。通过组合旧符号来产生新含义从而创造出新符号:例如,头的符号与面包的符号结合,以产生表示吃的符号。
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由非语音的表意符号(logogram)组成。也就是说,它不是基于苏美尔语的特定声音,它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声音发音,在任何其他语言中产生相同的含义——就像数字符号4在英语、俄语、芬兰语和印尼语中分别被发音为four、chetwíre、neljä和empat一样。也许整个书写史上最重要的单一步骤是苏美尔人引入了语音表示(phonetic representation),最初是通过使用一个可描绘名词的符号来书写一个抽象名词(不容易画成图画),该可描绘名词与抽象名词具有相同的语音发音。例如,很容易画出箭的可识别图画,很难画出生命的可识别图画,但两者在苏美尔语中都发音为ti,所以箭的图画既可以表示箭也可以表示生命。由此产生的歧义通过添加一个称为限定符(determinative)的不发音符号来解决,以指示所指对象所属的名词类别。语言学家将这一决定性的创新称为谜画原理(rebus principle),它也是今天双关语的基础。
一旦苏美尔人发现了这一语音原理,他们就开始将其用于远不止书写抽象名词。他们用它来书写构成语法词尾的音节或字母。例如,在英语中,很难明显地画出常见音节-tion的图画,但我们可以画一幅说明动词shun的图画,它们发音相同。语音解释的符号也被用来”拼写”较长的单词,作为一系列图画,每个图画描绘一个音节的声音。这就好比英语使用者通过画一只蜜蜂(bee)的图画后面跟着一片叶子(leaf)的图画来书写单词believe一样。语音符号还允许抄写员对一组相关词语(如tooth、speech和speaker)使用相同的图形符号,但用额外的语音解释符号(如选择two、each或peak的符号)来消除歧义。
因此,苏美尔文字由三种类型符号的复杂混合组成:表意符号(logogram),指整个单词或名称;语音符号(phonetic sign),实际上用于拼写音节、字母、语法元素或单词的部分;以及限定符(determinative),它们不发音,但用于消除歧义。尽管如此,苏美尔文字中的语音符号远未达到完整的音节文字(syllabary)或字母表(alphabet)。一些苏美尔音节缺乏任何书写符号;同一符号可以有不同的发音;同一符号可以分别被理解为一个单词、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
除了苏美尔楔形文字之外,人类历史上另一个确定的独立起源书写系统实例来自中美洲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可能是墨西哥南部。中美洲文字被认为是独立于旧大陆文字而产生的,因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新大陆社会在诺斯人之前与拥有文字的旧大陆社会有过接触。此外,中美洲文字符号的形式与任何旧大陆文字完全不同。目前已知约有十几种中美洲文字,它们全部或大部分似乎彼此相关(例如在数字和历法系统方面),其中大多数仍只被部分破译。目前,最早保存下来的中美洲文字来自公元前6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的萨波特克地区,但目前为止最容易理解的是低地玛雅地区的文字,那里已知最早的书面日期对应于公元292年。
尽管玛雅文字起源独立且符号形式独特,但其组织原则基本上与苏美尔文字以及苏美尔启发的其他西欧亚文字系统相似。与苏美尔文字一样,玛雅文字同时使用语标符号(logogram)和表音符号(phonetic sign)。抽象词汇的语标符号通常通过字谜原则(rebus principle)衍生而来。也就是说,抽象词用另一个发音相似但含义不同且易于描绘的词的符号来书写。与日本假名和迈锡尼希腊线形文字B音节文字的符号一样,玛雅表音符号主要是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的音节符号(如ta、te、ti、to、tu)。与早期闪米特字母的字母一样,玛雅音节符号源于发音以该音节开头的物体的图画(例如,玛雅音节符号”ne”类似于尾巴,玛雅语中尾巴的词是neh)。
中美洲文字与古代西欧亚文字之间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了人类创造力在本质上的普遍性。虽然苏美尔语和中美洲语言在世界语言中没有特殊关系,但两者在将其转化为书面形式时都提出了类似的基本问题。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发明的解决方案,在世界的另一端被早期中美洲印第安人在公元前600年之前重新发明了。
除了稍后将要讨论的埃及、中国和复活节岛文字这些可能的例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代设计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苏美尔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修改而来或至少受其启发的系统的衍生物。文字独立起源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是发明文字的巨大难度,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另一个原因是,其他独立发明文字的机会被苏美尔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及其衍生物抢先了。
我们知道苏美尔文字的发展至少花费了数百年,可能数千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发展的先决条件包括人类社会的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发现文字有用,以及该社会是否能够支持必要的专业抄写员(scribe)。除了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之外,许多其他人类社会——如古印度、克里特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恰好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具备这些条件的。一旦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了文字,他们文字的细节或原则就迅速传播到其他社会,在这些社会能够经历数百年或数千年独立的文字实验之前。因此,其他独立实验的潜力被抢占或中止了。
文字的传播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发生,这两种方法在技术和思想史上都有相似之处。有人发明了某物并将其投入使用。那么,作为另一个潜在用户的你,如何为自己的使用设计类似的东西,同时知道其他人已经建造并运行了他们自己的模型?
这种发明的传播呈现出一系列形式。一端是”蓝图复制”(blueprint copying),即你复制或修改可用的详细蓝图。另一端是”理念扩散”(idea diffusion),即你只接收到基本理念,必须重新发明细节。知道某事可以做到会刺激你尝试自己去做,但你最终的具体解决方案可能与最初发明者的方案相似,也可能不相似。
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历史学家仍在争论蓝图复制还是理念扩散对俄罗斯制造原子弹贡献更大。俄罗斯的造弹努力是否关键性地依赖于间谍窃取并传送给俄罗斯的已建成的美国炸弹蓝图?还是仅仅因为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事实最终说服斯大林相信制造这种炸弹的可行性,然后俄罗斯科学家在一个独立的紧急项目中重新发明了这些原理,几乎没有来自早期美国努力的详细指导?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轮子、金字塔和火药的发展史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蓝图复制和理念扩散如何促进了书写系统的传播。
今天,专业语言学家通过蓝图复制的方法为无文字语言设计书写系统。大多数这类定制系统都是对现有字母表的修改,不过也有一些设计音节文字。例如,传教士语言学家正在为数百种新几内亚和美洲原住民语言设计改良的罗马字母表。政府语言学家设计了1928年土耳其采用的用于书写土耳其语的改良罗马字母表,以及为俄罗斯许多部落语言设计的改良西里尔字母表。
在少数情况下,我们也了解一些在遥远过去通过蓝图复制设计书写系统的个人。例如,西里尔字母本身(今天在俄罗斯仍在使用的字母)源自圣西里尔的改编,他是公元九世纪斯拉夫人的希腊传教士,改编了希腊和希伯来字母。任何日耳曼语言(包括英语的语系)的第一批保存文本是用哥特字母书写的,该字母由乌尔菲拉主教创造,他是公元四世纪居住在今天保加利亚地区的西哥特人的传教士。像圣西里尔的发明一样,乌尔菲拉的字母是从不同来源借用字母的混合体:大约20个希腊字母,大约5个罗马字母,以及两个要么取自古北欧字母要么由乌尔菲拉本人发明的字母。更多时候,我们对设计过去著名字母表的个人一无所知。但仍然可以将过去新出现的字母表与之前存在的字母表进行比较,并从字母形式推断出哪些现有字母表作为模型。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确定迈锡尼希腊的线形文字B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克里特岛米诺斯的线形文字A改编而来的。
在数百次将一种语言的现有书写系统用作蓝图来适应不同语言的情况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没有两种语言拥有完全相同的音素集。当借出语言中这些字母所代表的音在借入语言中不存在时,一些继承的字母或符号可能会被简单地删除。例如,芬兰语缺乏许多其他欧洲语言用字母b、c、f、g、w、x和z表示的音,因此芬兰人从他们的罗马字母版本中删除了这些字母。也经常出现一个相反的问题,即设计字母来表示借入语言中存在但借出语言中不存在的”新”音。这个问题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例如使用两个或多个字母的任意组合(如英语的th来表示希腊和古北欧字母用单个字母表示的音);在现有字母上添加一个小的区别标记(如西班牙语的波浪符ñ,德语的变音符ö,以及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字母周围增加的各种标记);挪用借入语言不需要的现有字母(如现代捷克人重新利用罗马字母的c来表示捷克音ts);或者只是发明一个新字母(就像我们的中世纪祖先创造新字母j、u和w时所做的那样)。
罗马字母本身是一长串蓝图复制的最终产物。字母表显然在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在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地区的闪米特语使用者中。所有数百种历史上和现在存在的字母表最终都源自那个祖先闪米特字母表,在少数情况下(如爱尔兰欧甘字母)通过理念传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实际复制和修改字母形式。
字母表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24个符号,代表24个埃及辅音。埃及人从未采取对我们来说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即丢弃所有他们的词标符号、限定符号以及代表辅音对和辅音三元组的符号,只使用他们的辅音字母表。然而,从公元前1700年左右开始,熟悉埃及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确实开始尝试这一逻辑步骤。
将符号限制为单个辅音只是区分字母表与其他书写系统的三个关键创新中的第一个。第二个是通过将字母放在固定顺序中并给它们易于记忆的名称来帮助使用者记忆字母表。我们的英语名称大多是无意义的单音节词(“a”、“bee”、“cee”、“dee”等等)。但闪米特名称在闪米特语言中确实具有意义:它们是熟悉物体的单词(aleph = 牛,beth = 房子,gimel = 骆驼,daleth = 门,等等)。这些闪米特单词与它们所指的闪米特辅音”首音相关”:也就是说,物体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以该物体命名的字母(a、b、g、d等等)。此外,闪米特字母的最早形式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这些相同物体的图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闪米特字母表的形式、名称和顺序易于记忆。许多现代字母表,包括我们的字母表,在3000多年后仍然保留了原始顺序(在希腊语的情况下,甚至保留了字母的原始名称: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只是略有修改。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小修改是,闪米特和希腊的g变成了罗马和英语的c,而罗马人在现在的位置上发明了一个新的g。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导致现代字母表产生的创新是为元音提供表示方法。早在闪米特字母表的早期,就开始了通过添加小的附加字母来标示选定的元音,或者通过在辅音字母上点缀圆点、线条或钩子来书写元音的方法实验。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成为第一个系统性地用与辅音相同类型的字母来表示所有元音的民族。希腊人通过”征用”腓尼基字母表中用于希腊语中不存在的辅音音素的五个字母,衍生出了他们的元音字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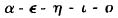 的形式。
的形式。
从那些最早的闪米特字母表开始,一条蓝图复制和进化修改的路线经由早期阿拉伯字母表发展到现代埃塞俄比亚字母表。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通过用于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阿拉米字母表,演化成现代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印度文和东南亚字母表。但对欧洲和美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路线是在公元前八世纪早期经由腓尼基人传到希腊人手中,然后在同一世纪传给伊特鲁里亚人,并在下一个世纪传给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母表经过轻微修改就是用于印刷本书的字母表。由于字母表具有将精确性与简洁性相结合的潜在优势,现在已被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所采用。
虽然蓝图复制和修改是传播技术最直接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有时并不可行。蓝图可能被保密,或者对于尚未深入掌握该技术的人来说可能无法读懂。关于某个遥远地方的发明的消息可能会逐渐传来,但细节可能无法传递。也许只有基本想法为人所知:某人以某种方式成功实现了某个最终结果。然而,这种知识可能会通过思想传播(idea diffusion)激励其他人设计出自己达到这种结果的途径。
书写历史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820年左右一位名叫塞阔雅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在阿肯色州发明的音节文字(syllabary)的起源,用于书写切罗基语。塞阔雅观察到白人在纸上做标记,并且他们通过使用这些标记来记录和重复冗长的演讲而获得了巨大优势。然而,这些标记的详细操作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像1820年以前的大多数切罗基人一样)塞阔雅是文盲,既不会说也不会读英语。因为他是一名铁匠,塞阔雅开始设计一个记账系统来帮助他追踪客户的债务。他为每个客户画一幅画像;然后画各种大小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的金额。
1810年左右,塞阔雅决定继续设计一个书写切罗基语的系统。他再次从绘画开始,但因为太复杂和对艺术要求太高而放弃了。接下来他开始为每个单词发明单独的符号,当他创造了数千个符号仍然需要更多时,又变得不满意了。
最后,塞阔雅意识到单词是由数量不多的不同音节片段组成的,这些片段在许多不同的单词中重复出现——我们称之为音节。他最初设计了200个音节符号,逐渐减少到85个,其中大多数用于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
作为符号本身的一个来源,塞阔雅练习抄写一位教师给他的英语拼写书中的字母。他的切罗基音节符号中约有二十多个直接取自这些字母,当然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塞阔雅不知道英语的含义。例如,他选择了D、R、b、h的形状分别代表切罗基音节a、e、si和ni,而数字4的形状被借用来表示音节se。他通过修改英语字母创造了其他符号,例如设计符号 、
、 和
和 分别代表音节yu、sa和na。
分别代表音节yu、sa和na。
还有一些符号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例如 、
、 和
和 分别代表ho、li和nu。塞阔雅的音节文字因其与切罗基语音的良好契合以及易于学习而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广泛赞赏。在很短的时间内,切罗基人在音节文字方面几乎达到了100%的识字率,购买了一台印刷机,将塞阔雅的符号铸成铅字,并开始印刷书籍和报纸。
分别代表ho、li和nu。塞阔雅的音节文字因其与切罗基语音的良好契合以及易于学习而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广泛赞赏。在很短的时间内,切罗基人在音节文字方面几乎达到了100%的识字率,购买了一台印刷机,将塞阔雅的符号铸成铅字,并开始印刷书籍和报纸。
切罗基文字仍然是通过思想传播产生的文字最有据可查的例子之一。我们知道塞阔雅获得了纸张和其他书写材料、书写系统的想法、使用独立标记的想法,以及几十个标记的形式。然而,由于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英语,他没有从周围现有的文字系统中获得任何细节甚至原则。被他无法理解的字母表包围,他反而独立地重新发明了音节文字,却不知道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在35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另一种音节文字。
SEQUOYAH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模型,说明观念传播(idea diffusion)可能如何导致了古代许多书写系统的产生。朝鲜世宗大王在公元1446年为朝鲜语设计的韩文字母显然受到了汉字块状格式以及蒙古或藏传佛教文字字母原则的启发。然而,世宗大王发明了韩文字母的形式和他的字母系统的几个独特特征,包括按音节将字母分组成方块、使用相关的字母形状来表示相关的元音或辅音、以及辅音字母的形状描绘发音时嘴唇或舌头的位置。从公元四世纪左右开始在爱尔兰和凯尔特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甘字母同样采用了字母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现有的欧洲字母),但又设计了独特的字母形式,显然基于五指手势系统。
我们可以自信地将韩文和欧甘字母归因于观念传播而非孤立的独立发明,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社会都与拥有文字的社会有密切接触,并且清楚哪些外国文字提供了灵感。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自信地将苏美尔楔形文字和最早的中美洲文字归因于独立发明,因为在它们首次出现时,各自所在的半球不存在其他可以启发它们的文字。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的文字起源仍存在争议。
生活在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字,最早保存下来的例子只能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远在欧洲人于1722年到达复活节岛之后。也许文字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复活节岛上独立产生,尽管没有例子保存下来。但最直接的解释是按字面理解这些事实,并假设复活节岛民在看到1770年西班牙探险队递给他们的吞并宣言后受到启发而设计了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最早见证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可能有更早的前身,它也有独特的本地符号和一些独特的原则,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独立演化的。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已在距早期中国城市中心4000英里以西的苏美尔发展起来,并于公元前2200年出现在2600英里以西的印度河流域,但在印度河流域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已知的早期书写系统。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最早的中国书写者可能知道任何其他可以启发他们的书写系统。
埃及象形文字是所有古代书写系统中最著名的,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发明的产物,但观念传播的替代解释比中国文字的情况更可行。象形文字的出现相当突然,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几乎以完全成熟的形式出现。埃及距离苏美尔只有800英里,与苏美尔有贸易往来。我发现可疑的是,没有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证据流传下来,尽管埃及干燥的气候本应有利于保存早期的文字实验,而且苏美尔类似的干燥气候已经产生了大量证据,证明苏美尔楔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至少发展了几个世纪。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和埃及文字兴起之后,伊朗、克里特岛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是独立设计的书写系统(分别是所谓的原始埃兰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和象形赫梯文字)。尽管每个系统都使用了不同于埃及或苏美尔的独特符号集,但相关民族不可能不知道其贸易伙伴邻国的文字。
如果在人类存在数百万年没有文字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恰好在几个世纪内独立地想到了文字的想法,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观念传播,就像塞阔雅音节文字的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文字的想法,可能还有一些原则,然后自己设计了其他原则和所有字母的具体形式。
L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一些社会中产生并传播到这些社会,而在许多其他社会中却没有?我们讨论的便利起点是早期书写系统有限的能力、用途和使用者。
早期的文字是不完整的、模糊的或复杂的,或者三者兼具。例如,最古老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无法书写正常的散文,而只是一种简略的电报式速记,其词汇仅限于名字、数字、度量单位、被计数物体的词汇以及少数形容词。这就好比现代美国法院书记员被迫写”约翰 27 肥羊”,因为英语书写缺乏必要的词汇和语法来写”我们命令约翰交付他欠政府的27只肥羊。“后来的苏美尔楔形文字确实能够书写散文了,但它是通过我已经描述过的混乱系统来实现的,混合了意符、表音符号和不发音的限定符,总共有数百个独立的符号。迈锡尼希腊的线形文字B至少更简单一些,它基于大约90个音节符号加上意符。与这一优点相抵消的是,线形文字B相当模糊。它省略了词尾的任何辅音,并且对几个相关辅音使用相同的符号(例如,一个符号同时代表l和r,另一个代表p和b和ph,还有一个代表g和k和kh)。我们知道,当日本本土人说英语时不区分l和r,我们会感到多么困惑: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字母表也这样做,同时类似地同质化我提到的其他辅音,会有多么混乱!这就好像我们把”rap”、“lap”、“lab”和”laugh”这些词拼写得完全相同。
一个相关的局限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文字。书写知识仅限于为国王或神庙服务的专业抄写员。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线形文字B被宫廷官僚小群体之外的任何迈锡尼希腊人使用或理解。由于可以通过保存文件上的笔迹来区分个别线形文字B抄写员,我们可以说,从克诺索斯和皮洛斯宫殿保存下来的所有线形文字B文件分别只是75位和40位抄写员的作品。
这些电报式的、笨拙的、模糊的早期文字的用途与其使用者的数量一样受限。任何希望发现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人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人都会失望。相反,最早的苏美尔文本是宫廷和神庙官僚毫无感情的记录。在已知最早的苏美尔档案(来自乌鲁克城)中,大约90%的泥板是支付的货物、获得口粮的工人和分配的农产品的文书记录。只是后来,当苏美尔人从意符发展到表音文字时,他们才开始书写散文叙事,如宣传和神话。
迈锡尼希腊人甚至从未达到那个宣传和神话阶段。克诺索斯宫殿所有线形文字B泥板中有三分之一是会计对羊和羊毛的记录,而皮洛斯宫殿不成比例的大量书写内容是亚麻的记录。线形文字B本质上非常模糊,以至于它仍然局限于宫廷账目,其上下文和有限的词汇选择使解释变得清晰。没有一丝它用于文学的痕迹保存下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识字的吟游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和传播的,直到数百年后希腊字母表发展起来才被书面记录下来。
类似的受限用途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征。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宗教和国家宣传以及官僚账目。保存下来的玛雅文字同样致力于宣传、国王的出生、即位和胜利,以及祭司的天文观测。商代晚期最古老的中国文字由关于王朝事务的宗教占卜组成,刻在所谓的甲骨上。一个商代文本样本:“王,读裂纹(加热骨头产生的裂纹)的意义,说:‘如果孩子出生在庚日,将极为吉祥。’”
对我们今天来说,很容易问为什么拥有早期书写系统的社会接受了将书写限制在少数功能和少数抄写员身上的模糊性。但即使提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古代视角与我们对大众识字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书写的预期受限用途为设计更清晰的书写系统提供了积极的抑制因素。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希望书写被专业抄写员用来记录税收中欠的羊的数量,而不是被大众用来写诗和策划阴谋。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古代书写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对其他人的奴役。“非专业人员对书写的个人使用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出现,随着书写系统变得更简单、更具表现力。
例如,随着迈锡尼希腊文明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衰落,线形文字B消失了,希腊重新进入了前文字时代。当文字最终在公元前8世纪重新回到希腊时,新的希腊文字、其使用者及其用途都大不相同。这种文字不再是混合了表意符号的模糊音节文字,而是从腓尼基辅音字母借用而来并通过希腊人发明元音而改进的字母表。希腊字母文字从出现之初就不再是只有抄写员能辨认、只在宫殿中阅读的羊群清单,而是承载诗歌和幽默的载体,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例如,希腊字母文字现存最早的例子刻在公元前740年左右的雅典酒壶上,是一行宣布舞蹈比赛的诗句:“所有舞者中谁表演得最灵巧,谁就将赢得这个花瓶作为奖品。”下一个例子是刻在饮酒杯上的三行扬抑抑格六音步诗句:“我是涅斯托耳美味的饮酒杯。谁从这个杯子喝酒,戴着美丽花冠的阿佛洛狄忒的欲望就会迅速抓住他。”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表现存最早的例子也是刻在饮酒杯和酒器上的铭文。只是到了后来,这种易于学习的私人交流工具才被征用于公共或官僚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序列与早期表意文字和音节文字系统的发展序列相反。
早期文字有限的用途和使用者表明了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晚。所有可能的或已知的文字独立发明(在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以及所有对这些已发明系统的早期改编(例如在克里特、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流域和玛雅地区),都涉及社会分层的、具有复杂集中政治制度的社会,这些制度与粮食生产的必然关系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探讨。早期文字服务于这些政治制度的需要(如记录保存和王室宣传),使用者是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种植的储存粮食盈余供养的全职官僚。狩猎采集社会从未发展甚至采用文字,因为他们既缺乏早期文字的制度用途,也缺乏产生供养抄写员所需粮食盈余的社会和农业机制。
因此,粮食生产及其采用后数千年的社会演化,对于文字的进化就像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病的微生物的进化一样至关重要。文字只在新月沃土、墨西哥以及可能的中国独立产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是各自半球中最早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一旦文字被这些少数社会发明出来,它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传播到具有类似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其他社会。
虽然粮食生产因此是文字演化或早期采用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在本章开头,我提到了一些在现代之前未能发展或采用文字的、具有复杂政治组织的粮食生产社会。这些案例最初让我们这些习惯于将文字视为复杂社会不可或缺的现代人感到困惑,包括截至公元1520年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它们还包括汤加的海上准帝国、18世纪末出现的夏威夷国家、伊斯兰教到来之前赤道以南非洲和撒哈拉以南西非的所有国家和酋邦,以及北美最大的土著社会——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的社会。为什么所有这些社会都未能获得文字,尽管它们与那些获得文字的社会共享先决条件?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绝大多数拥有文字的社会是通过从邻居那里借用文字或受其启发而发展文字来获得文字的,而不是通过自己独立发明文字。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是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起步较晚的社会。(这个陈述中唯一的不确定性涉及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最终的印加领地——粮食生产开始的相对日期。)假以时日,这些缺乏文字的社会最终也可能自行发展出文字。如果它们位于更靠近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的地方,它们可能会像印度、玛雅和大多数其他拥有文字的社会那样,从这些中心获得文字或文字的概念。但它们距离最早的文字中心太远,无法在现代之前获得文字。
隔离的重要性在夏威夷和汤加最为明显,这两个地方距离最近的拥有文字的社会至少有4000英里的海洋相隔。其他社会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直线距离对人类来说并不是衡量隔离程度的合适标准。安第斯山脉、西非的王国和密西西比河口距离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拥有文字的社会分别只有约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这些距离远远小于字母表从其发源地地中海东岸传播到爱尔兰、埃塞俄比亚和东南亚所需要跨越的距离,而后者在发明后的2000年内就完成了。但是人类会被乌鸦可以飞越的生态和水域障碍所阻挡。北非的国家(有文字)和西非(没有文字)被不适合农业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隔开。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同样将墨西哥南部的城市中心与密西西比河谷的酋邦分隔开来。墨西哥南部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的交流要么需要海上航行,要么需要通过狭窄、森林密布、从未城市化的达连地峡进行漫长的陆路接触链。因此,安第斯山脉、西非和密西西比河谷实际上与拥有文字的社会相当隔离。
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完全孤立。西非最终确实通过撒哈拉接收到了肥沃月弯的家养动物,后来还接受了伊斯兰影响,包括阿拉伯文字。玉米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及更缓慢地从墨西哥传播到密西西比河谷。但我们在第10章已经看到,非洲和美洲内部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延缓了作物和家养动物的传播。文字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地理和生态以类似的方式影响人类发明的传播。
1908年7月3日,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法伊斯托斯古代米诺斯宫殿进行发掘时,偶然发现了技术史上最非凡的物品之一。乍一看,它似乎并不起眼:只是一个小而扁平、未上色的圆形硬烤陶土盘,直径6½英寸。仔细观察发现,两面都覆盖着文字,位于一条从盘子边缘顺时针螺旋向中心盘绕五圈的曲线上。总共241个符号或字母被蚀刻的垂直线整齐地分成若干组,每组包含几个符号,可能构成单词。书写者必定仔细规划和执行了这个盘子,从边缘开始书写,填满螺旋线上所有可用空间,但到达中心时又不会用完空间(第13章)。
自从出土以来,这个盘子一直给文字史学家带来谜团。不同符号的数量(45个)表明这是一种音节文字而不是字母表,但它仍未被破译,符号的形式与任何其他已知书写系统都不同。自发现以来的89年里,再也没有发现这种奇怪文字的其他碎片。因此,它究竟代表克里特岛本土文字还是外来文字仍然未知。
对于技术史学家来说,法伊斯托斯圆盘更加令人困惑;其估计日期公元前1700年使其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印刷文件。与克里特岛后来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的所有文本都是手工蚀刻不同,圆盘上的符号是用印章压印到软陶土上(随后烧硬)的,这些印章上有凸起的符号作为活字。印刷者显然拥有一套至少45个印章,圆盘上出现的每个符号都有一个。制作这些印章必定需要大量工作,它们肯定不是仅仅为了印刷这一份文件而制造的。使用它们的人大概在做大量的书写工作。有了这些印章,它们的主人可以比手工写出文字的每个复杂符号更快、更整洁地制作副本。
法伊斯托斯圆盘预示了人类下一次印刷努力,同样使用雕刻的活字或木板,但将它们用墨水印在纸上,而不是不用墨水印在陶土上。然而,这些下一次努力直到2500年后才出现在中国,3100年后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为什么圆盘这种早熟的技术没有在克里特岛或古地中海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用?为什么它的印刷方法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克里特岛发明,而不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或其他任何古代文字中心的其他时间发明?为什么之后又花了数千年才加上墨水和印刷机的想法,最终发展出印刷机?因此,圆盘对历史学家构成了一个威胁性的挑战。如果发明像圆盘所暗示的那样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对技术史进行概括的努力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技术,以武器和运输工具的形式,为某些民族扩张领土和征服其他民族提供了直接手段。这使它成为历史最广泛模式的主要原因。但为什么是欧亚人,而不是美洲原住民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发明了火器、远洋船只和钢铁装备?这些差异延伸到大多数其他重要的技术进步,从印刷机到玻璃和蒸汽机。为什么所有这些发明都来自欧亚大陆?为什么到公元1800年,所有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就像欧亚大陆和大部分非洲数千年前丢弃的那些,尽管世界上最丰富的铜矿和铁矿分别位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事实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普通人认为欧亚人在发明创造和智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
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这种人类神经生物学上的差异来解释大陆间技术发展的差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另一种观点依赖于英雄发明理论(heroic theory of invention)。技术进步似乎不成比例地来自少数极为罕见的天才,如约翰内斯·古腾堡、詹姆斯·瓦特、托马斯·爱迪生和莱特兄弟。他们是欧洲人,或是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后裔。古代的阿基米德和其他罕见天才也是如此。这样的天才能否同样在塔斯马尼亚或纳米比亚出生?技术史是否仅仅取决于几位发明家出生地的偶然性?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个人发明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创新的接受度问题。有些社会似乎极端保守、内向且抵制变革。这是许多试图帮助第三世界人民却最终感到沮丧的西方人的印象。这些人作为个体似乎完全聪明;问题似乎在于他们的社会。否则如何解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土著人未能采用弓箭,尽管他们看到与他们贸易的托雷斯海峡岛民在使用弓箭?整个大陆的所有社会是否都不接受创新,从而解释了那里技术发展的缓慢步伐?在本章中,我们将最终解决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技术在不同大陆上以如此不同的速度演化?
我们讨论的起点是俗语”需求是发明之母”所表达的常见观点。也就是说,发明据称是在社会有未满足的需求时产生的:某些技术被广泛认为不令人满意或有局限性。潜在的发明家,受金钱或名声前景的驱使,察觉到这种需求并试图满足它。最终某位发明家想出了优于现有不令人满意技术的解决方案。如果该解决方案与社会的价值观和其他技术兼容,社会就会采用它。
确实有相当多的发明符合这种常识性观点,即需求是发明之母。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明确目标是在纳粹德国之前发明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技术。该项目在三年内成功,耗资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多亿美元)。其他例子包括伊莱·惠特尼1794年发明轧棉机以取代美国南方种植棉花的费力手工清理,以及詹姆斯·瓦特1769年发明蒸汽机以解决英国煤矿抽水问题。
这些熟悉的例子欺骗我们认为其他重大发明也是对感知需求的回应。事实上,许多或大多数发明是由好奇心或喜欢摆弄东西的人开发的,在对他们心中的产品没有任何初始需求的情况下。一旦设备被发明出来,发明家就必须为它找到应用。只有在使用了相当长时间后,消费者才会觉得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设备,为服务一个目的而发明,最终发现它们的大部分用途是用于其他未预料到的目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寻找用途的发明包括现代大多数重大技术突破,从飞机和汽车,到内燃机和电灯泡,再到留声机和晶体管。因此,发明往往是需求之母,而不是相反。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托马斯·爱迪生留声机的历史,这是现代最伟大发明家最原创的发明。当爱迪生在1877年制造出他的第一台留声机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他的发明可能用于的十种用途。它们包括保存垂死之人的遗言、为盲人录制书籍供其收听、报时和教授拼写。音乐复制在爱迪生的优先级列表上并不高。几年后,爱迪生告诉他的助手,他的发明没有商业价值。又过了几年,他改变了主意,确实进入商界销售留声机——但用作办公室口述机。当其他企业家通过安排留声机投币播放流行音乐来创造自动点唱机时,爱迪生反对这种贬低,这显然削弱了他发明的严肃办公用途。直到大约20年后,爱迪生才不情愿地承认他的留声机的主要用途是录制和播放音乐。
汽车是另一项在今天看来用途显而易见的发明。然而,它并非因为某种需求而被发明出来的。当尼古拉斯·奥托在1866年制造出他的第一台燃气发动机时,马匹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近6000年的陆地交通服务,而蒸汽动力铁路也在几十年间不断补充这一需求。当时既没有马匹供应危机,也没有人对铁路不满。
由于奥托的发动机动力弱、笨重且有七英尺高,它并没有比马匹更具优势。直到1885年,发动机才改进到让戈特利布·戴姆勒将其安装在自行车上,创造出第一辆摩托车的程度;他一直等到1896年才制造出第一辆卡车。
1905年,汽车仍然是昂贵、不可靠的富人玩具。公众对马匹和铁路的满意度一直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认为他们确实需要卡车。战后卡车制造商和军队的密集游说终于说服公众认识到自己的需求,使卡车开始在工业化国家取代马车。即使在美国最大的城市,这种转变也花了50年时间。
发明家往往必须在缺乏公众需求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他们的钻研,因为早期型号性能太差而无法使用。最早的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就像奥托那台七英尺高的燃气发动机一样糟糕。这使得发明家很难预见他或她糟糕的原型最终是否会找到用途,从而值得投入更多时间和费用来开发它。美国每年颁发约70000项专利,其中只有少数最终进入商业生产阶段。对于每一项最终找到用途的伟大发明,都有无数其他发明没有找到用途。即使是为最初设计目的而满足需求的发明,后来也可能在满足未预见的需求方面更有价值。虽然詹姆斯·瓦特设计他的蒸汽机是为了从矿井中抽水,但它很快就为棉纺厂提供动力,然后(获得更大利润)推动机车和船只前进。
因此,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常识性发明观颠倒了发明和需求的通常角色。它也夸大了像瓦特和爱迪生这样罕见天才的重要性。这种”英雄发明理论”受到专利法的鼓励,因为专利申请人必须证明所提交发明的新颖性。发明家因此有经济动机贬低或忽视先前的工作。从专利律师的角度来看,理想的发明是没有任何前身的发明,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前额完全成形地跳出来一样。
实际上,即使是最著名和看似最具决定性的现代发明,在”X发明了Y”的简单声明背后也潜藏着被忽视的前身。例如,我们经常被告知”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是受到观看茶壶嘴冒出蒸汽的启发。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精彩的虚构故事,瓦特实际上是在修理托马斯·纽科门的蒸汽机模型时获得他特定蒸汽机的想法,纽科门在57年前就发明了这种蒸汽机,到瓦特进行修理工作时,英国已经制造了一百多台。纽科门的发动机又是在英国人托马斯·萨维里1698年获得专利的蒸汽机之后,萨维里的蒸汽机又是在法国人丹尼斯·帕潘1680年左右设计(但没有制造)的蒸汽机之后,帕潘的蒸汽机又有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等人的想法作为前身。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大大改进了纽科门的发动机(通过加入独立的蒸汽冷凝器和双作用汽缸),正如纽科门大大改进了萨维里的发动机一样。
所有有充分记录的现代发明都可以讲述类似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发明功臣的英雄追随着之前的发明家,这些发明家有着相似的目标,并且已经制作出设计图、工作模型,或者(就像纽科门蒸汽机的情况)商业上成功的模型。爱迪生在1879年10月21日晚上著名的白炽灯泡”发明”,是在1841年至1878年间其他发明家获得专利的许多其他白炽灯泡基础上的改进。同样,莱特兄弟的载人动力飞机之前有奥托·李林塔尔的载人无动力滑翔机和塞缪尔·兰利的无人动力飞机;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之前有约瑟夫·亨利、威廉·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的电报;伊莱·惠特尼用于清理短纤维(内陆)棉花的轧棉机是对已经清理长纤维(海岛)棉花数千年的轧棉机的延伸。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爱迪生、莱特兄弟、莫尔斯和惠特尼做出了重大改进,从而增加或开创了商业成功。如果没有公认发明家的贡献,最终采用的发明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对于我们的目的,问题是:如果某个天才发明家没有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出生,世界历史的广泛模式是否会发生重大改变。答案很清楚: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有能力的前辈和继任者,并且在社会能够使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做出了改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完善费斯托斯圆盘上使用的印章的英雄的悲剧在于,他或她设计出了当时社会无法大规模利用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我的例子都取自现代技术,因为它们的历史记录详实。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是累积发展的,而非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的大部分用途是在发明之后才被发现的,而不是为了满足预见的需求而发明的。这些结论对于缺乏文献记载的古代技术史显然更加适用。当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注意到他们火堆中烧焦的沙子和石灰石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漫长而偶然的发现积累,这些发现将通过最早的表面釉面物品(约公元前4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独立玻璃物品(约公元前2500年)以及最早的玻璃器皿(约公元前1500年),最终导致第一批罗马玻璃窗的出现(约公元1年)。
我们对那些最早已知的表面釉面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今天技术”原始”的人群来推断史前发明的方法,比如和我一起工作的新几内亚人。我已经提到过他们对数百种当地动植物物种的了解,以及每个物种的可食性、药用价值和其他用途。新几内亚人同样告诉我关于他们环境中几十种岩石类型的知识,包括每种岩石的硬度、颜色、敲击或剥离时的表现以及用途。所有这些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反复试验获得的。每当我带新几内亚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时,我都能看到这种”发明”过程的进行。他们不断在森林中捡起不熟悉的东西,摆弄它们,偶尔发现它们足够有用就带回家。当我离开营地时,我也能看到同样的过程,当地人会来搜寻剩下的东西。他们玩弄我丢弃的物品,试图弄清楚它们在新几内亚社会中是否有用。废弃的锡罐很简单:它们最终被重新用作容器。其他物品则被测试用于与其制造目的截然不同的用途。那支黄色的2号铅笔作为装饰品会是什么样子,穿过耳垂或鼻中隔上的穿孔?那块碎玻璃是否足够锋利和坚固,可以用作刀具?找到了!
古代人们可用的原材料是天然材料,如石头、木材、骨头、皮革、纤维、粘土、沙子、石灰石和矿物,所有这些都有很大的多样性。从这些材料中,人们逐渐学会将特定类型的石头、木材和骨头加工成工具;将特定的粘土转化为陶器和砖块;将沙子、石灰石和其他”泥土”的特定混合物转化为玻璃;并加工可用的纯软金属如铜和金,然后从矿石中提取金属,最终加工硬金属如青铜和铁。
反复试验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从原材料发展出火药和汽油的过程。可燃的天然产品不可避免地引起注意,比如当一根含树脂的原木在篝火中爆炸时。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通过加热岩石沥青来提取数吨石油。古希腊人发现了石油、沥青、树脂、硫磺和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作为燃烧武器的用途,通过投石机、箭、燃烧弹和船只投放。中世纪伊斯兰炼金术士为生产酒精和香水而发展的蒸馏专业技术,也让他们能够将石油蒸馏成馏分,其中一些被证明是更强大的燃烧剂。这些燃烧剂通过手榴弹、火箭和鱼雷投放,在伊斯兰最终击败十字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到那时,中国人已经观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特定混合物(后来被称为火药)特别具有爆炸性。约公元1100年的一份伊斯兰化学论文描述了七种火药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份论文给出了70多种被证明适用于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种用于火箭,另一种用于大炮)。
至于中世纪后的石油蒸馏,19世纪的化学家发现中间馏分可用作油灯燃料。化学家们将最易挥发的馏分(汽油)作为不幸的废弃产品丢弃——直到它被发现是内燃机的理想燃料。今天还有谁记得,现代文明的燃料汽油,起源于又一项寻找用途的发明?
一旦发明者为新技术找到了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接受它。仅仅拥有一个更大、更快、更强大的设备来做某事,并不能保证被轻易接受。无数这样的技术要么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抵制后才被采用。臭名昭著的例子包括美国国会在1971年拒绝为开发超音速运输机提供资金、世界对高效设计的打字机键盘的持续拒绝,以及英国长期不愿采用电力照明。是什么促进了社会对发明的接受?
让我们从比较同一社会内不同发明的可接受性开始。事实证明,至少有四个因素影响接受度。
与现有技术相比,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相对经济优势(economic advantage)。虽然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原住民发明了带轴的轮式车辆用作玩具,但不用于运输。这对我们来说似乎难以置信,直到我们想到古代墨西哥人缺乏可以套在轮式车辆上的驯化动物,因此轮式车辆相比人力搬运工并无优势。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社会价值和声望,它可以超越经济利益(或缺乏经济利益)。今天数百万人购买设计师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用的普通牛仔裤的两倍——因为设计师标签的社会声望比额外的成本更重要。同样,日本继续使用其极其繁琐的汉字书写系统,而不是高效的字母表或日本自己高效的假名音节文字——因为汉字所附带的声望是如此之高。
另一个因素是与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的兼容性。这本书,就像你可能读过的其他所有打字文档一样,是用QWERTY键盘打字的,以其上排最左边的六个字母命名。现在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但这种键盘布局是在1873年作为反工程(anti-engineering)的壮举设计的。它采用了一系列反常的技巧,旨在迫使打字员尽可能慢地打字,例如将最常见的字母分散在所有键盘行上,并将它们集中在左侧(右撇子必须使用较弱的手)。所有这些看似适得其反的特征背后的原因是,1873年的打字机如果快速连续敲击相邻的键就会卡住,因此制造商不得不让打字员放慢速度。当打字机的改进消除了卡住的问题时,1932年对高效布局键盘的试验表明,它可以让我们的打字速度提高一倍,并将打字工作量减少95%。但那时QWERTY键盘已经根深蒂固。数亿QWERTY打字员、打字教师、打字机和计算机销售人员以及制造商的既得利益在60多年里粉碎了所有提高键盘效率的举措。
虽然QWERTY键盘的故事听起来可能很有趣,但许多类似的案例涉及更严重的经济后果。为什么日本现在主导着晶体管电子消费产品的世界市场,其程度损害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尽管晶体管是在美国发明和获得专利的?因为索尼从西部电气公司购买了晶体管许可权,当时美国电子消费行业正在大量生产真空管型号,不愿与自己的产品竞争。为什么英国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仍在使用煤气路灯,远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已经转换为电路灯之后?因为英国市政府在煤气照明方面投资巨大,并为竞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监管障碍。
影响新技术接受度的其余考虑因素是观察其优势的难易程度。公元1340年,当火器尚未到达欧洲大部分地区时,英格兰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恰好在西班牙出席了塔里法战役,阿拉伯人在那里对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伯爵们对所见印象深刻,将大炮引入英国军队,军队热情地采用了它们,六年后在克雷西战役中已经对法国士兵使用它们。
因此,轮子、设计师牛仔裤和QWERTY键盘说明了同一社会对所有发明并非同等接受的各种原因。相反,同一发明在当代社会中的接受度也有很大差异。我们都熟悉所谓的概括,即农村第三世界社会对创新的接受度低于西方化的工业社会。即使在工业化世界内部,一些地区也比其他地区更容易接受。如果这种差异存在于大陆规模上,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技术在某些大陆上比其他大陆发展得更快。例如,如果所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由于某种原因一致抵制变革,这可能解释了他们在其他所有大陆都出现金属工具后继续使用石器。社会之间接受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技术史学家提出了至少14个解释因素的清单。一个是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长,原则上应该给潜在的发明家积累技术知识所需的年限,以及开始长期开发计划(产生延迟回报)的耐心和安全感。因此,现代医学带来的大幅增加的预期寿命可能促进了最近加速的发明步伐。
接下来的五个因素涉及经济学或社会组织:(1) 古典时代廉价奴隶劳动力的可用性据称阻碍了当时的创新,而现在的高工资或劳动力短缺则刺激了对技术解决方案的探索。例如,移民政策可能改变并切断墨西哥季节性劳动力向加州农场供应的前景,成为加州开发可机器收割番茄品种的直接动力。(2) 专利和其他产权法律保护发明者的所有权,在现代西方奖励创新,而缺乏这种保护则在现代中国阻碍创新。(3) 现代工业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技术培训机会,正如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所做的那样,而现代扎伊尔则没有。(4) 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使得在技术开发中投资资本具有潜在回报价值,而古罗马经济则不是这样组织的。(5) 美国社会的强烈个人主义允许成功的发明者为自己保留收益,而新几内亚的强大家族纽带确保了开始赚钱的人会有十几个亲戚加入,期望搬进来并得到供养和支持。
另外四个建议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性的,而非经济或组织性的:(1) 冒险行为对创新努力至关重要,在某些社会中比在其他社会中更为普遍。(2) 科学观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的独特特征,对其现代技术卓越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3) 对不同观点和异端的宽容促进创新,而强烈的传统观念(如中国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强调)则抑制创新。(4) 宗教在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差异很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分支被认为特别兼容,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某些分支可能特别不兼容。
所有这十个假设都是合理的。但它们中没有一个与地理有任何必然联系。如果专利权、资本主义和某些宗教确实促进技术,那么是什么在中世纪后的欧洲而不是在当代中国或印度选择了这些因素?
至少这十个因素影响技术的方向似乎是明确的。剩余的四个提议因素——战争、中央集权政府、气候和资源丰度——似乎表现不一致:有时它们刺激技术,有时它们抑制技术。(1) 纵观历史,战争常常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刺激因素。例如,二战期间在核武器上的巨额投资以及一战期间在飞机和卡车上的投资,开启了全新的技术领域。但战争也可能对技术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挫折。(2) 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在19世纪末的德国和日本促进了技术,而在公元1500年后的中国却摧毁了技术。(3) 许多北欧人认为,技术在严酷的气候中繁荣,在那里没有技术就无法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中则枯萎,那里不需要衣服,香蕉据说会从树上掉下来。相反的观点是,温和的环境使人们摆脱了持续的生存斗争,可以自由地致力于创新。(4) 关于技术是由环境资源的丰富还是稀缺所刺激,也一直存在争论。丰富的资源可能刺激利用这些资源的发明的发展,例如多雨的北欧及其众多河流的水磨技术——但为什么水磨技术在雨水更多的新几内亚没有更快地发展?英国森林的破坏被认为是其在开发煤炭技术方面早期领先的原因,但为什么森林砍伐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
这次讨论并未穷尽为解释为什么社会在接受新技术方面存在差异而提出的原因清单。更糟糕的是,所有这些近因解释都绕过了它们背后的根本因素问题。这在我们试图理解历史进程时似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因为技术无疑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然而,我现在要论证的是,技术创新背后独立因素的多样性实际上使理解历史的广泛模式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难。
对于本书的目的而言,关于这个清单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因素在各大陆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从而导致技术发展的大陆差异。大多数普通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明确或默认地假设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作为一个群体共享导致其技术落后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据称(或者说是)保守,生活在想象中的创世梦幻时代(Dreamtime)的过去,而不专注于改善现在的实际方法。一位非洲历史的主要历史学家将非洲人描述为内向的,缺乏欧洲人的扩张驱动力。
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基于纯粹的推测。从来没有对两个大陆上相似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许多社会进行研究,证明两个大陆人民之间存在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差异。通常的推理反而是循环的:因为技术差异存在,所以推断存在相应的意识形态差异。
实际上,我经常在新几内亚观察到,那里的原住民社会在普遍的思想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就像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传统的新几内亚既有抵制新方法的保守社会,也有选择性采纳新方法的创新社会并存。结果是,随着西方技术的到来,更具创业精神的社会现在正在利用西方技术来压倒他们的保守邻居。
例如,当欧洲人在1930年代首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地时,他们”发现”了数十个此前未接触过的石器时代部落,其中钦布(Chimbu)部落在采用西方技术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定居者种植咖啡时,他们自己也开始种植咖啡作为经济作物。1964年,我遇到了一位50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草裙,出生在一个仍在使用石器工具的社会,但他通过种植咖啡致富,用利润花10万美元现金购买了一台锯木厂,并买了一队卡车将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相比之下,我与之工作了八年的邻近高地民族达里比(Daribi)人特别保守,对新技术不感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降落在达里比地区时,他们只是简单地看了看,然后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而钦布人可能已经在讨价还价租用它了。结果,钦布人现在正在迁入达里比地区,将其用于种植园,并使达里比人沦为为他们工作。
在其他大陆上,某些原住民社会也证明非常善于接受,选择性地采用外来方法和技术,并成功地将它们融入自己的社会。在尼日利亚,伊博(Ibo)人成为当地创业精神的代表,相当于新几内亚的钦布人。今天,美国人口最多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是纳瓦霍(Navajo)人,而在欧洲人到来时,他们只是数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但纳瓦霍人证明特别有韧性,能够选择性地处理创新。他们将西方染料融入编织中,成为银匠和牧场主,现在开着卡车,同时继续住在传统住所中。
在据说保守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中,也有接受性强的社会与保守的社会并存。一个极端是,塔斯马尼亚人继续使用在欧洲已被淘汰数万年、在澳大利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也被取代的石器工具。另一个极端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些原住民捕鱼群体设计了精细的技术来管理鱼类种群,包括建造运河、堰坝和固定捕鱼器。
因此,同一大陆上不同社会对发明的开发和接受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在同一社会内部也随时间而变化。如今,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对保守,并非处于技术前沿。但同一地区的中世纪伊斯兰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对创新持开放态度。它实现的识字率远高于同时代的欧洲;它吸收了古典希腊文明的遗产,许多古典希腊书籍现在仅通过阿拉伯语副本为我们所知;它发明或完善了风车、潮汐磨坊、三角学和三角帆;它在冶金、机械和化学工程以及灌溉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从中国采用了纸张和火药,并将它们传播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流动压倒性地从伊斯兰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流动的净方向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创新也随时间明显波动。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具创新性和先进性,甚至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中国发明的长长清单包括运河船闸、铸铁、深钻、高效动物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纸张、瓷器、印刷术(费斯托斯圆盘除外)、船尾舵和独轮车。然后中国停止了创新,原因我们将在尾声中推测。相反,我们认为西欧及其衍生的北美社会在技术创新方面引领现代世界,但直到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技术还不如旧世界任何其他”文明”地区先进。
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倾向于创新,而有些大陆的社会倾向于保守是不正确的。在任何大陆,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有创新社会和保守社会。此外,对创新的接受度在同一地区内随时间波动。
经过反思,这些结论恰恰符合人们的预期: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是由许多独立因素决定的,那么在没有详细了解所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创新能力就变得不可预测。因此,社会科学家们继续争论伊斯兰世界、中国和欧洲接受度变化的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钦布人、伊博人和纳瓦霍人比他们的邻居更愿意接受新技术。不过,对于研究广泛历史模式的学者来说,每个案例的具体原因并不重要。影响创新能力的无数因素反而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更容易,因为它们将社会创新能力的差异本质上转化为一个随机变量。这意味着,在足够大的区域(比如整个大陆)的任何特定时期,总会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具有创新性。
创新究竟从何而来?除了少数完全与世隔绝的过去社会之外,对于所有社会来说,大部分或大多数新技术并非本地发明,而是从其他社会借鉴而来。本地发明和借鉴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特定技术的发明难易程度,以及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有些发明直接来自对天然原材料的处理。这类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独立出现过多次,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和时期。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一个例子是植物驯化,它至少有九个独立起源。另一个例子是陶器,它可能源于对粘土这种非常普遍的天然材料在干燥或加热时行为的观察。陶器大约在14000年前出现在日本,大约在10000年前出现在肥沃月湾和中国,之后出现在亚马逊、非洲萨赫勒地区、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
一个复杂得多的发明例子是文字,它不会通过观察任何天然材料而自然产生。正如我们在第12章看到的,文字只有少数几个独立起源,而字母表在世界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一次。其他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旋转手磨、齿轮传动、磁罗盘、风车和暗箱(camera obscura),所有这些都只在旧大陆发明过一次或两次,在新大陆从未出现过。
这类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通过借鉴获得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比在本地独立发明的速度更快。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轮子,它首次出现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的黑海附近,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早期旧大陆的轮子都有一个独特的设计:一个由三块木板固定在一起构成的实心木圆盘,而不是带辐条的轮辋。相比之下,美洲原住民社会唯一的轮子(在墨西哥陶瓷器皿上描绘)是由一整块材料制成的,这表明轮子是第二次独立发明——正如其他证据所表明的新大陆与旧大陆文明的隔离状态。
没有人认为,在700万年没有轮子的人类历史之后,这种独特的旧大陆轮子设计会在几个世纪内偶然地在旧大陆的许多不同地点反复出现。相反,轮子的实用性肯定使它从唯一的发明地点迅速向东西方向扩散到整个旧大陆。其他从西亚单一源头向东西方向扩散到古代旧大陆的复杂技术例子包括门锁、滑轮、旋转手磨、风车——以及字母表。新大陆技术扩散的一个例子是冶金术,它从安第斯山脉经由巴拿马传播到中美洲。
当一项广泛有用的发明确实在某个社会中出现时,它往往会通过两种方式之一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了解到这项发明,接受它,并采用它。第二种方式是缺乏这项发明的社会发现自己相对于发明社会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劣势足够大,它们就会被压倒和取代。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火枪在新西兰毛利部落之间的传播。一个部落,恩加普希人(Ngapuhi),大约在1818年从欧洲商人那里获得了火枪。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新西兰被所谓的”火枪战争”所动荡,没有火枪的部落要么获得了火枪,要么被已经装备火枪的部落征服。结果是到1833年,火枪技术已经传播到整个新西兰:所有幸存的毛利部落现在都有火枪了。
当社会确实从发明它的社会那里采用新技术时,这种扩散可能发生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它们包括和平贸易(如1954年晶体管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间谍活动(公元552年将蚕从东南亚走私到中东)、移民(1685年被驱逐出法国的20万胡格诺派教徒将法国玻璃和服装制造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以及战争。最后一种情况的一个关键案例是中国造纸技术向伊斯兰世界的转移,这是在公元751年中亚塔拉斯河战役中阿拉伯军队击败中国军队后实现的,他们在战俘中发现了一些造纸工匠,并将他们带到撒马尔罕建立造纸业。
在第12章中我们看到,文化传播既可以涉及详细的”蓝图”,也可以只是模糊的想法刺激细节的重新发明。虽然第12章以文字传播为例说明了这些替代方案,但它们也适用于技术的传播。前面的段落给出了蓝图复制的例子,而中国瓷器技术向欧洲的转移则提供了一个漫长的想法传播的实例。瓷器,一种细粒度的半透明陶器,大约在公元7世纪发明于中国。当它在14世纪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时(没有任何关于它是如何制造的信息),它受到了很大的赞赏,人们进行了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来模仿它。直到1707年,德国炼金术士约翰·伯特格尔在经过长期的工艺实验以及混合各种矿物和粘土的实验后,才找到了解决方案并建立了现在著名的迈森瓷器厂。后来在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或多或少独立的实验导致了塞弗尔、韦奇伍德和斯波德瓷器的诞生。因此,欧洲陶工不得不自己重新发明中国的制造方法,但他们受到了刺激去这样做,因为他们面前有理想产品的样品。
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社会在通过传播从其他社会接受技术的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近代历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人群是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距离澳大利亚100英里的一个岛上,没有远洋航海器,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最孤立的大陆。塔斯马尼亚人在10,000年间与其他社会没有接触,除了他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外,没有获得任何新技术。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被印度尼西亚岛链与亚洲大陆隔开,只从亚洲获得了涓涓细流般的发明。最容易通过传播接受发明的社会是那些嵌入主要大陆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为迅速,因为它们不仅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还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从印度和中国获得了发明,并继承了古希腊的学问。
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可能的重要性,通过一些难以理解的社会放弃强大技术的案例得到了惊人的说明。我们倾向于假设,有用的技术一旦获得,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存在,直到被更好的技术所取代。实际上,技术不仅必须被获得,还必须被维护,而这也取决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任何社会都会经历社会运动或时尚,在这些运动或时尚中,经济上无用的东西变得有价值,或者有用的东西暂时被贬值。如今,当地球上几乎所有社会都相互联系时,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时尚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一项重要的技术实际上会被抛弃。一个暂时反对强大技术的社会会继续看到邻近社会使用它,并有机会通过传播重新获得它(或者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邻居征服)。但这种时尚可以在孤立的社会中持续存在。
一个著名的例子涉及日本放弃枪支。火器于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两名葡萄牙冒险家携带火绳枪(原始枪支)抵达一艘中国货船。日本人对这种新武器印象深刻,开始进行本土枪支生产,大大改进了枪支技术,到公元1600年,日本拥有的枪支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质量也更好。
但也有一些因素阻碍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众多的武士阶层,即武士,对他们来说,剑被评为阶级象征和艺术品(以及征服下层阶级的手段)。日本的战争以前涉及武士剑客之间的单打独斗,他们站在开阔地上,发表仪式性的演讲,然后以优雅的战斗为荣。在农民士兵不优雅地用枪射击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变得致命。此外,枪支是外国发明,在1600年后在日本受到鄙视,就像其他外国事物一样。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限制枪支生产在几个城市,然后引入了生产枪支需要政府许可的要求,然后只为政府生产的枪支发放许可证,最后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订单,直到日本几乎再次没有功能性枪支。
同时代的欧洲统治者中也有一些人鄙视枪支并试图限制其供应。但这些措施在欧洲从未走得太远,因为任何暂时放弃火器的国家都会被持枪的邻国迅速征服。只有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岛屿,它才能摆脱对这种强大的新军事技术的拒绝。它在孤立中的安全在1853年结束,当时佩里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装备着大炮的访问说服日本需要恢复枪支制造。
这种拒绝以及中国放弃远洋船只(以及机械钟表和水力纺织机)是孤立或半孤立社会中技术倒退的著名历史实例。其他此类倒退发生在史前时代。极端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他们甚至放弃了骨制工具和捕鱼,成为现代世界中技术最简单的社会(第15章)。澳大利亚原住民可能采用然后又放弃了弓箭。托雷斯岛民放弃了独木舟,而高阿岛民则先放弃后又重新采用。陶器在整个波利尼西亚被放弃。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和许多美拉尼西亚人在战争中放弃使用弓箭。北极爱斯基摩人失去了弓箭和皮划艇,而多塞特爱斯基摩人失去了弓箭、弓钻和狗。
这些对我们来说起初如此奇特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地理和传播在技术史中的作用。没有传播,获得的技术更少,失去的现有技术更多。
因为技术孕育更多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原始发明本身的重要性。技术史例证了所谓的自催化过程(autocatalytic process):即一个随时间推移加速的过程,因为该过程催化自身。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发令我们今天印象深刻,但与青铜时代相比,中世纪的爆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青铜时代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展相形见绌。
技术倾向于自我催化的一个原因是进步依赖于对更简单问题的先前掌握。例如,石器时代的农民没有直接进行铁的提取和加工,这需要高温熔炉。相反,铁矿石冶金术源于人类数千年与天然纯金属露头的经验,这些金属足够软,可以在不加热的情况下锤打成形(铜和金)。它还源于数千年简单熔炉的发展来制作陶器,然后提取铜矿石和加工不需要像铁那样高温的铜合金(青铜)。在新月沃土和中国,铁制品只有在大约2000年的青铜冶金经验之后才变得常见。新世界社会刚刚开始制作青铜器,还没有开始制作铁器,这时欧洲人的到来截断了新世界的独立轨迹。
自催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使得通过重组产生更多新技术成为可能。例如,为什么印刷术在公元1455年古腾堡印刷圣经后在中世纪欧洲爆炸性传播,而不是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不知名的印刷工印刷费斯托斯圆盘之后?解释部分在于中世纪欧洲印刷工能够结合六项技术进步,其中大部分对费斯托斯圆盘的制造者来说是不可用的。在这些进步中——纸张、活字、冶金术、印刷机、油墨和文字——纸张和活字的想法从中国传到欧洲。古腾堡从金属模具中铸造字体的发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均匀这一潜在致命问题,依赖于许多冶金发展:用于字母冲头的钢、用于模具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被钢取代)、用于铸模的铅,以及用于字体的锡锌铅合金。古腾堡的印刷机源自用于制作葡萄酒和橄榄油的螺旋压榨机,而他的油墨是对现有油墨的油基改进。中世纪欧洲从三千年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活字印刷,因为只需要铸造几十个字母形式,而不是中文书写所需的数千个符号。
在所有六个方面,费斯托斯圆盘的制造者可以组合成印刷系统的技术都比古腾堡拥有的要弱得多。圆盘的书写介质是粘土,比纸张笨重和沉重得多。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岛的冶金技能、油墨和印刷机比公元1455年德国的更原始,所以圆盘必须手工冲压,而不是用锁定在金属框架中的铸造活字上墨和压印。圆盘的文字是音节文字,比古腾堡使用的罗马字母有更多符号,形式更复杂。因此,费斯托斯圆盘的印刷技术比古腾堡的印刷机笨拙得多,与手写相比优势更少。除了所有这些技术缺陷之外,费斯托斯圆盘印刷时,书写知识仅限于少数宫殿或寺庙抄写员。因此,对圆盘制造者精美产品的需求很少,投资制作所需的几十个手工冲头的激励也很少。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印刷的潜在大众市场促使众多投资者借钱给古腾堡。
人类技术从250万年前使用的第一批石器工具,发展到1996年的激光打印机,它取代了我已经过时的1992年激光打印机,并用于打印本书的手稿。开始时发展速度慢得难以察觉,数十万年过去了,我们的石器工具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用其他材料制成的人工制品的证据留存下来。今天,技术进步如此迅速,以至于每日报纸都有报道。
在这段不断加速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可以特别指出两次重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距今100,000到50,000年前,可能是由我们身体的基因变化使之成为可能:即进化出现代解剖结构,从而实现现代语言能力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次飞跃带来了骨制工具、单一用途的石器工具和复合工具。第二次飞跃源于我们采用定居生活方式,这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已定居,而有些地区甚至到今天还未定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定居生活方式的采用与我们开始从事粮食生产有关,粮食生产要求我们必须留在农作物、果园和储存的粮食盈余附近。
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只能使用可携带的技术。如果你经常迁移且缺乏交通工具或役畜,你的财产就只能局限于婴儿、武器以及其他绝对必需品中少量足够小到可以携带的物品。当你迁移营地时,你不可能背负陶器和印刷机。这种实际困难可能解释了某些技术为何如此早就出现,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例如,陶瓷最早经证实的前身是27,000年前在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制作的烧制陶土雕像,这远早于已知最古老的烧制陶器(来自日本,距今14,000年前)。同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一地区还出土了编织的最早证据,而编织技术的其他证据直到距今约13,000年前出现最古老的已知篮子和距今约9,000年前出现最古老的已知编织布料时才再次出现。尽管有这些非常早期的初步尝试,但陶器和编织技术都要等到人们定居下来,从而摆脱了运输陶罐和织机的问题后才得以发展。
除了促成定居生活从而使财产积累成为可能之外,粮食生产在技术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人类进化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发展出经济专业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供养的非粮食生产专家组成。但我们已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看到,粮食生产在不同大陆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此外,正如我们在本章所见,当地技术的起源和维持不仅依赖于当地发明,还依赖于来自其他地方的技术传播。这一因素往往导致技术在那些地理和生态障碍较少、便于大陆内部或与其他大陆之间传播的大陆上发展最为迅速。最后,一个大陆上的每个社会都代表着一次发明和采用技术的额外机会,因为各个社会在创新能力上因诸多不同原因而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在人口众多、拥有许多潜在发明者和众多相互竞争社会的大型生产区域发展最快。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三个因素的变化——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传播障碍以及人口规模——是如何直接导致观察到的技术发展的洲际差异的。欧亚大陆(实际上包括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板块,拥有数量最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最早开始粮食生产的两个中心所在的陆地板块: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和中国。它的东西向主轴使得欧亚大陆某一地区采用的许多发明能够相对快速地传播到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纬度和气候相似的社会。它沿次轴(南北向)的宽度与美洲在巴拿马地峡处的狭窄形成对比。它缺乏横贯美洲和非洲主轴的严重生态障碍。因此,欧亚大陆的地理和生态传播障碍不如其他大陆严重。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欧亚大陆是技术最早开始更新世后加速发展并导致技术最大程度局部积累的大陆。
北美洲和南美洲传统上被视为独立的大陆,但它们已经连接了数百万年,面临着相似的历史问题,可以一起与欧亚大陆进行比较。美洲构成世界第二大陆地板块,明显小于欧亚大陆。然而,它们在地理和生态上是分裂的:仅40英里宽的巴拿马地峡在地理上几乎横断了美洲,地峡的达连雨林(Darien)和墨西哥北部沙漠在生态上也是如此。后者将中美洲的先进人类社会与北美洲的先进社会分隔开来,而地峡则将中美洲的先进社会与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的先进社会分隔开来。此外,美洲的主轴是南北向的,这迫使大多数传播必须逆纬度(和气候)梯度进行,而不是在同一纬度内进行。例如,轮子是在中美洲发明的,羊驼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在安第斯山脉中部被驯化,但5,000年后,美洲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轮子仍然没有相遇,尽管中美洲玛雅社会与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1,200英里)远小于共享轮子和马匹的法国与中国之间6,000英里的距离。在我看来,这些因素解释了美洲在技术上落后于欧亚大陆的原因。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第三大陆块,比美洲小得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比美洲更容易从欧亚大陆到达,但撒哈拉沙漠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生态屏障,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欧亚大陆和北非分隔开来。非洲的南北轴线对技术传播构成了进一步的障碍,无论是在欧亚大陆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还是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内部。作为后一种障碍的例证,陶器和铁冶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赫勒地区(赤道以北)出现或到达的时间,至少与它们到达西欧的时间一样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1年左右才到达非洲南端,而冶金技术在通过欧洲船只从海上到达非洲南端之前,尚未通过陆路传播到那里。
最后,澳大利亚是最小的大陆。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极低的降雨量和生产力使其在支持人口方面实际上显得更小。它也是最孤立的大陆。此外,粮食生产从未在澳大利亚本土自发产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澳大利亚成为唯一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属制品的大陆。
表13.1通过比较各大陆的面积和现代人口,将这些因素转化为数字。各大陆在10,000年前(就在粮食生产兴起之前)的人口虽然未知,但肯定遵循相同的顺序,因为今天生产最多粮食的许多地区在10,000年前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也是高产地区。人口差异非常明显: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的人口几乎是美洲的6倍,几乎是非洲的8倍,是澳大利亚的230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发明家和更多相互竞争的社会。表13.1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枪炮和钢铁在欧亚大陆起源的原因。
表13.1 各大陆的人口
| 大陆 | 1990年人口 | 面积(平方英里) |
|---|---|---|
| 欧亚大陆和北非 | 4,120,000,000 | 24,200,000 |
| (欧亚大陆) | (4,000,000,000) | (21,500,000) |
| (北非) | (120,000,000) | (2,700,000) |
| 北美洲和南美洲 | 736,000,000 | 16,400,000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535,000,000 | 9,100,000 |
| 澳大利亚 | 18,000,000 | 3,000,000 |
大陆在面积、人口、传播便利性和粮食生产开始时间方面的差异对技术兴起产生的所有这些影响都被放大了,因为技术会催化自身。欧亚大陆最初的巨大优势因此转化为截至公元1492年的巨大领先——这是因为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特征,而不是因为人类智力的独特性。我认识的新几内亚人中包括潜在的爱迪生。但他们将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适合他们处境的技术问题:在新几内亚丛林中不依靠任何进口物品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
1979年,当我和传教士朋友一起飞越新几内亚一个偏远的沼泽盆地上空时,我注意到相距数英里的几间小屋。飞行员向我解释说,就在我们下方某个泥泞的地方,一群印度尼西亚鳄鱼猎人最近遇到了一群新几内亚游牧民。双方都惊慌失措,这次相遇以印度尼西亚人射杀了几名游牧民而告终。
我的传教士朋友猜测这些游牧民属于一个未接触过的群体,叫做法尤人(Fayu),外界只通过他们惊恐的邻居——一个已传教化的前游牧群体基里基里人(Kirikiri)的描述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外来者与新几内亚群体的首次接触总是有潜在危险,但这个开端特别不祥。尽管如此,我的朋友道格还是乘直升机飞进去,试图与法尤人建立友好关系。他活着回来了,但很震惊,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
事实证明,Fayu人通常以单个家庭的形式生活,分散在沼泽地中,每年聚集一两次来协商新娘的交换。Doug的访问恰逢这样一次聚会,有几十个Fayu人参加。对我们来说,几十个人只是一次小型的、普通的聚会,但对Fayu人来说,这是一次罕见的、令人恐惧的事件。杀人犯突然发现自己与受害者的亲属面对面。例如,一个Fayu男子发现了杀害他父亲的人。儿子举起斧头冲向凶手,但被朋友们摔倒在地;然后凶手拿着斧头冲向倒在地上的儿子,也被摔倒了。两个人都被按住,愤怒地尖叫着,直到他们看起来足够疲惫才被释放。其他男人不时地互相辱骂,因愤怒和沮丧而颤抖,用斧头砸地。这种紧张气氛在聚会的几天里持续存在,Doug祈祷这次访问不会以暴力结束。
Fayu人由大约400名狩猎采集者组成,分为四个氏族,在几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游荡。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以前大约有2000人,但由于Fayu人杀害Fayu人,他们的人口大大减少了。他们缺乏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来和平解决严重的争端。最终,由于Doug的访问,一群Fayu人邀请了一对勇敢的传教士夫妇与他们一起生活。这对夫妇现在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年,逐渐说服Fayu人放弃暴力。Fayu人因此被带入了现代世界,在那里他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许多其他以前未接触过的新几内亚人和亚马逊印第安人群体同样归功于传教士,将他们融入现代社会。在传教士之后是教师和医生、官僚和士兵。因此,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政府和宗教的传播一直相互联系,无论这种传播是和平的(如最终的Fayu人)还是通过武力。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是政府组织征服,宗教为其辩护。虽然游牧民和部落民偶尔会击败有组织的政府和宗教,但在过去的13000年里,趋势是游牧民和部落民失败。
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与今天的Fayu人类似的社会中,没有人生活在更复杂的社会中。直到公元1500年,世界上不到20%的陆地被边界划分为由官僚管理、由法律管辖的国家。今天,除南极洲外的所有陆地都如此划分。那些最早实现集中政府和有组织宗教的社会的后裔最终主宰了现代世界。因此,政府和宗教的结合,与病菌、文字和技术一起,作为导致历史最广泛模式的四组主要近因代理之一发挥了作用。政府和宗教是如何产生的?
Fayu部落和现代国家代表了人类社会光谱的两个极端。现代美国社会和Fayu人在专业警察部队、城市、金钱、贫富差距以及许多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存在或缺失方面存在差异。所有这些制度是一起产生的,还是有些在其他之前产生?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组织水平的现代社会、检查关于过去社会的书面记录或考古证据,以及观察社会制度如何随时间变化来推断这个问题的答案。
试图描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将它们分为多达六个类别。任何这种定义进化或发展连续体阶段的尝试——无论是音乐风格、人类生命阶段还是人类社会——都注定在两方面不完美。首先,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从前一个阶段发展而来的,划分界限不可避免地是任意的。(例如,一个19岁的人是青少年还是年轻成人?)其次,发展序列不是不变的,因此被归类在同一阶段下的例子不可避免地是异质的。(勃拉姆斯和李斯特在坟墓里会翻身,如果知道他们现在被归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然而,任意划定的阶段为讨论音乐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提供了有用的简写,前提是要记住上述警告。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使用一个简单的分类,仅基于四个类别——部落(band)、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见表14.1)——来理解社会。
部落(Band)是最小的社会单位,通常由5到80人组成,大多数或全部成员通过血缘或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扩展家庭或几个相关的扩展家庭。如今,仍然独立生存的部落几乎仅限于新几内亚和亚马逊地区最偏远的地方,但在现代历史中还有许多其他部落,它们只是最近才被国家控制、同化或消灭。这些部落包括许多或大多数非洲俾格米人、南非桑人狩猎采集者(所谓的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以及美洲一些资源贫瘠地区的印第安人,如火地岛和北方针叶林地区。所有这些现代部落都是或曾经是游牧的狩猎采集者,而不是定居的食物生产者。可能所有人类至少在40,000年前都生活在部落中,而最近在11,000年前时大多数人仍然如此。
表14.1 社会类型
| 部落(Band) | 部族(Tribe) | 酋邦(Chiefdom) | 国家(State) | |
|---|---|---|---|---|
| 成员构成 | ||||
| 人数 | 数十人 | 数百人 | 数千人 | 超过50,000人 |
| 定居模式 | 游牧 | 固定:1个村庄 | 固定:1个或多个村庄 | 固定:多个村庄和城市 |
| 关系基础 | 亲属关系 | 基于亲属的氏族 | 阶级和居住地 | 阶级和居住地 |
| 族群和语言 | 1种 | 1种 | 1种 | 1种或多种 |
| 治理 | ||||
| 决策与领导 | “平等主义” | “平等主义”或大人物制 | 集中化、世袭 | 集中化 |
| 官僚机构 | 无 | 无 | 无,或1-2级 | 多级 |
| 武力和信息垄断 | 无 | 无 | 有 | 有 |
| 冲突解决 | 非正式 | 非正式 | 集中化 | 法律、法官 |
| 定居点等级 | 无 | 无 | 无→首要村庄 | 首都 |
部落缺少许多我们在自己社会中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他们没有永久的单一居住基地。部落的土地由整个群体共同使用,而不是在子群体或个人之间分割。除了按年龄和性别划分外,没有常规的经济专业化:所有身体健全的个体都寻找食物。没有正式的制度,如法律、警察和条约,来解决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冲突。部落组织通常被描述为”平等主义”:没有正式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分层,没有正式的或世袭的领导权,也没有信息和决策的正式垄断。然而,“平等主义”一词不应被理解为所有部落成员在声望上是平等的,或对决策的贡献是平等的。相反,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任何部落的”领导权”都是非正式的,是通过个性、力量、智慧和战斗技能等品质获得的。
| 部落(Band) | 部族(Tribe) | 酋邦(Chiefdom) | 国家(State) | |
|---|---|---|---|---|
| 宗教 | ||||
| 为盗贼统治辩护? | 否 | 否 | 是 | 是→否 |
| 经济 | ||||
| 食物生产 | 否 | 否→是 | 是→集约化 | 集约化 |
| 劳动分工 | 否 | 否 | 否→是 | 是 |
| 交换方式 | 互惠 | 互惠 | 再分配(“贡品”) | 再分配(“税收”) |
| 土地控制 | 部落 | 氏族 | 首领 | 各种形式 |
社会
| 分层化 | 否 | 否 | 是,按亲属关系 |
| 奴隶制 | 否 | 否 | 小规模 |
| 精英奢侈品 | 否 | 否 | 是 |
| 公共建筑 | 否 | 否 | 否 是 是 |
| 本土文字 | 否 | 否 | 否 |
横向箭头表示该属性在该类型的较简单和较复杂社会之间存在差异。
我对群落(band)的亲身经历来自新几内亚的低地沼泽地区,法尤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区域被称为湖泊平原。在那里,我仍然能遇到由几个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以及老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们住在溪流旁简陋的临时棚屋里,乘独木舟和步行出行。为什么湖泊平原的人们继续过着游牧群落的生活,而新几内亚的大多数其他民族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其他民族现在都生活在定居的更大群体中?解释是该地区缺乏密集的本地资源集中,无法让许多人生活在一起,而且(直到传教士带来农作物之前)该地区也缺乏能够实现高产农业的本土植物。群落的主食是西米棕榈树,当棕榈树成熟时,其树芯会产生含淀粉的髓。群落是游牧性的,因为当他们砍伐完一个地区的成熟西米树后,他们必须搬迁。群落人数因疾病(尤其是疟疾)、沼泽中缺乏原材料(甚至制作工具的石头都必须通过贸易获得)以及沼泽为人类提供的食物有限而保持在低水平。类似的资源限制(以现有人类技术可获取的)也存在于世界上最近被其他群落占据的地区。
我们最亲近的动物亲戚,非洲的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生活在群落中。所有人类大概也是如此,直到改进的食物获取技术使一些狩猎采集者能够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定居下来。群落是我们从数百万年进化历史中继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我们超越它的所有发展都发生在最近几万年内。
超越群落的第一个阶段被称为部落(tribe),其不同之处在于规模更大(通常有数百人而不是几十人),并且通常有固定的定居点。然而,一些部落甚至酋邦由季节性迁徙的牧民组成。
部落组织的例证是新几内亚高地人,在殖民政府到来之前,他们的政治单位是一个村庄或一个紧密联系的村庄群。因此,这种”部落”的政治定义通常比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定义的部落要小得多——即共享语言和文化的群体。例如,1964年我开始在一群被称为福雷人的高地人中工作。按照语言和文化标准,当时有12,000名福雷人,说着两种互通的方言,生活在65个村庄中,每个村庄有数百人。但福雷语言群体的村庄之间完全没有政治统一。每个村落都与所有邻近村落处于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战争和变动联盟模式中,无论邻居是福雷人还是说不同语言的人。
最近独立、现在以各种方式从属于民族国家的部落,仍然占据着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和亚马逊地区的大部分地区。过去类似的部落组织是从考古证据中推断出来的,这些证据显示定居点规模可观,但缺乏我将在下文解释的酋邦的考古标志。这些证据表明,部落组织大约在13,000年前开始在肥沃月湾出现,后来在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定居生活的先决条件是食物生产,或者是资源特别集中的高产环境,可以在小范围内狩猎和采集。这就是为什么定居点以及推断的部落在那时开始在肥沃月湾激增,当时气候变化和技术改进相结合,使得野生谷物的丰收成为可能。
部落除了通过定居居住和更大的人口数量与群落不同之外,还在于它由不止一个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组成,称为氏族(clan),这些氏族之间交换婚姻伴侣。土地属于特定的氏族,而不属于整个部落。然而,部落中的人数仍然很少,每个人都知道其他所有人的名字和关系。
对于其他类型的人类群体来说,“几百人”似乎也是群体规模的上限,在这个规模内每个人都能认识其他所有人。例如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中,如果学校有几百名学生,校长可能会知道所有学生的名字,但如果有几千名学生就不可能了。在成员超过几百人的社会中,人类政府组织倾向于从部落形式转变为酋邦(chiefdom)形式,原因之一是在更大的群体中,陌生人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部落中进一步化解潜在冲突解决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每个人都通过血缘或婚姻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与其他人有联系。这些将所有部落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亲属关系纽带使得警察、法律和其他更大社会的冲突解决机构变得不必要,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民都会有许多共同的亲属,这些亲属会对他们施加压力,防止争执演变成暴力。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在离开各自村庄时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新几内亚人,两人会就他们的亲属关系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试图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两人不应该试图杀死对方。
尽管部落与群体之间存在所有这些差异,但仍有许多相似之处。部落仍然有一种非正式的”平等主义”政府制度。信息和决策都是共享的。在新几内亚高地,我曾观察过村庄会议,村里的所有成年人都在场,坐在地上,个人发表演讲,没有任何人”主持”讨论的迹象。许多高地村庄确实有一个被称为”大人物”(big-man)的人,即村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但这个职位不是一个需要填补的正式职位,而且权力有限。大人物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不掌握外交秘密,只能试图影响共同决策。大人物凭借自己的特质获得这一地位;这个职位不是继承的。
部落也与群体共享”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没有等级制的世系或阶级。地位不仅不能继承;传统部落或群体的任何成员都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不成比例地富有,因为每个人都对许多其他人负有债务和义务。因此,外人不可能从外表上猜出村里所有成年男子中谁是大人物:他住在同样类型的小屋里,穿着同样的衣服或饰品,或者像其他人一样一丝不挂。
与群体一样,部落缺乏官僚机构、警察力量和税收。他们的经济基于个人或家庭之间的互惠交换,而不是基于向某个中央权威缴纳的贡品再分配。经济专业化程度很低:缺乏全职工艺专家,每个身体健全的成年人(包括大人物)都参与种植、采集或狩猎食物。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所罗门群岛路过一个花园,看到一个男人在远处挖地并向我挥手,我惊讶地意识到那是我的一个朋友,名叫法勒陶。他是所罗门群岛最著名的木雕家,一位极具原创性的艺术家——但这并没有使他摆脱自己种植红薯的必要性。由于部落因此缺乏经济专家,他们也没有奴隶,因为没有专门的卑微工作让奴隶去做。
正如古典时期的音乐作曲家从C.P.E.巴赫到舒伯特,从而涵盖了从巴洛克作曲家到浪漫主义作曲家的整个光谱,部落也在一个极端向群体过渡,在另一个极端向酋邦过渡。特别是,部落大人物在为宴会屠宰的猪肉分配中的作用,预示了酋长在酋邦中收集和重新分配食物和物品——现在被重新解释为贡品——的作用。同样,公共建筑的存在与否本应是部落与酋邦之间的区别之一,但大型新几内亚村庄经常有祭祀屋(在塞皮克河被称为haus tamburan),预示着酋邦的寺庙。
虽然今天仍有少数群体和部落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偏远和生态边缘地带生存,但完全独立的酋邦在20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着被国家觊觎的优质土地。然而,截至公元1492年,酋邦仍然广泛分布在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尚未被本土国家吞并的富饶地区,以及整个波利尼西亚。下面讨论的考古证据表明,酋邦大约在公元前5500年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出现。让我们考虑一下酋邦的显著特征,它与现代欧美国家截然不同,同时也与群体和简单的部落社会不同。
就人口规模而言,酋邦比部落大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种规模造成了严重的内部冲突潜力,因为对于生活在酋邦中的任何人来说,酋邦中绝大多数其他人既不是通过血缘或婚姻关系密切相关的,也不是知道名字的。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邦的兴起,人们不得不在历史上第一次学会如何在经常遇到陌生人时不试图杀死他们。
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是由一个人,即酋长,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与部落的大人物相比,酋长拥有一个公认的职位,通过世袭权利继承。酋长不是村庄会议的分散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永久的中央集权机构,做出所有重大决策,并垄断关键信息(例如邻近酋长私下威胁什么,或者神灵据称承诺了什么收成)。与大人物不同,酋长可以通过可见的显著特征从远处识别出来,例如西南太平洋伦内尔岛上背在背后的大扇子。平民遇到酋长时有义务表现出仪式性的尊重标志,例如(在夏威夷)俯卧在地。酋长的命令可能通过一两级官僚传达,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僚相比,酋邦官僚具有普遍化而非专业化的角色。在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同样的官僚(称为 konohiki)为酋长征收贡品、监督灌溉和组织劳役,而国家社会则有独立的税收征收员、水利区管理者和征兵委员会。
酋邦在小面积上的大量人口需要充足的食物,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粮食生产获得,在少数特别富饶的地区通过狩猎采集获得。例如,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印第安人,如夸扎尔人、努特卡人和特林吉特人,在没有任何农业或家畜的情况下在酋长领导下生活在村庄中,因为河流和海洋盛产鲑鱼和比目鱼。一些被降为平民等级的人产生的食物盈余用于养活酋长、他们的家人、官僚和工艺专家,这些人制作独木舟、石斧或痰盂,或担任捕鸟者或纹身师。
奢侈品,由这些专业工艺品或通过长途贸易获得的稀有物品组成,专为酋长保留。例如,夏威夷酋长有羽毛斗篷,其中一些由数万根羽毛组成,需要许多代人才能制造(当然是由平民斗篷制造者制造)。这种奢侈品的集中往往使我们能够从考古学上识别酋邦,因为一些墓葬(酋长的墓葬)比其他墓葬(平民的墓葬)包含更丰富的物品,这与早期人类历史的平等埋葬形成对比。一些古代复杂的酋邦也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建筑(如寺庙)遗迹和区域性的定居点等级体系与部落村庄区分开来,其中一个地点(最高酋长的地点)明显更大,拥有比其他地点更多的行政建筑和文物。
与部落一样,酋邦由居住在一个地点的多个世袭血统组成。然而,部落村庄的血统是平等等级的氏族,而在酋邦中,酋长血统的所有成员都拥有世袭特权。实际上,社会被划分为世袭的酋长和平民阶级,夏威夷酋长本身又细分为八个等级制度的血统,每个血统都将婚姻集中在自己的血统内。此外,由于酋长需要卑微的仆人以及专业工匠,酋邦与部落的不同之处在于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担任的工作,通常通过突袭俘获获得。
酋邦最显著的经济特征是它们从仅依赖带群和部落特有的互惠交换转变,即 A 给 B 一个礼物,同时期望 B 在某个未指定的未来时间给 A 一个可比价值的礼物。我们现代国家居民在生日和节日时沉迷于这种行为,但我们大部分商品流动是通过根据供求规律用货币买卖来实现的。在继续互惠交换并且没有市场或货币的情况下,酋邦发展了一种额外的新系统,称为再分配经济(redistributive economy)。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时节从酋邦的每个农民那里收到小麦,然后为所有人举办盛宴并提供面包,或者储存小麦并在收获之间的几个月内逐渐再次分发。当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大部分物品不是重新分配给他们,而是由酋长血统和工匠保留和消费时,重新分配就变成了贡品(tribute),这是税收的前身,首次出现在酋邦中。酋长不仅要求平民提供物品,还要求他们为公共工程建设提供劳动,这可能会回馈平民(例如,帮助养活所有人的灌溉系统),或者主要使酋长受益(例如,奢华的陵墓)。
我们一直在泛泛地谈论酋邦,好像它们都一样。事实上,酋邦之间差异很大。规模较大的酋邦往往拥有更强大的酋长,更多等级的酋长世系,酋长和平民之间的区别更大,酋长保留的贡品更多,官僚层级更多,公共建筑也更宏伟。例如,波利尼西亚小岛上的社会实际上与拥有大人物的部落社会相当相似,只是酋长的地位是世袭的。酋长的小屋看起来和其他小屋一样,没有官僚或公共工程,酋长将收到的大部分物品重新分配给平民,土地由社区控制。但在最大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如夏威夷、塔希提和汤加,酋长通过他们的装饰品一眼就能认出,大量劳动力修建公共工程,大部分贡品由酋长保留,所有土地都由他们控制。拥有等级世系(ranked lineages)的社会之间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等级划分,从政治单位是单个自治村庄的社会,到由区域性村庄集合组成的社会,其中最大的村庄和最高酋长控制着较小的村庄和次级酋长。
到现在,酋邦引入了所有中央集权、非平等主义社会的根本困境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往好了说,它们通过提供无法以个人为基础签约的昂贵服务来做好事。往坏了说,它们毫不掩饰地作为盗窃统治(kleptocracies)运作,将净财富从平民转移到上层阶级。这些高尚和自私的功能密不可分,尽管一些政府强调其中一种功能远多于另一种。盗窃统治者与明智的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强盗大亨与公共恩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问题: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贡品中,精英阶层保留的百分比有多大,以及平民对重新分配的贡品的公共用途有多喜欢。我们认为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是盗窃统治者,因为他保留了太多贡品(相当于数十亿美元),重新分配的贡品太少(扎伊尔没有正常运作的电话系统)。我们认为乔治·华盛顿是政治家,因为他将税款用于广受赞誉的项目,并且在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使自己致富。然而,乔治·华盛顿出生富裕,美国的财富分配比新几内亚村庄的不平等得多。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邦还是国家,人们都必须问:为什么平民容忍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转移到盗窃统治者手中?这个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家提出的问题,在每次现代选举中都被选民重新提出。公众支持很少的盗窃统治有被推翻的风险,要么被受压迫的平民推翻,要么被寻求公众支持的新兴替代盗窃统治者推翻,他们承诺提供更高的服务与掠夺成果比率。例如,夏威夷历史反复被反抗压迫性酋长的起义打断,通常由承诺减少压迫的年轻兄弟领导。这在古老的夏威夷背景下对我们来说可能听起来很有趣,直到我们反思现代世界中这种斗争仍然造成的所有苦难。
精英阶层应该做什么来获得民众支持,同时仍然保持比平民更舒适的生活方式?历代盗窃统治者采用了四种解决方案的混合:
解除民众武装,武装精英。在这些高科技武器时代,这要容易得多,这些武器只在工业工厂生产,容易被精英垄断,而不像古代时代的长矛和棍棒可以在家里轻松制作。
通过以受欢迎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到的大部分贡品来使民众高兴。这个原则对夏威夷酋长和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利用武力垄断通过维持公共秩序和遏制暴力来促进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社会相对于非中央集权社会的一个巨大且未被充分认识的优势。人类学家以前将部落和氏族社会理想化为温和和非暴力的,因为访问的人类学家在三年研究中没有在25人的群体中观察到谋杀。当然他们没有:很容易计算出,一个由十几个成年人和十几个孩子组成的群体,受到因通常原因而非谋杀而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如果另外每三年有一个成年人谋杀另一个成年人,就无法延续下去。关于部落和氏族社会的更广泛的长期信息表明,谋杀是主要死因。例如,我恰好在一位女人类学家采访Iyau妇女关于她们生活史的时候访问了新几内亚的Iyau人。当被要求说出她的丈夫时,一个又一个女人说出了几个相继死于暴力的丈夫。一个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任丈夫被Elopi袭击者杀死。我的第二任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男人杀死,他成了我的第三任丈夫。那个丈夫被我第二任丈夫的兄弟杀死,为他的谋杀报仇。”这样的传记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族来说很常见,并促成了随着部落社会规模扩大而接受中央集权。
窃权者获得公众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是构建一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来为窃权统治辩护。部落和族群早已有超自然信仰,就像现代的成熟宗教一样。但部落和族群的超自然信仰并不是用来为中央权威辩护、为财富转移辩护,或维持无亲缘关系个体之间的和平。当超自然信仰获得了这些功能并制度化后,它们就转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夏威夷酋长和其他地方的酋长一样,宣称自己具有神性、拥有神圣血统,或者至少与神灵有直接联系。酋长声称通过为人民向神灵求情、诵读获得降雨、丰收和捕鱼成功所需的仪式咒语来服务人民。
酋邦通常拥有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制度化宗教的前身,用来支持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将政治领袖和祭司的职能集于一身,或者支持一个独立的窃权者群体(即祭司),其职能是为酋长提供意识形态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邦将如此多的贡品用于建造神庙和其他公共工程,这些建筑作为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可见标志。
除了为向窃权者转移财富辩护外,制度化宗教还为集中化社会带来了两个其他重要好处。首先,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帮助解决了无亲缘关系的个体如何共同生活而不互相残杀的问题——通过为他们提供一种不基于亲缘关系的纽带。其次,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动机,而不仅仅是基因上的自我利益,去为他人牺牲生命。以少数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为代价,整个社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抗攻击方面变得更加有效。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国家的制度,现在国家统治着世界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陆地。许多早期国家和所有现代国家都有识字的精英阶层,许多现代国家也有识字的大众。消失的国家往往留下可见的考古特征,如标准化设计的神庙遗址、至少四个等级的定居点规模,以及覆盖数万平方英里的陶器风格。因此我们知道,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7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现在中美洲,2000多年前出现在安第斯、中国和东南亚,1000多年前出现在西非。在现代,人们反复观察到从酋邦形成国家的过程。因此,我们掌握的关于过去国家及其形成的信息,远比关于过去酋邦、部落和族群的信息多得多。
原始国家扩展了大型最高酋邦(多村庄酋邦)的许多特征。它们延续了从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邦的规模增长。酋邦的人口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而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人口超过一百万,中国的人口超过十亿。最高酋长的所在地可能成为国家的首都。国家在首都之外的其他人口中心也可能符合真正城市的标准,而这在酋邦中是缺乏的。城市与村庄的区别在于其宏伟的公共工程、统治者的宫殿、来自贡品或税收的资本积累,以及非食物生产者的集中。
早期国家有一个世袭领袖,头衔相当于国王,就像一个超级最高酋长,对信息、决策和权力行使着更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中,关键知识也只有少数人掌握,他们控制着向政府其他部门的信息流动,从而控制决策。例如,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决定是否让五亿人陷入核战争的信息和讨论,最初由肯尼迪总统限制在他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人执行委员会内;然后他将最终决策限制在一个四人小组中,由他本人和三位内阁部长组成。
中央控制在国家中比在酋邦中更加深远,以贡品(更名为税收)形式进行的经济再分配也更加广泛。经济专业化更加极端,以至于今天甚至农民也不再自给自足。因此,当国家政府崩溃时,对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就像公元407年至411年间罗马军队、行政官员和货币从不列颠撤离时所发生的那样。即使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也对其经济进行了集中控制。它们的食物由四个专业群体生产(谷物农民、牧民、渔民和果园及菜园种植者),国家从每个群体那里获取产品,并向每个群体分发必要的供应品、工具和该群体不生产的其他类型食物。国家向谷物农民提供种子和耕畜,从牧民那里获取羊毛,通过长途贸易用羊毛交换金属和其他必需原材料,并向维护农民所依赖的灌溉系统的劳工支付口粮。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在比酋邦大得多的规模上采用了奴隶制。这不是因为酋邦对战败的敌人更加仁慈,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业化程度更高,有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为奴隶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用途。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使得更多的俘虏可供使用。
酋邦的一两个管理层级在国家中被极大地增加,任何看过政府组织结构图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除了官僚的纵向层级增加,还有横向专业化。国家政府不再像夏威夷地区的konohiki那样负责管理的所有方面,而是有几个独立的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层级,分别处理水资源管理、税收、征兵等。即使是小型国家也比大型酋邦有更复杂的官僚机构。例如,西非的马拉迪国家有一个拥有130多个授衔职位的中央政府。
国家内部的冲突解决已通过法律、司法机构和警察变得越来越正式化。法律通常是书面的,因为许多国家(有明显的例外,如印加国家)都有识字的精英,文字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最早的国家形成的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相比之下,没有一个未处于国家化边缘的早期酋邦发展出文字。
早期国家有国家宗教和标准化的神庙。许多早期国王被认为是神圣的,并在无数方面受到特殊待遇。例如,阿兹特克和印加皇帝都被抬在轿子里;仆人走在印加皇帝的轿子前面清扫地面;日语包括专门用于称呼天皇的代词”你”的特殊形式。早期国王本身就是国家宗教的首领,或者有独立的大祭司。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经济再分配、书写和手工艺技术的中心。
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推向了极致。然而,除此之外,国家在几个新方向上与酋邦产生了分歧。最根本的区别是,国家是按照政治和领土界线组织的,而不是按照定义了游群、部落和简单酋邦的亲属关系界线。此外,游群和部落总是,酋邦通常是由单一的民族和语言群体组成的。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国家的合并或征服形成的所谓帝国——通常是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官僚不像酋邦那样主要根据亲属关系选拔,而是至少部分根据培训和能力选拔的专业人员。在后来的国家,包括今天的大多数国家,领导层往往变成非世袭的,许多国家放弃了从酋邦继承下来的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体系。
在过去的13000年里,人类社会的主要趋势是用更大、更复杂的单位取代更小、更简单的单位。显然,这只是一个平均的长期趋势,在任一方向都有无数的变化:1000次合并对应999次逆转。我们从日常报纸上知道,大型单位(例如,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就像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那样。更复杂的单位并不总是征服不太复杂的单位,而可能会屈服于它们,就像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分别被”野蛮人”和蒙古酋邦推翻一样。但长期趋势仍然是朝向大型、复杂的社会,最终达到国家的顶峰。
显然,当国家与更简单的实体发生碰撞时,国家获胜的部分原因是国家通常在武器和其他技术方面享有优势,并且在人口数量上有很大优势。但酋邦和国家固有的还有另外两个潜在优势。首先,集中的决策者在集中军队和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爱国热情使他们的军队愿意进行自杀式战斗。
后一种意愿被我们现代国家的公民通过学校、教会和政府如此强烈地灌输,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标志着与以前人类历史的根本决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口号,敦促其公民在必要时准备为国家而死:英国的”为了国王和国家”,西班牙的”为了上帝和西班牙”,等等。类似的情感激励着16世纪的阿兹特克战士:“没有什么比战争中的死亡更好,没有什么比这种对赐予生命的祂(阿兹特克民族神威齐洛波奇特利)如此珍贵的花样死亡更好:我在远处看到它,我的心渴望它!”
这种情绪在部落和氏族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的新几内亚朋友向我讲述的所有关于他们过去部落战争的故事中,没有一个暗示过部落爱国主义、自杀式冲锋或任何其他承认有被杀风险的军事行为。相反,袭击是通过伏击或优势兵力发起的,目的是尽一切代价降低可能为自己村庄而死的风险。但与国家社会相比,这种态度严重限制了部落的军事选择。自然,爱国和宗教狂热分子之所以成为如此危险的对手,不是因为狂热分子自己的死亡,而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一部分成员的死亡,以便消灭或粉碎他们的异教敌人。战争中的狂热主义,即推动有记载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征服的那种类型,在酋邦(chiefdoms)特别是国家在过去6000年内出现之前,可能在地球上是未知的。
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如何演变成大型的中央集权社会,其中大多数成员彼此并无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回顾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推动社会进行这种转变。
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国家都是独立产生的——或者如文化人类学家所说,“原生地”(pristinely)产生的,即在没有任何先前存在的周围国家的情况下。除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外,每个大陆上至少发生过一次,可能多次原生国家起源。史前国家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和西非的国家。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与欧洲国家接触的本土国家在马达加斯加、夏威夷、塔希提和非洲许多地区从酋邦反复出现。酋邦更是经常原生地出现,在所有这些地区以及北美洲东南部和太平洋西北部、亚马逊、波利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有。所有这些复杂社会的起源为我们理解它们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库。
在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众多理论中,最简单的一个否认存在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解释。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所熟悉的所有社会——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们现在知道,截至公元1492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由酋邦、部落或氏族组织的。国家形成确实需要解释。
下一个理论是最熟悉的理论。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测,国家是由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形成的,这是一个理性决定,当人们计算自己的利益时达成的,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国家中会比在更简单的社会中过得更好,并自愿废除了他们更简单的社会。但观察和历史记录未能发现一个国家在这种冷静远见的空灵氛围中形成的案例。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放弃主权并合并成较大的单位。他们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压力下才会这样做。
第三个理论,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仍然流行,从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出发:在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和墨西哥,大约在国家开始出现的时候,大规模灌溉系统开始建设。该理论还指出,任何大型、复杂的灌溉或水利管理系统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bureaucracy)来建造和维护它。然后,该理论将观察到的时间上的粗略相关性转变为假设的因果链。据说,美索不达米亚人、华北人和墨西哥人预见到了大规模灌溉系统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尽管当时在数千英里范围内(或地球上任何地方)没有这样的系统来为他们说明这些好处。那些有远见的人选择将他们低效的小酋邦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国家,能够为他们带来大规模灌溉的福祉。
然而,这种国家形成的”水力理论”(hydraulic theory)受到与一般社会契约理论相同的反对。更具体地说,它只涉及复杂社会演变的最后阶段。它对在大规模灌溉前景出现在地平线上之前的数千年间,从部落到氏族再到酋邦的进程是什么驱动的只字未提。当详细检查历史或考古日期时,它们无法支持灌溉作为国家形成驱动力的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华北、墨西哥和马达加斯加,小规模灌溉系统在国家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设并没有伴随国家的出现,而是在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都明显晚得多才出现。在中美洲玛雅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形成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当地社区可以自行建造和维护的小规模系统。因此,即使在那些确实出现了复杂水利管理系统的地区,它们也是国家的次要后果,而这些国家肯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形成的。
在我看来,能够指向一个根本正确的国家形成观点的,是一个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更具广泛有效性的不争事实——即,区域人口规模是社会复杂性最强的单一预测因素。正如我们所见,部落(bands)由几十个人组成,氏族(tribes)由几百人组成,酋邦(chiefdoms)由几千到几万人组成,而国家通常超过约5万人。除了区域人口规模与社会类型(部落、氏族等)之间的这种粗略关联外,在每个类别内部,人口与社会复杂性之间还存在更细致的趋势:例如,拥有大量人口的酋邦被证明是最集中、最分层、最复杂的。
这些关联强烈表明,区域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某种关系。但这些关联并没有准确告诉我们,在导致复杂社会这一结果的因果链中,人口变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为了追溯这条链,让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大规模密集人口本身是如何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检验为什么一个庞大但简单的社会无法维持自身。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最终将回到这个问题:随着区域人口的增加,一个更简单的社会实际上是如何变得更复杂的。
我们已经看到,大规模或密集的人口只在粮食生产的条件下才会出现,或者至少在狩猎采集异常富饶的条件下才会出现。一些富饶的狩猎采集社会达到了酋邦的组织水平,但没有一个达到国家的水平:所有国家都通过粮食生产来养活其公民。这些考虑因素,连同刚才提到的区域人口规模与社会复杂性之间的关联,引发了一场关于粮食生产、人口变量和社会复杂性之间因果关系的长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是集约化粮食生产是原因,触发了人口增长并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复杂社会?还是大量人口和复杂社会反而是原因,以某种方式导致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
以那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提出问题是错误的。集约化粮食生产和社会复杂性通过自催化(autocatalysis)相互刺激。也就是说,人口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导致社会复杂性,而社会复杂性反过来导致粮食生产集约化,从而导致人口增长。复杂的中央集权社会具有独特的能力来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长距离贸易(包括进口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业工具),以及不同经济专业群体的活动(例如用农民的谷物喂养牧民,并将牧民的牲畜转移给农民用作耕畜)。纵观历史,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能力都促进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从而促进了人口增长。
此外,粮食生产至少通过三种方式促进了复杂社会的具体特征。首先,它涉及季节性的脉冲式劳动投入。当收获被储存起来后,农民的劳动力就可以被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所利用——用于建造展示国家权力的公共工程(如埃及金字塔),或建造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进行征服战争以形成更大的政治实体。
其次,粮食生产可以被组织起来以产生储存的粮食盈余,这允许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层。这些盈余可以用来养活复杂社会的所有阶层:酋长、官僚和其他精英成员;抄写员、工匠和其他非粮食生产专家;以及农民自己,在他们被征召建造公共工程期间。
最后,粮食生产允许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生活,这是积累大量财产、发展精细技术和手工艺以及建造公共工程的先决条件。固定居住对复杂社会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传教士和政府,每当他们与新几内亚或亚马逊以前未接触的游牧部落或部落首次接触时,总是有两个直接目标。当然,一个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安抚”游牧民:也就是说,劝阻他们不要杀害传教士、官僚或彼此。另一个目标是诱使游牧民在村庄定居,这样传教士和官僚就能找到游牧民,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和学校等服务,并对他们进行传教和控制。
因此,粮食生产增加了人口规模,也在许多方面使复杂社会的特征成为可能。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大量人口使复杂社会成为必然。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经验观察:部落或氏族组织对于数十万人的社会根本不起作用,而所有现存的大型社会都具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四个明显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不相关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数增加,这个问题会呈天文数字般增长。一个20人部落内的关系只涉及190个双人互动(20人乘以19再除以2),但一个2000人的部落将有1,999,000个二元关系(dyads)。每一个二元关系都代表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可能在激烈争吵中爆发。在部落和氏族社会中,每次谋杀通常都会引发报复性杀戮的尝试,从而开启一个又一个无休止的谋杀与反谋杀循环,使社会动荡不安。
在一个部落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与争吵双方同时有关系的人会介入调解纠纷。在一个氏族中,许多人仍然是近亲,而且每个人至少都知道其他人的名字,共同的亲戚和朋友会调解争吵。但一旦跨越了”几百人”这个门槛——在这个门槛以下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其他所有人——越来越多的二元关系变成了不相关的陌生人配对。当陌生人打架时,在场的人很少有人会同时是双方战斗者的朋友或亲戚,并有自身利益去阻止打架。相反,许多旁观者只是其中一方战斗者的朋友或亲戚,会支持那个人,将两人的打架升级为全面的混战。因此,一个继续把冲突解决留给所有成员的大型社会注定会崩溃。仅这一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千人的社会只有在发展出集中权威来垄断武力和解决冲突时才能存在。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公共决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新几内亚村庄中,如果村庄足够小,新闻和信息能迅速传播到每个人,每个人都能在全村会议上听到其他所有人的声音,每个想在会议上发言的人都有机会这样做,那么由全体成年人口进行决策仍然是可能的。但在更大的社区中,所有这些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都变得无法实现。即使在现在,在这个有麦克风和扩音器的时代,我们都知道群体会议不是为数千人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一个大型社会必须是结构化和集中化的,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
第三个原因涉及经济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物品的手段。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获得更多的某种必需品,而在另一天获得较少。由于个人有不同的才能,一个人往往会持续拥有某些必需品的过剩和其他必需品的不足。在成员配对较少的小型社会中,由此产生的必要物品转移可以通过互惠交换直接在个人或家庭对之间安排。但使得大型社会中直接的成对冲突解决效率低下的数学原理,也同样使得直接的成对经济转移效率低下。大型社会只有在拥有再分配经济(redistributive economy)以及互惠经济(reciprocal economy)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运作。超过个人需求的物品必须从个人转移到集中权威,然后由集中权威将物品重新分配给有缺口的个人。
要求大型社会进行复杂组织的最后一个考虑与人口密度有关。粮食生产者的大型社会不仅成员更多,而且人口密度也高于狩猎采集者的小型部落。每个由几十个猎人组成的部落占据一大片领地,在这片领地内他们可以获得对他们来说最基本的大部分资源。他们可以通过在部落战争间歇期间与邻近部落交易来获得剩余的必需品。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那个几十人的部落规模人口的领地将缩小到一个小区域,生活必需品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必须从该区域外获得。例如,人们不能仅仅把荷兰的16,000平方英里和16,000,000人口分成800,000个独立的领地,每个领地占地13英亩,作为一个由20人组成的自治部落的家园,这些人仍然自给自足地限制在他们的13英亩内,偶尔利用临时停战的机会来到他们小领地的边界,与下一个部落交换一些贸易物品和新娘。这样的空间现实要求人口密集的地区支持大型和复杂组织的社会。
因此,冲突解决、决策制定、经济和空间的考虑汇聚在一起,要求大型社会集中化。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握权力、获得信息、做出决策和重新分配物品的人打开了大门,让他们利用由此产生的机会来奖励自己和他们的亲戚。对于任何熟悉现代人群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渐确立了自己作为精英的地位,可能起源于几个以前地位平等的村庄氏族之一,后来变得比其他氏族”更平等”。
这些就是大型社会无法以部落组织形式运作,而必须是复杂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ies)的原因。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小型、简单的社会实际上是如何演变或合并成大型、复杂社会的。合并、集中化的冲突解决、决策制定、经济再分配和盗贼式宗教不会仅仅通过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自动发展起来。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合并?
部分答案取决于演化推理。我在本章开头就说过,归类在同一类别的社会并非完全相同,因为人类和人类群体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例如,在部落(bands)和氏族(tribes)中,有些大人物(big-men)必然比其他人更具魅力、更有权力、更善于做出决策。在大型氏族中,那些拥有更强大的大人物、因而具有更高集权程度的氏族,往往比集权程度较低的氏族更有优势。像法尤人(Fayu)那样解决冲突能力差的氏族往往会再次分裂成部落,而治理不善的酋邦(chiefdoms)则会分裂成更小的酋邦或氏族。拥有有效冲突解决机制、合理决策能力和和谐经济再分配的社会,能够发展出更好的技术,集中军事力量,夺取更大、更富饶的领土,并逐个击溃自治的小型社会。
因此,同一复杂程度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导致出现下一复杂程度的社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氏族征服或合并其他氏族以达到酋邦的规模,酋邦征服或合并其他酋邦以达到国家的规模,国家征服或合并其他国家以成为帝国。更一般地说,大型单位相比单个小型单位可能享有优势——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大型单位能够解决伴随其更大规模而来的问题,例如来自新兴领导权觊觎者的长期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不满,以及与经济整合相关的日益增多的问题。
小型单位合并成大型单位的过程在历史上或考古学上经常有记载。与卢梭的观点相反,这种合并从来不是通过不受威胁的小社会自由决定合并来促进其公民幸福的过程实现的。小社会的领导者和大社会的领导者一样,都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权。合并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发生的:在外部力量威胁下的合并,或通过实际征服。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说明每种合并模式。
在外部力量威胁下的合并,切罗基印第安人联邦(Cherokee Indian confederation)在美国东南部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证。切罗基人最初分为30到40个独立的酋邦,每个酋邦由一个约400人的村庄组成。白人定居者的不断增加导致切罗基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当个别切罗基人抢劫或袭击白人定居者和商人时,白人无法区分不同的切罗基酋邦,而是不加区别地对任何切罗基人进行报复,要么通过军事行动,要么通过切断贸易。作为回应,切罗基酋邦在18世纪逐渐发现自己不得不联合成一个联邦。最初,1730年较大的酋邦选择了一位总领袖,一位名叫莫伊托伊(Moytoy)的酋长,1741年由他的儿子继任。这些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惩罚袭击白人的个别切罗基人,并与白人政府打交道。大约在1758年,切罗基人将他们的决策制度化,建立了一个年度议事会,以之前的村庄议事会为模板,在一个村庄(埃乔塔Echota)召开会议,该村庄因此成为事实上的”首都”。最终,切罗基人识字了(正如我们在第12章中看到的),并采用了成文宪法。
因此,切罗基联邦的形成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以前相互嫉妒的较小实体的合并,这些实体只有在受到强大外部力量的毁灭威胁时才合并。以类似的方式,在每本美国历史教科书中都有描述的一个国家形成的例子中,白人美洲殖民地本身——其中之一(乔治亚州Georgia)曾促成了切罗基国家的形成——在受到英国君主制这一强大外部力量的威胁时,被迫组成自己的国家。美洲殖民地最初像切罗基酋邦一样珍视自己的自治权,它们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1781年)下的第一次合并尝试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为前殖民地保留了太多的自治权。只有进一步的威胁,特别是1786年的谢司起义(Shays’s Rebellion)和未解决的战争债务负担,才克服了前殖民地对牺牲自治权的极端不情愿,并推动它们在1787年通过了我们目前强有力的联邦宪法。19世纪德国嫉妒的公国统一同样困难。三次早期尝试(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1850年恢复的德意志邦联和1866年的北德意志邦联)都失败了,直到1870年法国宣战的外部威胁最终导致小公国们在1871年放弃了大部分权力给中央帝国德国政府。
除了在外部力量威胁下合并之外,复杂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模式是通过征服合并。一个有充分记录的例子是非洲东南部祖鲁国的起源。当白人定居者首次观察到祖鲁人时,他们被分成数十个小酋邦。在1700年代后期,随着人口压力上升,酋邦之间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在所有这些酋邦中,设计集中权力结构这个普遍问题被一个名叫丁吉斯瓦约的酋长最成功地解决了,他在1807年左右通过杀死一个对手获得了姆特特瓦酋邦的统治地位。丁吉斯瓦约发展了一种优越的集中军事组织,从所有村庄征召年轻男子,按年龄而不是按村庄将他们编成团。他还发展了优越的集中政治组织,在征服其他酋邦时避免屠杀,保持被征服酋长的家族完整,仅限于用愿意与丁吉斯瓦约合作的亲属替换被征服的酋长本人。他通过扩大争端裁决发展了优越的集中冲突解决机制。通过这种方式,丁吉斯瓦约能够征服并开始整合其他30个祖鲁酋邦。他的继任者通过扩大司法系统、治安和仪式来加强由此形成的祖鲁国雏形。
这个通过征服形成国家的祖鲁例子可以无限复制。18和19世纪恰好被欧洲人目睹从酋邦形成的土著国家包括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国、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国、马达加斯加的梅里纳国、莱索托和斯威士以及除祖鲁之外的其他南非国家、西非的阿散蒂国,以及乌干达的安科莱和布干达国。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通过15世纪的征服形成的,但我们从早期西班牙定居者转录的印第安人口述历史中了解了很多关于它们形成的情况。罗马国的形成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帝国的扩张被同时代的古典作家详细描述。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战争,即使只是在部落之间,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常态。那么,为什么它们显然只是在过去13,000年内才开始导致社会合并呢?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复杂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口压力有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寻找人口压力与战争结果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当人口密集时战争往往会导致社会合并,而当人口稀疏时却不会?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密度,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地方,如狩猎采集部落占据的地区通常的情况,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需远离他们的敌人。这往往是新几内亚和亚马逊地区游牧部落之间战争的结果。
在人口密度适中的地方,如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没有大片空地可供战败部落的幸存者逃往。但没有集约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没有使用奴隶的需求,也不会产生足够大的粮食盈余来支付大量贡品。因此胜利者对战败部落的幸存者没有用处,除非娶走女人。战败的男人被杀死,他们的领土可能被胜利者占领。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如国家或酋邦占据的地区,战败者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现在有两种选择可以在让他们活着的同时剥削他们。由于酋邦和国家社会有经济专业化(specialization),战败者可以被用作奴隶,就像圣经时代常见的那样。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拥有能够产生大量盈余的集约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留在原地,但剥夺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让他们定期缴纳粮食或货物贡品,并将他们的社会合并到胜利的国家或酋邦中。这一直是有记载历史中与国家或帝国建立相关的战斗的通常结果。例如,西班牙征服者希望从墨西哥战败的土著人口那里索取贡品,所以他们对阿兹特克帝国的贡品清单非常感兴趣。结果发现,阿兹特克人每年从臣服民族那里获得的贡品包括7,000吨玉米、4,000吨豆类、4,000吨苋菜籽粒、2,000,000件棉布斗篷,以及大量可可豆、战争服装、盾牌、羽毛头饰和琥珀。
因此,粮食生产,以及社会之间的竞争和传播,作为根本原因,通过细节不同但都涉及大规模密集人口和定居生活的因果链,最终导致了征服的直接手段:病菌、文字、技术和集中化的政治组织。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在不同大陆上的发展各不相同,这些征服手段也随之不同。因此,这些手段往往相互关联地出现,但这种关联并非严格:例如,印加帝国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崛起,而阿兹特克则拥有文字却没有大规模流行病。丁吉斯瓦约的祖鲁人说明了这些手段在历史模式中各自独立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数十个祖鲁酋邦中,姆特特瓦酋邦在技术、文字或病菌方面相对其他酋邦没有任何优势,但它仍然成功击败了它们。其优势完全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此形成的祖鲁国家得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了非洲大陆的一部分。
当我和妻子玛丽在澳大利亚度假的一个夏天,我们决定参观梅宁迪镇附近沙漠中一处保存完好的土著岩画遗址。虽然我知道澳大利亚沙漠以干旱和夏季高温著称,但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沙漠和新几内亚热带草原炎热干燥的环境下工作过很长时间,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作为游客在澳大利亚面临的小挑战。带着充足的饮用水,玛丽和我在正午时分出发,徒步几英里前往岩画遗址。
从护林站出发的小径向上延伸,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穿过完全没有遮荫的开阔地带。我们呼吸着的炎热干燥空气让我想起坐在芬兰桑拿房里呼吸的感觉。当我们到达有岩画的悬崖遗址时,我们的水已经喝完了。我们也失去了对艺术的兴趣,所以继续向上前进,缓慢而有规律地呼吸着。不久我注意到一只鸟,明显是某种鹛科(babbler)鸟类,但与任何已知的鹛科物种相比,它显得异常巨大。那时,我意识到我平生第一次出现了热幻觉(heat hallucinations)。玛丽和我决定最好直接返回。
我们俩都停止了交谈。走路时,我们专注于听自己的呼吸,计算到下一个地标的距离,估算剩余时间。我的嘴巴和舌头现在很干燥,玛丽的脸红了。当我们终于到达有空调的护林站时,瘫坐在饮水机旁边的椅子上,喝完了饮水机里最后半加仑的水,并向护林员要了另一瓶。筋疲力尽地坐在那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我想到创作那些岩画的土著人曾在那片沙漠中度过他们的整个人生,没有空调避难所,却能设法找到食物和水。
对白人澳大利亚人来说,梅宁迪因一个多世纪前两个在沙漠干热中遭受更严重折磨的白人而闻名:爱尔兰警察罗伯特·伯克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威尔斯,他们是第一支从南到北穿越澳大利亚的欧洲探险队的不幸领队。伯克和威尔斯带着六头骆驼,装载了足够三个月的食物出发,但在梅宁迪以北的沙漠中耗尽了给养。他们三次遇到并被营养良好的土著人救助,那些土著人以沙漠为家,给探险者提供鱼、蕨类植物饼和烤肥鼠。但后来伯克愚蠢地向其中一个土著人开枪,于是整个群体都逃走了。尽管伯克和威尔斯相对于土著人拥有可用来狩猎的枪支这一巨大优势,但在土著人离开后的一个月内,他们还是饿死了、倒下了、死去了。
我和妻子在梅宁迪的经历,以及伯克和威尔斯的命运,让我生动地认识到在澳大利亚建立人类社会的困难。澳大利亚在所有大陆中脱颖而出:与澳大利亚和其他任何陆地之间的差异相比,欧亚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差异都显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亚是迄今为止最干旱、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不可预测、生物最贫乏的大陆。它是最后一个被欧洲人占领的大陆。在此之前,它支撑着最独特的人类社会和所有大陆中人口最少的人类群体。
因此,澳大利亚为关于大陆间社会差异的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检验。它拥有最独特的环境,也拥有最独特的社会。是前者导致了后者吗?如果是,如何导致的?澳大利亚是开始我们环游世界之旅的合理起点,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教训应用于理解所有大陆的不同历史。
大多数普通人在描述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时,会认为是他们看似的”落后性”。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在现代,所有土著民族仍然生活在没有任何所谓文明标志的大陆——没有农业、畜牧业、金属、弓箭、大型建筑、定居村庄、文字、酋邦或国家。相反,澳大利亚原住民是游牧或半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以部落群体(band)组织,居住在临时庇护所或小屋中,仍然依赖石器工具。在过去的13,000年里,澳大利亚积累的文化变化少于任何其他大陆。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普遍看法已经典型地体现在一位早期法国探险家的话中,他写道:“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最接近野兽的人类。”
然而,在40,000年前,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比欧洲和其他大陆的社会享有巨大的领先优势。澳大利亚土著开发了一些已知最早的带有磨光边缘的石器工具,最早的装柄石器工具(即安装在手柄上的石斧头),以及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一些已知最古老的岩石表面绘画来自澳大利亚。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可能在定居西欧之前就定居了澳大利亚。那么,尽管有这样的领先优势,为什么最终是欧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亚,而不是反过来?
在这个问题中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在更新世冰河时代期间,当大量海水被封存在大陆冰盖中,海平面远低于目前的水平时,现在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分隔开的浅阿拉弗拉海是低矮的干地。随着大约12,000至8,000年前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那片低地被淹没,原来的大澳大利亚大陆被分割成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两个半大陆(见第15章图15.1)。
这两个曾经相连的陆地上的人类社会在现代非常不同。与我刚才所说的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一切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如亚利的人民,是农民和养猪人。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中,政治上组织成部落(tribe)而不是部落群体(band)。所有新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使用陶器。新几内亚人往往拥有比澳大利亚人更坚固的住所、更适航的船只以及更多样化的器具。由于是粮食生产者而不是狩猎采集者,新几内亚人的平均人口密度远高于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的面积仅为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其土著人口却是澳大利亚的数倍。
为什么更新世大澳大利亚大陆分离出的较大陆地上的人类社会在发展上仍然如此”落后”,而较小陆地上的社会”进步”得更快?为什么新几内亚的所有这些创新没有传播到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仅隔着托雷斯海峡90英里的海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地理距离甚至不到90英里,因为托雷斯海峡散布着由使用弓箭的农民居住的岛屿,这些岛民在文化上类似于新几内亚人。最大的托雷斯海峡岛屿距离澳大利亚仅10英里。岛民与澳大利亚土著以及新几内亚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两个如此不同的文化世界如何能够在仅10英里宽、经常被独木舟穿越的平静海峡两侧维持自己?
与澳大利亚土著相比,新几内亚人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先进的”。但大多数其他现代人甚至认为新几内亚人”落后”。直到19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在新几内亚殖民之前,所有新几内亚人都是无文字的,依赖石器工具,政治上尚未组织成国家或(除少数例外)酋邦。尽管新几内亚人已经”进步”超越了澳大利亚土著,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像许多欧亚大陆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那样”进步”?因此,亚利的人民和他们的澳大利亚表亲提出了一个谜题中的谜题。
当被要求解释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的文化”落后性”时,许多白人澳大利亚人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所谓的原住民自身的缺陷。在面部结构和肤色上,原住民确实看起来与欧洲人不同,导致一些19世纪末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猿类和人类之间缺失的一环。否则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白人英国殖民者在殖民一个大陆后的几十年内就创建了一个有文字的、粮食生产的、工业化的民主社会,而该大陆的居民在超过40,000年后仍然是无文字的狩猎采集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铁和铝矿藏,以及丰富的铜、锡、铅和锌储量。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不知道金属工具,生活在石器时代?
这看起来像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完美对照实验。大陆是相同的;只有人不同。因此,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和欧洲-澳大利亚社会之间差异的解释必定在于组成它们的不同的人。这种种族主义结论背后的逻辑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我们将看到,它包含一个简单的错误。
作为检验这一逻辑的第一步,让我们先考察这些民族本身的起源。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都在至少4万年前就有人居住了,那时它们仍然连接在一起,形成大澳大利亚洲。看一眼地图(图15.1)就会发现,这些殖民者最初必定来自最近的大陆——东南亚,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跳岛方式到达。这一结论得到了现代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亚洲人之间遗传关系的支持,也得到了今天在菲律宾、马来半岛和缅甸外海的安达曼群岛上仍存活着的一些外貌相似人群的支持。
一旦殖民者到达大澳大利亚洲的海岸,他们就迅速遍布整个大陆,甚至占据了最遥远和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4万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证明了他们在澳大利亚西南角的存在;3.5万年前,他们到达了澳大利亚东南角和塔斯马尼亚,这是距离殖民者可能在西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距离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最近的部分)登陆点最远的澳大利亚角落;到3万年前,他们已经到达了寒冷的新几内亚高地。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从西部登陆点通过陆路到达。然而,在3.5万年前对新几内亚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殖民,需要进一步跨越数十英里的水域。这次占领可能比从4万年前到3万年前这段明显的传播时期更加迅速,因为这些不同的日期在放射性碳测年法的实验误差范围内几乎没有差异。
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最初被占据的更新世时期,亚洲大陆向东延伸,包括了现代的婆罗洲、爪哇和巴厘岛,比东南亚现在的边缘更接近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近1000英里。然而,从婆罗洲或巴厘岛到达更新世大澳大利亚洲,仍然需要穿越至少8条宽达50英里的海峡。4万年前,这些穿越可能是通过竹筏完成的,这是一种技术含量低但适合航海的水上交通工具,今天在中国南方沿海仍在使用。然而,这些穿越一定很困难,因为在4万年前的最初登陆之后,考古记录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数万年内有来自亚洲的进一步人类抵达大澳大利亚洲。直到最近几千年内,我们才遇到下一个确凿证据,即在新几内亚出现了源自亚洲的猪,在澳大利亚出现了源自亚洲的狗。
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类社会在与建立它们的亚洲社会基本隔离的状态下发展。这种隔离反映在今天使用的语言中。经过了这么多千年的隔离,现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新几内亚的主要语言群体(所谓的巴布亚语)都没有显示出与任何现代亚洲语言的明确关系。
这种隔离也反映在基因和体质人类学上。遗传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高地人与现代亚洲人的相似度略高于与其他大陆人群的相似度,但这种关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外貌上,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也与大多数东南亚人群不同,如果将澳大利亚人或新几内亚人的照片与印度尼西亚人或中国人的照片进行比较,这一点就会变得明显。造成所有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亚洲的最初亚洲殖民者有很长的时间与他们留在家乡的亚洲表亲分化,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有限的基因交流。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大澳大利亚洲殖民者所源自的原始东南亚血统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中国扩张出来的其他亚洲人所取代。
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在遗传、体质和语言上也相互分化了。例如,在主要的(由基因决定的)人类血型中,所谓ABO系统的B型血和MNS系统的S型血在新几内亚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但在澳大利亚几乎不存在。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紧密卷曲的头发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直发或波浪发形成对比。澳大利亚语言和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不仅与亚洲语言无关,彼此之间也没有关系,除了托雷斯海峡两个方向有一些词汇的传播。
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所有这些分化反映了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长期隔离的结果。自从大约1万年前阿拉弗拉海最终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彼此分开以来,基因交流仅限于通过托雷斯海峡岛链的微弱接触。这使得两个半大陆的人口能够适应各自的环境。虽然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与澳大利亚北部相当相似,但两个半大陆的其他栖息地几乎在所有主要方面都不同。
以下是一些差异。新几内亚几乎位于赤道上,而澳大利亚延伸到温带地区,几乎到达赤道以南40度。新几内亚多山且极为崎岖,海拔高达16,500英尺,最高峰被冰川覆盖,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低平——94%的面积海拔低于2,000英尺。新几内亚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澳大利亚则是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超过100英寸,高地的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英寸,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少于20英寸。新几内亚的赤道气候在季节和年份之间变化不大,但澳大利亚的气候具有高度季节性,年际变化远超任何其他大陆。因此,新几内亚分布着永久性的大河,而澳大利亚常年流动的河流在大多数年份仅限于澳大利亚东部,即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系统(墨累-达令河)在干旱期间也会停止流动数月。新几内亚的大部分陆地被茂密的雨林覆盖,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沙漠和开阔的干燥林地。
新几内亚覆盖着年轻肥沃的土壤,这是火山活动、冰川反复前进和后退并冲刷高地、以及山间溪流向低地输送大量淤泥的结果。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拥有所有大陆中最古老、最贫瘠、养分流失最严重的土壤,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几乎没有火山活动,也缺乏高山和冰川。尽管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新几内亚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数量与澳大利亚大致相当——这是新几内亚的赤道位置、更高的降雨量、更大的海拔范围和更高肥力的结果。所有这些环境差异都影响了两个半大陆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我们现在将对此进行考察。
大澳大利亚最早和最集约化的食物生产,以及最稠密的人口,出现在新几内亚海拔4,000到9,000英尺之间的高地山谷。考古发掘发现了可追溯到9,000年前的复杂排水沟系统,到6,000年前变得广泛,还有用于在干旱地区保持土壤湿度的梯田。这些沟渠系统与今天高地仍在使用的排干沼泽地用作菜园的系统相似。大约在5,000年前,花粉分析证明高地山谷出现了广泛的森林砍伐,表明为农业清理森林。
如今,高地农业的主要作物是最近引进的甘薯,以及芋头、香蕉、山药、甘蔗、可食用草茎和几种叶菜。由于芋头、香蕉和山药原产于东南亚——一个毫无疑问的植物驯化地点,过去人们认为新几内亚高地除甘薯外的作物都来自亚洲。然而,人们最终意识到甘蔗、叶菜和可食用草茎的野生祖先是新几内亚物种,新几内亚种植的特定类型香蕉的野生祖先是新几内亚而非亚洲的,芋头和一些山药既原产于新几内亚也原产于亚洲。如果新几内亚农业真的起源于亚洲,人们可能会期望找到明确来自亚洲的高地作物,但并没有。基于这些原因,现在普遍承认农业是通过驯化新几内亚野生植物物种在新几内亚高地独立产生的。
因此,新几内亚与肥沃月湾、中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地区一起,成为世界植物驯化独立起源中心之一。6,000年前高地实际种植的作物遗存并未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然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代高地主要作物是除非在特殊条件下否则不会留下考古可见遗迹的植物物种。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很可能也是高地农业的创始作物,特别是因为保存下来的古代排水系统与用于种植芋头的现代排水系统非常相似。
第一批欧洲探险家所见的新几内亚高地食物生产中三个明确的外来元素是鸡、猪和甘薯。鸡和猪在东南亚被驯化,大约3,600年前由南岛人(Austronesians)引入新几内亚和大多数其他太平洋岛屿,南岛人是一个最终起源于华南的民族,我们将在第17章讨论。(猪可能更早到达。)至于原产于南美洲的甘薯,它显然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到达新几内亚的,是在西班牙人将其引入菲律宾之后。甘薯在新几内亚扎根后,取代芋头成为高地的主要作物,因为它成熟所需时间更短、每英亩产量更高、对贫瘠土壤条件的耐受性更强。
新几内亚高地农业的发展一定在数千年前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爆炸,因为在新几内亚原有的巨型有袋动物大型哺乳动物群(megafauna)被灭绝后,高地只能支持非常低密度的狩猎采集者人口。红薯的到来在最近几个世纪引发了进一步的人口爆炸。当欧洲人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飞越高地时,他们惊讶地看到下面的景观类似于荷兰。广阔的山谷完全被砍伐,散布着村庄,整个谷底都覆盖着经过排水和围栏的集约化粮食生产田地。这种景观证明了使用石器工具的农民在高地实现的人口密度。
陡峭的地形、持续的云层覆盖、疟疾以及低海拔地区的干旱风险,将新几内亚高地农业限制在海拔约4000英尺以上。实际上,新几内亚高地是一个密集农业人口的岛屿,被推向天空,下方被云海包围。海岸和河流沿岸的新几内亚低地居民是高度依赖鱼类的村民,而那些远离海岸和河流的干燥地面上的人则以香蕉和山药为基础的刀耕火种农业(slash-and-burn agriculture)为生,人口密度较低,并辅以狩猎和采集。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低地沼泽居民作为游牧狩猎采集者生活,依赖野生西米棕榈(sago palms)的富含淀粉的髓,这种植物产量很高,每小时工作产生的卡路里是园艺的三倍。因此,新几内亚沼泽提供了一个环境的明确例证,在这里人们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因为农业无法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竞争。
在低地沼泽中坚持食用西米的人们体现了游牧狩猎采集者的群体组织(band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过去一定是所有新几内亚人的特征。由于我们在第13章和第14章讨论的所有原因,农民和渔民是发展出更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群体。他们生活在永久性村庄和部落社会中,通常由大人物(big-man)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建造大型的、装饰精美的仪式房屋。他们的伟大艺术,以木雕和面具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备受珍视。
新几内亚因此成为大澳大利亚地区中拥有最先进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艺术的部分。然而,从美国或欧洲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新几内亚仍然被评为”原始”而不是”先进”。为什么新几内亚人继续使用石器工具而不是发展金属工具,仍然不识字,并且未能将自己组织成酋邦(chiefdoms)和国家?事实证明,新几内亚有几个生物和地理上的不利因素。
首先,虽然本土粮食生产确实在新几内亚高地出现,但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它产生的蛋白质很少。膳食主食是低蛋白质的块根作物,唯一的家养动物物种(猪和鸡)的产量太低,无法为人们的蛋白质预算做出太多贡献。由于猪和鸡都不能被套上拉车,高地人除了人力之外没有其他动力源,也未能演化出流行病(epidemic diseases)来击退最终的欧洲入侵者。
对高地人口规模的第二个限制是可用面积有限:新几内亚高地只有少数宽阔的山谷,特别是瓦吉谷(Wahgi Valley)和巴列姆谷(Baliem Valley),能够支持密集人口。第三个限制是,海拔4000至9000英尺之间的中山地带(mid-montane zone)是新几内亚唯一适合集约化粮食生产的海拔带。在新几内亚海拔9000英尺以上的高山栖息地完全没有粮食生产,在4000至1000英尺之间的山坡上很少,在低地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种农业。因此,新几内亚从未发展出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不同海拔社区之间的大规模粮食经济交换。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这种交换不仅通过为所有海拔地区的人们提供更均衡的饮食来增加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还促进了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传统新几内亚的人口在欧洲殖民政府带来西方医学和结束部落间战争之前从未超过100万。在我们在第5章讨论的大约九个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中,新几内亚仍然是人口最少的一个。只有100万人口,新几内亚无法发展出中国、肥沃新月地带、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数千万人口中产生的技术、文字和政治系统。
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仅总体规模小,而且由于崎岖的地形而分散成数千个微观人口:低地大部分地区的沼泽,高地中陡峭的山脊和狭窄的峡谷交替出现,以及覆盖低地和高地的密林。当我在新几内亚从事生物考察时,由新几内亚人组成的团队作为野外助手,即使我们沿着现有的小路旅行,我也认为每天三英里是极好的进展。传统新几内亚的大多数高地人一生中从未离开家超过10英里。
这些地形困难,加上新几内亚部落或村庄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导致了传统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区:全球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集中在这个仅比德克萨斯州稍大的地区,分为数十个语系和孤立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像英语和中文一样大。近一半的新几内亚语言使用者不到500人,即使是最大的语言群体(仍然只有10万使用者)在政治上也分裂成数百个村庄,彼此之间的争斗与和其他语言使用者的争斗一样激烈。每个这样的微型社会单独来看都太小,无法支持酋长和专业工匠,也无法发展冶金术和文字。
除了人口规模小且分散之外,新几内亚发展的另一个限制是地理隔离,这限制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技术和思想的流入。新几内亚的三个邻居都被水域与新几内亚隔开,直到几千年前,它们在技术和粮食生产方面都比新几内亚(尤其是新几内亚高地)更加落后。在这三个邻居中,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新几内亚人而新几内亚人自己还不具备的东西。新几内亚的第二个邻居是东部更小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这就剩下新几内亚的第三个邻居——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但该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占据的文化落后地区。在新几内亚最初被殖民40000多年前之后,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岛语系扩张时期,没有任何物品可以被确认是通过印度尼西亚到达新几内亚的。
随着这次扩张,印度尼西亚被来自亚洲的粮食生产者占据,他们带来了家畜,带来了至少与新几内亚一样复杂的农业和技术,以及作为从亚洲到新几内亚更有效渠道的航海技能。南岛语族定居在新几内亚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岛屿上,以及新几内亚本身的最西端和北部及东南沿海地区。南岛语族向新几内亚引入了陶器、鸡,可能还有狗和猪。(早期考古调查声称公元前4000年新几内亚高地就有猪骨,但这些说法尚未得到证实。)至少在过去一千年里,贸易将新几内亚与技术上先进得多的爪哇和中国社会连接起来。作为出口天堂鸟羽毛和香料的回报,新几内亚人获得了东南亚商品,甚至包括东山铜鼓和中国瓷器等奢侈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岛语系扩张肯定会对新几内亚产生更大影响。西新几内亚最终会在政治上被并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苏丹国,金属工具可能会通过印度尼西亚东部传播到新几内亚。但是——这在公元1511年之前还没有发生,那一年葡萄牙人抵达摩鹿加群岛,截断了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发展进程。当欧洲人不久之后到达新几内亚时,那里的居民仍然生活在部落或激烈独立的小村庄中,仍然使用石器工具。
虽然大澳洲的新几内亚半大陆因此发展出了畜牧业和农业,但澳大利亚半大陆两者都没有发展出来。在冰河时代,澳大利亚拥有的大型有袋动物甚至比新几内亚还要多,包括双门齿兽(有袋动物中相当于牛和犀牛的物种)、巨型袋鼠和巨型袋熊。但所有这些可以驯化的有袋动物候选者都在伴随人类殖民澳大利亚的灭绝浪潮中消失了。这使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可驯化的本土哺乳动物。澳大利亚采用的唯一外来驯化哺乳动物是狗,它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亚洲(推测是在南岛语族的独木舟中)到达,并在澳大利亚野外建立起来,成为澳洲野犬。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把圈养的澳洲野犬作为伙伴、看门狗,甚至作为活毯子,由此产生了”五狗之夜”这个表达,意思是非常寒冷的夜晚。但他们不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用澳洲野犬/狗作为食物,也不像新几内亚人那样用它们来协作狩猎野生动物。
农业在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澳大利亚不仅是最干旱的大陆,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大陆大部分地区气候的压倒性影响是一个不规则的非年度周期——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的首字母缩写),而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所熟悉的规律性年度季节周期。不可预测的严重干旱持续数年,被同样不可预测的暴雨和洪水打断。即使在今天,有了欧亚作物,有了卡车和铁路来运输农产品,澳大利亚的粮食生产仍然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牲畜群在好年景增长,却在干旱中被杀死。澳大利亚土著中的任何初期农民都会在自己的人口中面临类似的周期。如果在好年景他们定居在村庄里,种植作物,生育婴儿,那么这些庞大的人口会在干旱年份挨饿和死亡,那时土地只能养活少得多的人口。
澳大利亚粮食生产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可驯化野生植物的匮乏。即使是现代欧洲植物遗传学家也未能从澳大利亚本土野生植物群中培育出除夏威夷果之外的任何作物。世界潜在优质谷物清单——56种颗粒最重的野生草本物种——仅包括两种澳大利亚物种,且两者都排在清单末尾(颗粒重量仅13毫克,而世界其他地区最重的颗粒重达40毫克)。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完全没有潜在作物,或者澳大利亚土著永远不会发展出本土粮食生产。一些植物,如某些种类的山药、芋头和竹芋,在新几内亚南部被种植,但也野生生长在澳大利亚北部,并被那里的土著采集。我们将看到,澳大利亚气候条件最有利地区的土著正朝着可能最终产生粮食生产的方向演化。但澳大利亚本土产生的任何粮食生产都会受到缺乏可驯化动物、可驯化植物贫乏以及土壤和气候困难等因素的限制。
游牧、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产的最少投资,是对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驱动的资源不可预测性的明智适应。当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只需迁移到条件暂时较好的地区。他们没有依赖少数几种可能失败的作物,而是通过发展基于多种野生食物的经济来最小化风险,这些食物不太可能同时全部失败。他们没有维持波动的人口,这种人口会周期性地超过资源供应并挨饿,而是维持较小的人口,在丰年享有充足的食物,在歉年也有足够的食物。
澳大利亚土著的粮食生产替代方式被称为”火棒农业”。土著以增加可食用植物和动物产量的方式改造和管理周围景观,而无需诉诸耕种。特别是,他们有意定期焚烧大片景观。这有几个目的:火驱赶出可以立即捕杀和食用的动物;火将茂密的灌木丛转变为人们可以更容易穿行的开阔草地;草地也是袋鼠的理想栖息地,袋鼠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猎物;火促进了袋鼠取食的新草和土著自己取食的蕨类植物根的生长。
我们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沙漠民族,但他们大多数不是。相反,他们的人口密度随降雨量(因为降雨控制陆地野生植物和动物食物的产量)以及海洋、河流和湖泊中水生食物的丰富程度而变化。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是澳大利亚最湿润和最富饶的地区: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流系统、东部和北部海岸以及西南角。这些地区后来也支撑了现代澳大利亚欧洲定居者的最密集人口。我们认为土著是沙漠民族的原因很简单:欧洲人杀害或驱逐了他们出最理想的地区,使最后完整的土著人口仅存在于欧洲人不想要的地区。
在过去5000年中,其中一些富饶地区见证了土著食物采集方法的集约化以及土著人口密度的增加。澳大利亚东部开发出了通过浸出或发酵毒素来使丰富且富含淀粉但剧毒的苏铁种子可食用的技术。澳大利亚东南部以前未被开发的高地开始被土著在夏季定期造访,他们不仅享用苏铁坚果和山药,还享用一种叫做博贡蛾的迁徙蛾类巨大的冬眠聚集群,这种蛾烤制后味道像烤栗子。另一种发展起来的集约化食物采集活动是墨累-达令河流系统的淡水鳗鱼渔业,那里沼泽的水位随季节性降雨而波动。澳大利亚土著建造了长达一英里半的精巧运河系统,使鳗鱼能够从一个沼泽延伸到另一个沼泽。鳗鱼通过同样精巧的鱼梁、设置在死胡同侧运河中的陷阱以及跨运河的石墙捕获,石墙开口处放置渔网。沼泽中不同水位的陷阱随着水位上升和下降而发挥作用。虽然这些”养鱼场”的初始建设必定涉及大量工作,但它们随后养活了许多人。19世纪的欧洲观察者在鳗鱼养殖场发现了有十几座土著房屋的村庄,还有多达146座石屋村庄的考古遗迹,这意味着至少季节性常驻人口达数百人。
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个发展是收获野生小米的种子,这种小米与中国早期农业的主要作物黍属于同一属。小米用石刀收割,堆成干草堆,脱粒以获得种子,然后储存在皮袋或木盘中,最后用磨石研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石制收割刀和磨石,与肥沃月湾独立发明的用于处理其他野生草本种子的工具相似。在澳大利亚土著的所有食物获取方法中,小米收获可能是最有可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生产的方法。
在过去5000年里,随着食物采集的强化,新型工具也随之出现。小型石刃和石尖相比它们所取代的大型石器,每磅工具提供了更长的锋利边缘。曾经仅在澳大利亚局部地区存在的磨制石斧变得普遍。贝壳鱼钩在最近一千年内出现。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政治复杂的社会?一个主要原因是原住民始终是狩猎采集者,而正如我们在第12-14章中看到的,这些发展在其他地方只出现在人口众多且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中。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的不可预测性将其狩猎采集人口限制在仅几十万人。与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数千万人相比,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拥有的潜在发明者要少得多,能够尝试采用创新的社会也少得多。澳大利亚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织成紧密互动的社会。相反,澳大利亚原住民由人烟稀少的沙漠海洋组成,分隔着几个生产力较高的生态”岛屿”,每个岛屿只容纳大陆人口的一小部分,彼此之间的互动因距离而减弱。即使在大陆相对湿润和富饶的东部地区,社会之间的交流也受到限制,从昆士兰东北部的热带雨林到维多利亚东南部的温带雨林相距1900英里,这一地理和生态距离相当于从洛杉矶到阿拉斯加的距离。
澳大利亚某些明显的区域性或全大陆范围的技术退化可能源于其人口中心的孤立和相对较少的居民。回旋镖这一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遗弃了。当欧洲人遇到他们时,澳大利亚西南部的原住民不吃贝类。大约5000年前出现在澳大利亚考古遗址中的小型石尖的功能仍不确定:虽然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它们可能被用作矛尖和倒钩,但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箭矢上使用的石尖和倒钩惊人地相似。如果它们真的是这样使用的,那么弓箭在现代新几内亚存在但在澳大利亚不存在的谜团可能会更加复杂:也许弓箭实际上曾被采用过一段时间,然后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被遗弃了。所有这些例子让我们想起日本放弃枪支,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放弃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孤立社会放弃其他技术的情况(第13章)。
澳大利亚地区技术损失最极端的地方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该岛距离澳大利亚东南海岸130英里。在更新世海平面较低的时期,现在将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分隔开的浅海巴斯海峡是陆地,居住在塔斯马尼亚的人们是连续分布在扩大的澳大利亚大陆上的人口的一部分。当海峡在大约10000年前最终被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大陆人彼此隔绝,因为两个群体都没有能够穿越巴斯海峡的水上交通工具。此后,塔斯马尼亚的4000名狩猎采集者与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失去了联系,生活在一种只有科幻小说中才知道的孤立状态中。
当欧洲人在公元1642年最终遇到他们时,塔斯马尼亚人拥有现代世界上任何民族中最简单的物质文化。像大陆原住民一样,他们是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者。但他们也缺乏大陆上广泛存在的许多技术和器物,包括带倒钩的长矛、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回旋镖、磨制或抛光石器、装柄石器、鱼钩、网、多叉矛、陷阱,以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做法。其中一些技术可能是在塔斯马尼亚被隔离后才到达或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被发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数稀少的塔斯马尼亚人口没有独立发明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中的另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时被带到那里的,后来在塔斯马尼亚的文化隔离中消失了。例如,塔斯马尼亚的考古记录记录了捕鱼以及锥子、针和其他骨制工具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消失。在至少三个较小的岛屿(弗林德斯岛、袋鼠岛和国王岛)上,这些岛屿在大约10000年前因海平面上升而与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隔离,最初人口约为200到400人的人类种群完全灭绝了。
塔斯马尼亚岛和那三个更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展示了一个对世界历史具有广泛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人类种群无法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4,000人的种群能够存续1万年,但伴随着显著的文化损失和明显的发明失败,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简化物质文化。澳大利亚大陆的30万狩猎采集者比塔斯马尼亚人数更多、隔离程度更低,但仍然构成了所有大陆中规模最小、最孤立的人类种群。澳大利亚大陆上有记载的技术退化实例,以及塔斯马尼亚的例子,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其他大陆民族相比技能储备有限,可能部分源于隔离和种群规模对技术发展和维持的影响——类似于对塔斯马尼亚的影响,但程度较轻。由此推论,同样的影响可能也导致了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次小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技术差异。
为什么更先进的技术没有从澳大利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被水域分隔,生态环境也大不相同。此外,印度尼西亚本身直到几千年前还是一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没有证据表明在澳大利亚最初于4万年前被殖民之后,有任何新技术或引入从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dingo)出现。
澳洲野犬在南岛语系(Austronesian)从中国南方经印度尼西亚扩张的高峰期到达澳大利亚。南岛语系族群成功定居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岛屿,包括距离澳大利亚最近的两个岛屿——帝汶岛和塔宁巴尔岛(分别距离现代澳大利亚仅275英里和205英里)。由于南岛语系族群在跨太平洋扩张过程中跨越了更远的海上距离,即使没有澳洲野犬的证据证明,我们也必须假设他们曾反复到达澳大利亚。在历史时期,澳大利亚西北部每年都会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望加锡地区的航海独木舟来访,直到澳大利亚政府在1907年停止这些访问。考古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而且很可能更早就开始了。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海参(也称为bêche-demer或trepang),这是一种海星类生物,从望加锡出口到中国,被认为是催情剂和汤品的珍贵配料。
自然地,望加锡人年度访问期间发展起来的贸易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许多遗产。望加锡人在沿海营地种植罗望子树,并与原住民妇女生育了孩子。布料、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作为贸易品被带来,尽管原住民从未学会自己制造这些物品。原住民确实从望加锡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外来词、一些仪式,以及使用独木航海舟和用烟斗吸烟的做法。
但这些影响都没有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特征。比望加锡人访问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望加锡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无疑是因为面向印度尼西亚的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对望加锡农业来说过于干旱。如果印度尼西亚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望加锡人本可以定居,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到过那么远的地方。由于望加锡人因此只是少量临时来访,从未深入内陆,只有少数澳大利亚人在狭长的海岸线上接触到他们。即使是那少数澳大利亚人也只看到了望加锡文化和技术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一个拥有稻田、猪、村庄和作坊的完整望加锡社会。由于澳大利亚人仍然是游牧狩猎采集者,他们只获得了少数与其生活方式相容的望加锡产品和做法。独木航海舟和烟斗,可以;铁匠铺和猪,不行。
显然,比澳大利亚人对印度尼西亚影响的抵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新几内亚影响的抵制。在被称为托雷斯海峡的狭窄水带对面,说新几内亚语言、拥有猪、陶器和弓箭的新几内亚农民面对着说澳大利亚语言、缺乏猪、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亚狩猎采集者。此外,这个海峡不是开阔水域屏障,而是散布着一连串岛屿,其中最大的(穆拉鲁格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仅10英里。澳大利亚和这些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和新几内亚之间有定期的贸易访问。许多原住民妇女作为妻子来到穆拉鲁格岛,在那里她们看到了园圃和弓箭。为什么这些新几内亚特征没有传播到澳大利亚呢?
托雷斯海峡的这种文化屏障之所以令人惊讶,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误导自己,想象在距离澳大利亚海岸1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完整的新几内亚社会,拥有集约农业和猪。实际上,约克角原住民从未见过新几内亚大陆人。相反,贸易发生在新几内亚和最靠近新几内亚的岛屿之间,然后在这些岛屿和海峡中部的马布亚格岛之间,然后在马布亚格岛和海峡更南边的巴杜岛之间,然后在巴杜岛和穆拉拉格岛之间,最后在穆拉拉格岛和约克角之间。
新几内亚社会沿着这条岛链逐渐减弱。猪在这些岛屿上很稀少或根本没有。托雷斯海峡沿岸的新几内亚低地南部居民实行的不是新几内亚高地的集约农业,而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农业,严重依赖海产品、狩猎和采集。即使是这些刀耕火种的做法,其重要性也沿着岛链从新几内亚南部向澳大利亚方向递减。穆拉拉格岛本身,即最靠近澳大利亚的岛屿,是干旱的,不适合农业,只养活了一小部分人口,主要靠海产品、野生山药和红树林果实为生。
因此,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跨越托雷斯海峡的交界面让人想起儿童的传话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孩子们围成一圈,一个孩子对第二个孩子耳语一个词,第二个孩子把她认为自己刚听到的话传给第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传回给第一个孩子的词与最初的词毫无相似之处。同样,沿托雷斯海峡岛屿的贸易就像一场传话游戏,最终呈现给约克角原住民的东西与新几内亚社会大不相同。此外,我们不应该想象穆拉拉格岛民和约克角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是一场不间断的盛宴,原住民急切地从岛屿教师那里吸收文化。贸易与战争交替进行,目的是猎头和抓捕妇女成为妻子。
尽管新几内亚文化因距离和战争而被稀释,但一些新几内亚的影响确实设法到达了澳大利亚。通婚将新几内亚的身体特征,如卷曲而非直发,带到了约克角半岛。约克角的四种语言有澳大利亚不常见的音位(phonemes),可能是受到新几内亚语言的影响。最重要的传播是新几内亚贝壳鱼钩,传播到澳大利亚很远的地方,以及新几内亚外伸支架独木舟(outrigger canoes),沿约克角半岛传播。新几内亚的鼓、仪式面具、葬礼柱和烟斗也在约克角被采用。但约克角原住民没有采用农业,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穆拉拉格岛看到的农业太过稀释。他们没有采用猪,因为岛上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猪,而且在没有农业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喂养猪。他们也没有采用弓箭,而是继续使用长矛和投矛器(spear-throwers)。
澳大利亚很大,新几内亚也很大。但这两个大陆块之间的接触仅限于少数几个托雷斯海峡岛民小群体,他们拥有高度衰减的新几内亚文化,与少数几个约克角原住民小群体互动。后者群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使用长矛而不是弓箭,并且不采用他们所看到的稀释的新几内亚文化的某些其他特征,阻止了这些新几内亚文化特征传播到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结果,除了贝壳鱼钩之外,没有新几内亚特征传播到澳大利亚很远的地方。如果新几内亚凉爽高地的数十万农民与澳大利亚东南部凉爽高地的原住民有密切接触,集约粮食生产和新几内亚文化可能会大规模转移到澳大利亚。但新几内亚高地与澳大利亚高地之间被2000英里生态差异极大的地貌所隔开。就澳大利亚人观察和采用新几内亚高地做法的机会而言,新几内亚高地可能和月球上的山一样遥远。
简而言之,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游牧狩猎采集者的持续存在,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民和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进行贸易,乍一看似乎表明澳大利亚土著有一种特殊的固执。仔细研究后,这仅仅证明了地理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无处不在的作用。
我们还需要考虑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石器时代社会与铁器时代欧洲人的相遇。一位葡萄牙航海家在1526年”发现”了新几内亚,荷兰在1828年宣称占有西半部,英国和德国在1884年瓜分了东半部。最早的欧洲人定居在海岸,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深入内陆,但到1960年,欧洲政府已经建立了对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政治控制。
欧洲人殖民新几内亚,而不是反过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拥有远洋船只和罗盘来到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来制作地图、描述性记录和管理文书,这些对于建立对新几内亚的控制很有用;他们有政治制度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有枪支来射杀那些用弓箭和棍棒反抗的新几内亚人。然而,欧洲定居者的数量一直非常少,今天新几内亚仍然主要由新几内亚人居住。这与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地方,欧洲定居者数量众多且持久,并在大片地区取代了原住民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不同?
一个主要因素是直到1880年代一直击败欧洲人在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所有尝试的原因: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些疾病都不是第11章讨论的急性流行性人群感染(crowd infection)。这些失败的低地定居计划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个,是1880年左右由法国侯爵德雷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的,结果是1000名殖民者中有930人在三年内死亡。即使在今天有现代医疗手段可用,我在新几内亚的许多美国和欧洲朋友也因为疟疾、肝炎或其他疾病而被迫离开,而我自己在新几内亚的健康遗产是一年的疟疾和一年的痢疾。
当欧洲人被新几内亚低地的病菌击倒时,为什么欧亚病菌没有同时击倒新几内亚人?一些新几内亚人确实被感染了,但不是像杀死大部分澳大利亚和美洲原住民那样的大规模感染。新几内亚人的一个幸运之处是,直到1880年代才有欧洲人在新几内亚永久定居,到那时,公共卫生的发现已经在控制天花和欧洲人群的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语族扩张(Austronesian expansion)已经在3500年间给新几内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印度尼西亚定居者和商人。由于亚洲大陆的传染病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根深蒂固,新几内亚人因此获得了长期接触,并建立起了比澳大利亚土著人多得多的对欧亚病菌的抵抗力。
新几内亚唯一欧洲人不会遭受严重健康问题的地方是高地,在疟疾的海拔上限之上。但是高地已经被密集的新几内亚人口占据,直到1930年代才被欧洲人到达。到那时,澳大利亚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通过大量杀害原住民或将他们赶出土地来开放白人定居的土地,就像早期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期间发生的那样。
欧洲潜在定居者面临的剩余障碍是,欧洲作物、牲畜和生存方式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中到处表现不佳。虽然现在少量种植引进的热带美洲作物,如南瓜、玉米和西红柿,并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建立了茶叶和咖啡种植园,但欧洲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从未扎根。引进的牛和山羊,少量饲养,和欧洲人自己一样,遭受热带疾病的困扰。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仍然以新几内亚人在数千年过程中完善的作物和农业方法为主。
所有这些疾病、崎岖地形和生存的问题都导致欧洲人让新几内亚东部(现在的独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由新几内亚人占据和管理,尽管他们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用字母书写,生活在以英国为蓝本的民主政府制度下,并使用海外制造的枪支。新几内亚西部的结果不同,印度尼西亚在1963年从荷兰接管了那里,并将其更名为伊里安查亚省(Irian Jaya)。该省现在由印度尼西亚人管理,为印度尼西亚人服务。其农村人口仍然绝大多数是新几内亚人,但其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亚人,这是政府旨在鼓励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政策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人因长期接触与新几内亚人共有的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没有像欧洲人那样面临如此强大的病菌屏障(germ barrier)。他们也比欧洲人更有准备在新几内亚生存,因为印度尼西亚农业已经包括香蕉、甘薯和新几内亚农业的一些其他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亚正在发生的变化代表了3500年前开始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语族扩张的延续,并得到了中央政府全部资源的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是现代南岛语族人(Austronesians)。
欧洲人殖民了澳大利亚,而不是土著澳大利亚人殖民欧洲,原因与我们刚才在新几内亚案例中看到的相同。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今天,澳大利亚由2000万非原住民居住和管理,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后裔,以及自1973年澳大利亚废除之前的白澳移民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原住民人口下降了80%,从欧洲人定居时的约30万人降至1921年的最低6万人。今天的原住民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底层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传教站或政府保留地,或者在牧牛场为白人做牧民。为什么原住民的境遇比新几内亚人糟糕得多?
根本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某些地区)适合欧洲粮食生产和定居,加上欧洲人的枪支、病菌和钢铁在清除原住民方面所起的作用。虽然我已经强调了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所带来的困难,但其最具生产力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可以支持欧洲农业。澳大利亚温带地区的农业现在由欧亚温带地区的主要作物主导,包括小麦(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以及来自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高粱和棉花,以及来自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超出肥沃月湾作物最佳范围的热带地区,欧洲农民引进了来自新几内亚的甘蔗、来自热带东南亚的香蕉和柑橘类水果,以及来自热带南美的花生。至于牲畜,欧亚绵羊使得粮食生产能够扩展到澳大利亚不适合农业的干旱地区,而欧亚牛则在较湿润的地区与作物一起发展。
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从世界上气候相似但过于遥远的地区引进非本地作物和动物,这些驯化物直到通过跨洋航运才能到达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缺乏足以阻止欧洲人的严重疾病。只有在澳大利亚热带北部,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才迫使欧洲人放弃他们在19世纪的定居尝试,直到20世纪医学发展才获得成功。
当然,澳大利亚原住民阻碍了欧洲粮食生产,特别是因为潜在最具生产力的农田和乳品产区最初支撑着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原住民狩猎采集者。欧洲人的定居通过两种方式减少了原住民的数量。一种方式是射杀他们,这在19世纪和18世纪后期比1930年代进入新几内亚高地时更容易被欧洲人接受。最后一次大规模屠杀发生在1928年的艾丽斯泉,造成31名原住民死亡。另一种方式是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原住民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进化出遗传抗性。在1788年第一批欧洲定居者抵达悉尼的一年内,死于流行病的原住民尸体成为常见景象。主要记录的致命疾病包括天花、流感、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
通过这两种方式,独立的原住民社会在所有适合欧洲粮食生产的地区都被消灭了。唯一幸存下来或多或少完整的社会是那些位于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对欧洲人无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殖民的一个世纪内,原住民4万年的传统大部分被扫除。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在本章开头附近提出的问题。除了假设原住民本身存在缺陷之外,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白人英国殖民者在殖民一个大陆后的几十年内显然创建了一个有文字的、粮食生产的、工业化的民主社会,而这个大陆的居民在超过4万年后仍然是无文字的游牧狩猎采集者?这难道不构成人类社会演化的完美对照实验,迫使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种族主义结论吗?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很简单。白人英国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建一个有文字的、粮食生产的、工业化的民主社会。相反,他们从澳大利亚以外引进了所有这些要素:牲畜、所有作物(除了澳洲坚果)、冶金知识、蒸汽机、枪支、字母表、政治制度,甚至病菌。所有这些都是欧亚环境中1万年发展的最终产物。由于地理上的偶然,1788年登陆悉尼的殖民者继承了这些要素。如果没有继承的欧亚技术,欧洲人从未学会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生存。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和威廉·威尔斯(William Wills)足够聪明能够写作,但不够聪明在原住民生活的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生存。
真正在澳大利亚创建社会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当然,他们创建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粮食生产的、工业化的民主社会。原因直接源于澳大利亚环境的特点。
移民、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多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民族多样性——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是这些有争议政策的先驱,现在也是这些政策反弹的先驱。看看洛杉矶公立学校系统的教室,我的儿子们在那里接受教育,孩子们的面孔使抽象的辩论具体化了。这些孩子代表着80多种家庭使用的语言,说英语的白人占少数。我儿子们的每一个玩伴都至少有一位父母或祖父母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也适用于我自己儿子四位祖父母中的三位。但移民只是在恢复美国数千年来一直拥有的多样性。在欧洲人定居之前,美国大陆曾是数百个美洲原住民部落和语言的家园,直到最近一百年才受到单一政府的控制。
在这些方面,美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世界六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除了一个之外,都是最近才实现政治统一的大熔炉,仍然支持数百种语言和民族群体。例如,俄罗斯曾经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年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扩张。从那时到19世纪,俄罗斯吞并了数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仍保留着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正如美国历史是我们大陆如何变成美国的故事一样,俄罗斯历史就是俄罗斯如何变成俄罗斯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最近的政治创造物(或者在印度的情况下是重新创造),分别拥有约850、670和210种语言。
这个近期大熔炉规则的最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和语言上看起来是单一的,至少对外行来说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实现政治统一,此后大部分世纪都保持统一。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开始,它就只有一种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使用数十种改良字母表。中国12亿人口中,超过8亿人说普通话,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母语使用者最多的语言。另外约3亿人说其他七种语言,这些语言与普通话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就像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一样。因此,中国不仅不是一个大熔炉,而且问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似乎很荒谬。中国几乎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一直是中国。
我们如此理所当然地看待中国这种表面上的统一,以至于忘记了它有多么令人惊讶。我们不应该预期这种统一的一个原因是基因。虽然对世界人民的粗略种族分类把所有中国人归为所谓的蒙古人种(Mongoloids),但这个类别掩盖了比欧洲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差异更大的变化。特别是,北方和南方中国人在基因和身体上相当不同:北方中国人与西藏人和尼泊尔人最相似,而南方中国人则与越南人和菲律宾人相似。我的北方和南方中国朋友往往能通过外貌一眼就分辨出彼此:北方人往往更高、更重、肤色更浅、鼻子更尖、眼睛更小,看起来更”细长”(因为他们的内眦赘皮(epicanthic fold))。
中国南北方在环境和气候上也有所不同:北方更干燥、更冷;南方更潮湿、更热。在这些不同环境中产生的基因差异意味着中国南北方人民之间长期存在适度隔离的历史。那么这些人如何最终拥有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语言和文化呢?
从世界其他长期定居地区的语言不统一来看,中国表面上的语言近乎统一也令人费解。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人类历史只有约40,000年,却有一千种语言,包括数十个语言群,其差异远大于八种主要中国语言之间的差异。西欧在印欧语系到来后的6,000到8,000年间,已经演化或获得了约40种语言,包括英语、芬兰语和俄语等差异很大的语言。然而化石证明人类在中国存在了超过50万年。在那么长的时间跨度中,中国必定产生过数以万计的不同语言,它们都去哪儿了?
这些悖论暗示中国也曾经是多元化的,就像所有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一样。中国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更早地实现了统一。它的”汉化”(Sinification)涉及在一个古老的大熔炉中彻底同质化一个巨大的地区,重新填充热带东南亚,并对日本、韩国甚至可能对印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是理解整个东亚历史的关键。本章将讲述中国如何成为中国的故事。
中国详细的语言地图(见图16.1)是一个方便的起点。对我们这些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单一整体的人来说,看一眼这张地图就会大开眼界。事实证明,除了中国的八种”大”语言——普通话及其七种近亲(通常统称为”汉语”),每种语言的使用者在1100万到8亿之间——中国还有超过130种”小”语言,其中许多只有几千名使用者。所有这些”大”和”小”语言都属于四个语系,这些语系的分布紧密程度差异很大。
一个极端是,普通话及其近亲语言构成了汉藏语系的汉语支,从中国北方到南方连续分布。人们可以穿越中国,从北方的满洲到南方的北部湾,全程都在普通话及其近亲语言的母语使用者所占据的土地上行走。另外三个语系的分布则是碎片化的,由被其他语系使用者”海洋”包围的”岛屿”状人群使用。
特别碎片化的是苗瑶语系(又名Hmong-Mien)的分布,该语系包含约600万使用者,分布在大约五种语言中,这些语言有着丰富多彩的名称:红苗、白苗(又名花苗)、黑苗、青苗(又名蓝苗)和瑶族语。苗瑶语使用者生活在数十个小的飞地中,全部被其他语系的使用者包围,分散在50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内,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泰国。超过10万名来自越南的苗族难民将这个语系带到了美国,在那里他们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苗族(Hmong)。
另一个碎片化的语言群体是南亚语系,其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寨语。6000万南亚语系使用者分散在从东部的越南到南部的马来半岛再到西部的印度北部的广大地区。中国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语系是侗台语系(包括泰语和老挝语),其5000万使用者从中国南方向南分布到泰国半岛,向西分布到缅甸(图16.1)。
当然,苗瑶语使用者并不是通过古代直升机飞行将他们随处投放在亚洲大陆上而获得目前碎片化分布的。相反,人们可能会猜测他们曾经有更接近连续的分布,随着其他语系使用者的扩张或导致苗瑶语使用者放弃他们的语言而变得碎片化。事实上,这种语言碎片化的过程大部分发生在过去2500年内,并有充分的历史记录。现代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使用者的祖先都是在历史时期从中国南方及邻近地区向南迁移到他们现在的位置,相继淹没了之前迁移的定居后裔。汉语使用者在取代和语言转化其他族群方面尤其积极,汉语使用者将其他族群视为原始和低劣的。中国周朝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有记载历史,描述了讲汉语的国家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
我们可以使用几种推理类型来尝试重建几千年前东亚的语言地图。首先,我们可以逆转近几千年来历史上已知的语言扩张。其次,我们可以推断,现代占据大片连续区域的单一语言或相关语言群体证明了该群体最近的地理扩张,以至于没有足够的历史时间使其分化为许多语言。最后,我们可以反向推理,在给定语系内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现代区域更接近该语系的早期分布中心。
使用这三种推理类型来倒转语言时钟,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北方最初由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的使用者占据;中国南方的不同部分分别由苗瑶语、南亚语和侗台语系语言的使用者占据;汉藏语系使用者已经在中国南方取代了这些其他语系的大多数使用者。更剧烈的语言剧变一定席卷了中国以南的热带东南亚地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这些地区最初使用的任何语言现在一定已经完全灭绝,因为这些国家的所有现代语言似乎都是最近的入侵者,主要来自中国南方,或在少数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由于苗瑶语勉强存活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猜测中国南方除了苗瑶语、南亚语和侗台语之外,曾经还有其他语系,但这些其他语系没有留下现代幸存的语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南岛语系(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的所有语言都属于该语系)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其他语系之一,我们只知道它是因为它传播到太平洋岛屿并在那里幸存下来。
东亚的这些语言替换让我们想起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新世界的传播,那里曾是一千种或更多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家园。我们从近代历史中知道,英语取代美国印第安人语言并不仅仅是因为英语在印第安人耳中听起来悦耳。相反,这种替换伴随着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谋杀和引入的疾病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而幸存的印第安人被迫采用英语这种新的主流语言。这种语言替换的直接原因是入侵的欧洲人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相对于美洲原住民拥有的优势,这些优势最终源于食物生产的早期兴起。基本上相同的过程也解释了英语取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以及班图语言取代赤道以南非洲原有的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语言。
因此,东亚的语言剧变引发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使得汉藏语系使用者从华北扩散到华南,而南亚语系和其他原有的华南语系使用者向南扩散到热带东南亚?在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寻找一些亚洲人明显相对于其他亚洲人获得的技术、政治和农业优势的证据。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东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的考古记录只显示了使用未经打磨的石器且缺乏陶器的狩猎采集者的遗迹。东亚第一个不同的证据来自中国,那里的作物遗存、家畜骨骼、陶器和打磨过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500年。这个日期与肥沃月湾新石器时代和食物生产开始的时间相差不到一千年。但由于中国之前的千年在考古学上知之甚少,目前无法确定中国食物生产的起源是与肥沃月湾同时、稍早还是稍晚。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和动物驯化中心之一。
中国实际上可能包含两个或更多独立的食物生产起源中心。我已经提到了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和温暖潮湿的南方之间的生态差异。在同一纬度上,沿海低地和内陆高地之间也存在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原产于这些不同的环境,因此中国各地的早期农民可以获得的植物各不相同。事实上,最早被确认的作物是华北的两种抗旱小米,而华南则是水稻,这表明可能存在独立的北方和南方植物驯化中心。
拥有最早作物证据的中国遗址也包含了家猪、狗和鸡的骨骼。这些家畜和作物逐渐被中国的许多其他驯化物种所补充。在动物中,水牛最为重要(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是其他驯化动物。后来熟悉的中国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橘类水果、茶、杏、桃和梨。此外,正如欧亚大陆的东西走向使得许多这些中国动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传播一样,西亚的驯化物种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并在那里变得重要。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要的西方贡献包括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绵羊和山羊。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食物生产逐渐导致了第11-14章讨论的”文明”的其他标志。中国杰出的青铜冶金传统起源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最终导致中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发展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铸铁生产。接下来的1500年见证了第13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涌现,包括纸、指南针、独轮车和火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出现了设防城镇,墓地中未装饰墓葬和豪华装饰墓葬之间的巨大差异说明了新兴的阶级差异。能够动员大量平民劳动力的分层社会也通过巨大的城市防御墙、大型宫殿以及最终连接华北和华南的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超过1000英里长)得到证明。文字保存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但可能更早出现。我们对中国新兴城市和国家的考古学知识随后得到了中国最早朝代的文字记载的补充,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兴起的夏朝。
至于食物生产带来的更为险恶的副产品——传染病,我们无法具体说明旧大陆大多数主要疾病起源于旧大陆的何处。然而,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著作清楚地描述了鼠疫和可能的天花从东方传来,因此这些病菌可能起源于中国或东亚。流感(源自猪)更有可能起源于中国,因为猪在那里被驯化得如此之早并变得如此重要。
中国的面积和生态多样性孕育了许多独立的地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考古学上可以通过不同的陶器和器物风格来区分。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这些地方文化在地理上扩展开来,并开始相互影响、竞争和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作物交换丰富了中国的食物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部落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的国家的形成(第14章)。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阻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作为障碍的作用比在美洲或非洲要小,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小;而且中国既没有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横切,也没有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分隔。相反,中国漫长的东西向河流(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促进了作物和技术在沿海和内陆之间的传播,而其广阔的东西向延伸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个河流系统得以通过运河连接起来,促进了南北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都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欧虽然面积相似,但地形更加崎岖,也没有这样的统一河流,至今仍抵制文化和政治统一。
中国的一些发展是从南向北传播的,尤其是炼铁和水稻种植。但主要的传播方向是从北向南。这一趋势在文字方面最为明显:与西欧亚大陆产生了大量早期文字系统(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赫梯文字、米诺斯文字和闪米特字母)相比,中国只发展出了一个有充分证据的文字系统。它在华北地区得到完善,传播并抢占或取代了任何其他萌芽系统,并演变成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文字。华北社会向南传播的其他主要特征包括青铜技术、汉藏语系和国家形成。中国最初的三个朝代——夏朝、商朝和周朝——都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在华北兴起的。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保存下来的文献显示,当时华夏民族(正如今天许多人仍然如此)在文化上倾向于认为自己优于非华夏”蛮族”,而华北人甚至倾向于把华南人也视为蛮族。例如,一位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晚周作者这样描述中国的其他民族:“那五个地区的人民——中原诸国以及周围的戎、夷和其他野蛮部落——都有各自的本性,无法改变。东方的部落被称为夷。他们披散着头发,在身上纹身。他们中的一些人吃的食物不经火烹煮。”这位周朝作者继续描述南方、西方和北方的野蛮部落沉溺于同样野蛮的做法,如脚趾内翻、在前额纹身、穿着兽皮、住在洞穴里、不吃谷物,当然还有生吃食物。
由华北周朝建立或仿照的国家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传播到华南,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而达到顶峰。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化统一加速进行,因为有文字的”文明”华夏国家吸收了不识字的”蛮族”,或被他们模仿。一些文化统一是残酷的:例如,秦始皇谴责以前写的所有历史书籍毫无价值,并下令焚烧,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对早期中国历史和文字的理解。这些和其他严酷措施必定促成了华北的汉藏语系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传播,并使苗瑶语系和其他语系沦为现在的碎片化分布。
在东亚范围内,中国在食物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形成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的创新也极大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发展。例如,直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被采用卵石和薄片石器的狩猎采集者占据,这些石器属于所谓的和平(Hoabinhian)传统,以越南的和平遗址命名。此后,源自中国的作物、新石器技术、村落生活以及类似华南的陶器传播到东南亚热带地区,可能伴随着华南的语系。缅甸人、老挝人和泰国人从华南向南的历史扩张完成了东南亚热带地区的汉化。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华南同胞的近期分支。
中国的这股浪潮如此强大,以至于热带东南亚的原住民在该地区现代人口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只有三个残存的狩猎采集者群体——马来半岛的塞芒矮黑人(Semang Negritos)、安达曼群岛人(Andaman Islanders)和斯里兰卡的维达类矮黑人(Veddoid Negritos)——仍然存在,表明热带东南亚的前居民可能是深色皮肤、卷发的,就像现代新几内亚人一样,而不像浅色皮肤、直发的华南人以及作为他们分支的现代热带东南亚人。这些东南亚的残存矮黑人可能是新几内亚殖民来源人群的最后幸存者。塞芒矮黑人作为狩猎采集者持续存在,与邻近的农民进行贸易,但从这些农民那里采用了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语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菲律宾矮黑人和非洲俾格米人狩猎采集者从他们的农民贸易伙伴那里采用了语言。只有在偏远的安达曼群岛,与华南语系无关的语言仍然存在——这是数百种现已灭绝的东南亚原住民语言的最后语言幸存者。
即使是韩国和日本也深受中国影响,尽管它们与中国的地理隔离确保了它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自己的语言或身体和基因特征。韩国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从中国引入了水稻,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引入了青铜冶金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引入了文字。中国还将西亚的小麦和大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
在描述中国在东亚文明中的开创性作用时,我们不应夸大其词。并非东亚所有的文化进步都源于中国,也并非韩国人、日本人和热带东南亚人是毫无创造力的野蛮人,没有任何贡献。古代日本人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并在食物生产到来之前很久,就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定居在村庄中,依靠日本丰富的海产资源生存。一些作物可能首先或独立地在日本、韩国和热带东南亚被驯化。
但中国的作用仍然不成比例。例如,中国文化的声望价值在日本和韩国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日本尽管中国衍生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语方面存在缺陷,但从未想过要废弃它,而韩国现在才用其出色的本土谚文字母表取代笨拙的中国衍生文字。中国文字在日本和韩国的持续存在,是中国近一万年前植物和动物驯化的生动的20世纪遗产。由于东亚第一批农民的成就,中国变成了中国人,从泰国到(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复活节岛的人们成为了他们的表亲。
太平洋岛屿历史对我来说浓缩在一个事件中,当时我和三位印度尼西亚朋友走进查亚普拉(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的首都)的一家商店。我朋友们的名字是阿赫马德(Achmad)、威沃尔(Wiwor)和绍阿卡里(Sauakari),商店由一位名叫平华(Ping Wah)的商人经营。阿赫马德是一名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充当老板,因为他和我正在为政府组织一次生态调查,并雇用威沃尔和绍阿卡里作为当地助手。但阿赫马德以前从未去过新几内亚山地森林,不知道该买什么物资。结果很滑稽。
在我的朋友们进入商店的那一刻,平华正在读一份中文报纸。当他看到威沃尔和绍阿卡里时,他继续阅读,但一注意到阿赫马德,就立即把报纸藏到柜台下面。阿赫马德拿起一个斧头,引起威沃尔和绍阿卡里的笑声,因为他把它拿倒了。威沃尔和绍阿卡里向他展示了如何正确握住并测试它。然后阿赫马德和绍阿卡里看着威沃尔光着的脚,脚趾因一生不穿鞋而张得很开。绍阿卡里挑出最宽的鞋子,把它们贴在威沃尔的脚上,但鞋子仍然太窄,让阿赫马德、绍阿卡里和平华大笑起来。阿赫马德拿起一把塑料梳子来梳理他那笔直、粗糙的黑发。他瞥了一眼威沃尔那坚硬、紧密卷曲的头发,把梳子递给威沃尔。梳子立即卡在威沃尔的头发里,然后威沃尔一拉梳子就断了。每个人都笑了,包括威沃尔。威沃尔回应说,提醒阿赫马德应该买很多大米,因为在新几内亚山区村庄除了红薯没有食物可买,这会让阿赫马德胃不舒服——引发更多欢笑。
尽管笑声不断,我能感觉到潜在的紧张气氛。阿赫马德是爪哇人,平华是中国人,威沃尔是新几内亚高地人,绍阿卡里是来自北海岸的新几内亚低地人。爪哇人主导着印度尼西亚政府,该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吞并了西新几内亚,并使用炸弹和机关枪镇压新几内亚人的反抗。阿赫马德后来决定留在城里,让我独自与威沃尔和绍阿卡里进行森林调查。他通过指着自己笔直、粗糙的头发向我解释了他的决定,这与新几内亚人的头发非常不同,并说如果新几内亚人在远离军队支援的地方发现任何有像他这样头发的人,就会杀死他。
彭华收起了他的报纸,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进口中文印刷品在名义上是非法的。在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商人都是华人移民。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华人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爪哇人之间潜在的相互恐惧,在1966年一场血腥革命中爆发,当时爪哇人屠杀了数十万华人。作为新几内亚人,维沃和绍阿卡里与大多数新几内亚人一样对爪哇人的独裁统治充满怨恨,但他们也看不起彼此的群体。高地人嘲笑低地人是软弱的西米食用者,而低地人则嘲笑高地人是原始的大头族——这既指他们盘绕的厚重发型,也指他们傲慢的名声。在我与维沃和绍阿卡里建立一个孤立的森林营地后的几天内,他们就差点用斧头打起来。
艾哈迈德、维沃、绍阿卡里和彭华所代表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着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这些现代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当我们想到重大的海外人口迁移时,往往会关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的那些迁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时期内非欧洲人被欧洲人取代的情况。但在哥伦布之前很久,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海外迁移,以及史前时期非欧洲民族被其他非欧洲民族取代的情况。维沃、艾哈迈德和绍阿卡里代表了从亚洲大陆向太平洋海外迁移的三次史前浪潮。维沃的高地人可能是早期浪潮的后裔,他们在4万年前从亚洲殖民到新几内亚。艾哈迈德的祖先最终来自华南海岸,大约在4000年前抵达爪哇,在那里完成了对与维沃祖先相关的人群的取代。绍阿卡里的祖先大约在3600年前到达新几内亚,作为来自华南海岸的同一浪潮的一部分,而彭华的祖先仍然居住在中国。
将艾哈迈德和绍阿卡里的祖先分别带到爪哇和新几内亚的人口迁移,被称为南岛语系扩张(Austronesian expansion),是过去6000年来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它的一个分支成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在太平洋最偏远的岛屿上定居,是新石器时代民族中最伟大的航海家。今天,南岛语系语言作为母语在全球超过一半的范围内使用,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在这本关于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人类人口迁移的书中,南岛语系扩张占据中心位置,是需要解释的最重要现象之一。为什么最终源自中国大陆的南岛语系民族殖民了爪哇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并取代了那里的原住民,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殖民中国并取代中国人?在占领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之后,为什么南岛语系民族只能占领新几内亚低地的一个狭窄海岸带,为什么他们完全无法将维沃的人民从新几内亚高地赶走?华人移民的后裔是如何转变为波利尼西亚人的?
今天,爪哇、大多数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最东部的除外)和菲律宾的人口相当同质化。在外貌和基因上,这些岛屿的居民与华南人相似,甚至与热带东南亚人更相似,尤其是马来半岛的居民。他们的语言同样同质化:虽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部及中部有374种语言,但它们都密切相关,都属于南岛语系的同一亚语族(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南岛语系语言到达了亚洲大陆的马来半岛,以及越南和柬埔寨的小片区域,靠近印度尼西亚最西端的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岛,但在大陆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图17.1)。一些被英语借用的南岛语系词汇包括”taboo(禁忌)“和”tattoo(纹身)“(来自波利尼西亚语言)、”boondocks(偏远地区)“(来自菲律宾的他加禄语),以及”amok(发狂)“、”batik(蜡染)“和”orangutan(猩猩)“(来自马来语)。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基因和语言上的这种一致性,最初和中国在语言上的主导一致性一样令人惊讶。著名的爪哇直立人化石证明,人类至少在印度尼西亚西部居住了一百万年。这应该给人类足够的时间来进化出基因和语言多样性以及热带适应性,比如像许多其他热带民族那样的深色皮肤——但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却拥有浅色皮肤。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在除了浅肤色之外的其他身体特征以及基因方面,与热带东南亚人和华南人如此相似。看一眼地图就很明显,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人类在4万年前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唯一可能路线,所以人们可能天真地认为现代印度尼西亚人应该像现代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实际上,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只有少数类似新几内亚人的族群,特别是生活在菲律宾山区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s)。正如我在谈到热带东南亚时提到的三个类似新几内亚人的孑遗族群(第16章),菲律宾尼格利陀人可能是维沃尔人的祖先族群在到达新几内亚之前的孑遗。即使是这些尼格利陀人也说与菲律宾邻居相似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语言,这意味着他们也(像马来西亚的塞芒尼格利陀人和非洲的俾格米人一样)失去了他们的原始语言。
所有这些事实强烈表明,说南岛语系语言的热带东南亚人或华南人最近通过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散,取代了这些岛屿的所有原住民,除了菲律宾尼格利陀人之外,并取代了所有原始岛屿语言。这一事件显然发生得太近,殖民者还没有进化出深色皮肤、不同的语系或基因独特性或多样性。他们的语言当然比中国大陆的八种主流汉语数量更多,但并不更多样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许多相似语言的激增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岛屿从未经历过像中国那样的政治和文化统一。
语言分布的细节为这一假设的南岛语系扩张路线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整个南岛语系由959种语言组成,分为四个亚语系。但其中一个亚语系,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包括959种语言中的945种,覆盖了南岛语系几乎整个地理范围。在说印欧语系的欧洲人最近的海外扩张之前,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这表明马来-波利尼西亚亚语系最近从南岛语系分化出来,从南岛语系的发源地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产生了许多地方语言,所有这些语言仍然密切相关,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较大的语言差异。因此,对于南岛语系发源地的位置,我们不应该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而应该看其他三个南岛语系亚语系,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之间的差异远大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次亚语系之间的差异。
事实证明,其他三个亚语系的分布是重合的,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分布相比都很小。它们仅限于台湾岛的原住民,台湾岛距离中国大陆南部仅90英里。台湾原住民基本上独自拥有这个岛屿,直到最近一千年内中国大陆人开始大量定居。1945年后又有更多大陆人到来,特别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之后,因此原住民现在仅占台湾人口的2%。四个南岛语系亚语系中有三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在目前的南岛语系领域内,台湾是南岛语系语言使用时间最长的发源地,因此有最长的时间分化。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的所有其他南岛语系语言,都源于从台湾向外扩张的族群。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考古证据。虽然古代村落遗址的残骸不包括化石化的词语以及骨骼和陶器,但它确实揭示了可能与语言相关的人类和文化遗物的移动。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目前南岛语系领域的大部分地区——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最初是由缺乏陶器、磨制石器、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狩猎采集者占据的。(这一概括的唯一例外是马达加斯加、美拉尼西亚东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的偏远岛屿,这些岛屿从未被狩猎采集者到达,直到南岛语系扩张之前一直没有人类。)南岛语系领域内第一个不同事物的考古迹象来自——台湾。大约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开始,磨制石器和一种独特的装饰陶器风格(所谓的大坌坑陶器)出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南部的对岸海岸,这些陶器源自早期的华南大陆陶器。后期台湾遗址的稻米和小米遗存提供了农业的证据。
台湾和华南沿海的大坌坑遗址充满了鱼骨和软体动物壳,以及适合挖空木制独木舟的石制渔网坠子和石锛。显然,台湾的第一批新石器时代居民拥有足以进行深海捕鱼和跨越台湾海峡(将台湾岛与中国海岸分隔开)进行定期海上交通的水上交通工具。因此,台湾海峡可能作为训练场,中国大陆人在那里发展了开放水域的航海技能,使他们能够在太平洋扩张。
一种将台湾大坌坑文化与后来的太平洋岛屿文化联系起来的特定器物类型是树皮捣棒(bark beater),这是一种石器工具,用于将某些树种的纤维树皮捣碎制成绳索、网和衣物。一旦太平洋民族扩散到产羊毛的家养动物和纤维植物作物以及编织服装的范围之外,他们就变得依赖捣碎的树皮”布”来制作衣物。雷内尔岛是一个传统的波利尼西亚岛屿,直到1930年代才西化,岛上居民告诉我,西化带来了一个美妙的附带好处——岛屿变得安静了。不再有到处都是树皮捣棒的声音,从黎明到黄昏后每天都在捣制树皮布!
在大坌坑文化到达台湾后的大约一千年内,考古证据表明,明显源于它的文化从台湾向外扩散得越来越远,填满了现代南岛语系(Austronesian)的分布区域(图17.2)。这些证据包括磨制石器、陶器、家猪骨骼和农作物遗存。例如,台湾的装饰性大坌坑陶器被无装饰的素面或红陶取代,这种陶器也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和帝汶岛的遗址中被发现。这种包含陶器、石器和驯化动植物的文化”组合”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在菲律宾,大约公元前2500年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北婆罗洲和帝汶岛,大约公元前2000年出现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大约公元前1600年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在那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扩张呈现出快艇般的速度,文化组合的携带者向东迅速进入所罗门群岛以外此前无人居住的太平洋。扩张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公元1年后的一千年间,导致了每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岛屿的殖民。令人惊讶的是,它还向西横扫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导致了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
至少在扩张到达新几内亚海岸之前,岛屿之间的旅行可能是通过双舷外支架帆船独木舟(double-outrigger sailing canoes)进行的,这种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各地仍然很普遍。这种船只设计代表了对世界各地传统民族在内陆水道上普遍使用的简单独木舟的重大改进。独木舟正如其名:一根实心树干被”挖空”(即掏空),其两端用手斧成型。由于独木舟的底部像它所雕刻的树干一样是圆形的,重量分布的最轻微不平衡都会使独木舟向重量过大的一侧倾斜。每当我在新几内亚河流上被新几内亚人用独木舟划桨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恐惧之中:似乎我的每一个轻微动作都有可能使独木舟倾覆,把我和我的双筒望远镜倒出去与鳄鱼为伴。新几内亚人在平静的湖泊和河流上划独木舟时看起来很安全,但即使是新几内亚人也不能在有中等波浪的海上使用独木舟。因此,某种稳定装置不仅对于南岛语系通过印度尼西亚的扩张至关重要,甚至对于台湾的最初殖民也是必不可少的。
解决方案是将两根较小的圆木(“舷外支架”)平行于船体并距其几英尺处绑扎,一边一根,通过垂直于船体和舷外支架绑扎的杆子连接到船体上。每当船体开始向一侧倾斜时,那一侧舷外支架的浮力就会阻止舷外支架被推入水下,从而使船只几乎不可能倾覆。双舷外支架帆船独木舟的发明可能是触发南岛语系从中国大陆扩张的技术突破。
考古证据和语言学证据之间的两个显著巧合支持了这样的推论:数千年前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带到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人们说南岛语,并且是今天仍然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南岛语使用者的祖先。首先,两种类型的证据都明确指向台湾的殖民是从华南海岸扩张的第一阶段,而从台湾殖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下一阶段。如果扩张是从热带东南亚的马来半岛进行到最近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然后到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最后到菲律宾和台湾,我们会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现代语言中发现南岛语系最深的分支(反映最大的时间深度),而台湾和菲律宾的语言只是在一个单一的亚语族内最近才分化的。相反,最深的分支在台湾,而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语言归入同一个亚-亚语族:西部马来-波利尼西亚亚-亚语族的一个近期分支,而这又是马来-波利尼西亚亚语族的一个相当近期的分支。这些语言关系的细节与考古证据完全吻合,即马来半岛的殖民是近期的,并且是在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殖民之后而非之前发生的。
考古学证据与语言学证据之间的另一个巧合涉及古代南岛语族使用的文化物品。考古学以陶器、猪骨和鱼骨等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的直接证据。人们最初可能会疑惑,一个语言学家仅研究现代语言,而这些语言的未书写祖先形式仍然未知,他如何能够弄清楚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南岛语族是否有猪。解决方法是通过比较从原始语言衍生出的现代语言的词汇,来重建已消失的古代语言(所谓的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s))的词汇表。
例如,在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许多语言中,“羊”这个词的意思非常相似,这些语言分布从爱尔兰到印度:“avis”、“avis”、“ovis”、“oveja”、“ovtsa”、“owis”和”oi”分别在立陶宛语、梵语、拉丁语、西班牙语、俄语、希腊语和爱尔兰语中使用。(英语的”sheep”显然来自不同的词根,但英语在”ewe”一词中保留了原始词根。)对各种现代印欧语言在其历史中经历的语音变化的比较表明,原始形式是大约6000年前使用的祖先印欧语言中的”owis”。这种未书写的祖先语言被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显然,6000年前的原始印欧人有羊,这与考古学证据一致。他们词汇表中的近2000个其他词汇同样可以被重建,包括”山羊”、“马”、“轮子”、“兄弟”和”眼睛”等词汇。但没有原始印欧语词汇可以重建为”枪”,它在不同的现代印欧语言中使用不同的词根:英语中的”gun”、法语中的”fusil”、俄语中的”ruzhyo”等等。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6000年前的人们不可能有”枪”这个词,因为枪只在过去1000年内才被发明。由于因此没有继承的共享词根表示”枪”,当枪最终被发明时,每种印欧语言都必须发明或借用自己的词。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我们可以比较现代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语言,来重建在遥远过去使用的原始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不出所料,重建的原始南岛语有”二”、“鸟”、“耳朵”和”头虱”等含义的词:当然,原始南岛人可以数到2,知道鸟类,有耳朵和虱子。更有趣的是,重建的语言有”猪”、“狗”和”稻米”的词汇,因此这些必定是原始南岛文化的一部分。重建的语言充满了表示海洋经济的词汇,如”外伸支架独木舟”、“帆”、“巨蛤”、“章鱼”、“鱼笼”和”海龟”。关于原始南岛人文化的这一语言学证据,无论他们何时何地生活,都与考古学证据很好地吻合,即大约6000年前生活在台湾的制陶、以海洋为导向的粮食生产者。
同样的程序可以用于重建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Proto-Malayo-Polynesian),即南岛人从台湾移民后使用的祖先语言。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包含许多热带作物的词汇,如芋头、面包果、香蕉、山药和椰子,这些词在原始南岛语中无法重建。因此,语言学证据表明,许多热带作物是在从台湾移民后才添加到南岛人的目录中的。这一结论与考古学证据一致:随着殖民农民从台湾(位于赤道以北约23度)向赤道热带地区向南扩散,他们越来越依赖热带块根和树木作物,然后他们继续将这些作物带到热带太平洋地区。
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经由台湾的说南岛语的农民如何能够如此彻底地取代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原始狩猎采集者人口,以至于原始人口几乎没有遗传学证据,也没有语言学证据幸存下来?原因类似于欧洲人在过去两个世纪内取代或灭绝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原因,以及早期中国南方人取代原始热带东南亚人的原因:农民的人口密度要大得多,拥有更优越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上交通工具和海事技能,以及农民具有一定抵抗力但狩猎采集者没有的流行病。在亚洲大陆上,说南岛语的农民同样能够取代马来半岛的一些前狩猎采集者,因为南岛人大约在说南亚语(Austroasiatic)的农民从北方(从泰国)殖民该半岛的同时,从南部和东部(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岛)殖民了该半岛。其他南岛人设法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占族(Chamic)少数民族的祖先。
然而,南岛语族农民无法进一步扩散到东南亚大陆,因为南亚语和泰-卡岱语(Tai-Kadai)农民已经取代了那里的前狩猎采集者,而且南岛语族农民相对于南亚语和泰-卡岱语农民没有优势。尽管我们推断南岛语使用者起源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但今天在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都不使用南岛语,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是被汉藏语系(Sino-Tibetan)使用者向南扩张所消灭的数百种前中国语言之一。但被认为与南岛语最接近的语系是泰-卡岱语、南亚语和苗瑶语(Miao-Yao)。因此,虽然中国的南岛语可能没有在中国王朝的冲击中幸存下来,但它们的一些姊妹语言和表亲语言却幸存了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追随南岛语族扩张的初期阶段,从中国南方海岸出发,经过台湾和菲律宾,到达印度尼西亚西部和中部,行程达2,500英里。在这次扩张过程中,南岛语族占据了这些岛屿上所有可居住的地区,从海岸到内陆,从低地到山区。到公元前1500年,他们熟悉的考古标志物,包括猪骨和素面红陶,表明他们已经到达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哈马黑拉岛,距离新几内亚这个多山大岛的西端不到200英里。他们是否继续征服了那座岛屿,就像他们已经征服了西里伯斯、婆罗洲、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些多山大岛一样?
他们没有,只要看一眼大多数现代新几内亚人的面孔就很明显,对新几内亚人基因的详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朋友维沃和所有其他新几内亚高地人在深色皮肤、紧密卷曲的头发和面部特征上,明显不同于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中国南方人。新几内亚内陆和南部海岸的大多数低地居民与高地人相似,只是他们往往更高。遗传学家未能在新几内亚高地人的血液样本中找到南岛语族特征性的基因标记。
但新几内亚北部和东部海岸,以及新几内亚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人民,呈现出更复杂的情况。在外观上,他们介于像维沃这样的高地人和像阿赫迈德这样的印度尼西亚人之间,尽管平均而言更接近维沃。例如,我来自北海岸的朋友萨乌卡里的头发是波浪状的,介于阿赫迈德的直发和维沃的卷发之间,皮肤比维沃的稍浅,但比阿赫迈德的深得多。从基因上看,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居民以及新几内亚北海岸居民约15%是南岛语族,85%像新几内亚高地人。因此,南岛语族显然到达了新几内亚地区,但完全未能深入该岛内部,并在北海岸和岛屿上被新几内亚原有居民在基因上稀释了。
现代语言基本上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增加了细节。在第15章中,我解释过,大多数新几内亚语言被称为巴布亚语,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语系都无关。无一例外,新几内亚山区、整个西南部和中南部低地新几内亚(包括海岸)以及新几内亚北部内陆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巴布亚语。但南岛语族语言仅在北部和东南部海岸的狭长地带使用。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大多数语言是南岛语族语言:巴布亚语只在少数岛屿的孤立地区使用。
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海岸使用的南岛语族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子亚语族,称为大洋洲语族(Oceanic),与哈马黑拉岛和新几内亚西端使用的子亚语族有关。这种语言关系证实了,正如人们从地图上所预期的那样,新几内亚地区的南岛语族使用者是经由哈马黑拉岛到达的。新几内亚北部南岛语族和巴布亚语言及其分布的细节,证明了南岛语族入侵者与说巴布亚语的居民之间的长期接触。该地区的南岛语族语言和巴布亚语言都显示出彼此词汇和语法的大量影响,使得很难判断某些语言基本上是受巴布亚语言影响的南岛语族语言还是相反。当人们沿着北海岸或其边缘岛屿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旅行时,会从一个说南岛语族语言的村庄来到一个说巴布亚语的村庄,然后又到另一个说南岛语族语言的村庄,在语言边界处没有任何基因上的不连续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南岛语族入侵者的后裔和新几内亚原住民在新几内亚北海岸及其岛屿上进行贸易、通婚,并相互获取对方的基因和语言已有数千年。这种长期接触更有效地传播了南岛语族语言而非南岛语族基因,结果是,大多数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居民现在说南岛语族语言,尽管他们的外貌和大部分基因仍然是巴布亚人的。但南岛语族的基因和语言都没有渗透到新几内亚内陆。因此,他们入侵新几内亚的结果与入侵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大岛的结果大不相同,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压路机(steamroller)几乎消除了以前居民基因和语言的所有痕迹。为了理解新几内亚发生了什么,现在让我们转向考古学证据。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几乎与他们在哈马黑拉岛出现的同时,南岛语族扩张的熟悉考古标志物——猪、鸡、狗、红陶和磨制石器以及巨蛤贝壳制成的锛——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但有两个特征将南岛语族在那里的到来与他们早期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到来区分开来。
第一个特征是陶器设计,这是一种没有经济意义的美学特征,但它确实让考古学家能够立即识别出早期南岛语系遗址。虽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早期南岛语系陶器都没有装饰,但新几内亚地区的陶器却用排列成水平带状的几何图案精美装饰。在其他方面,这些陶器保留了印度尼西亚早期南岛语系陶器特有的红色陶衣和器型。显然,新几内亚地区的南岛语系定居者萌生了给他们的陶罐”纹身”的想法,也许是受到了他们已经在树皮布和身体纹身上使用的几何图案的启发。这种风格被称为拉皮塔陶器(Lapita pottery),源自一个名为拉皮塔的考古遗址,该风格在那里被描述。
早期南岛语系在新几内亚地区遗址更为重要的区别特征是它们的分布。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相反,即使是已知最早的南岛语系遗址也位于吕宋岛、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等大岛上,而新几内亚地区带有拉皮塔陶器的遗址实际上仅限于偏远较大岛屿周边的小岛。迄今为止,拉皮塔陶器仅在新几内亚北海岸的一个遗址(艾塔佩)和所罗门群岛的几个遗址中被发现。新几内亚地区的大多数拉皮塔遗址位于俾斯麦群岛,在较大的俾斯麦岛屿沿海的小岛上,偶尔在较大岛屿本身的海岸上。由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拉皮塔陶器的制造者能够航行数千英里,他们未能将村庄转移到几英里外的俾斯麦大岛,或几十英里外的新几内亚,肯定不是因为无法到达那里。
拉皮塔人的生计基础可以从考古学家在拉皮塔遗址挖掘的垃圾中重建。拉皮塔人严重依赖海鲜,包括鱼、海豚、海龟、鲨鱼和贝类。他们有猪、鸡和狗,并食用许多树木的坚果(包括椰子)。虽然他们可能也食用通常的南岛语系块根作物,如芋头和山药,但这些作物的证据很难获得,因为坚硬的坚果壳比柔软的块根更有可能在垃圾堆中保存数千年。
自然地,不可能直接证明制作拉皮塔陶罐的人说南岛语。然而,两个事实使这一推断几乎确定无疑。首先,除了陶罐上的装饰外,陶罐本身及其相关的文化器物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相似,这些遗址是现代南岛语系社会的祖先。其次,拉皮塔陶器也出现在以前没有人类居住的遥远太平洋岛屿上,没有证据表明在带来拉皮塔陶罐的定居之后有重大的第二波定居浪潮,而那里的现代居民说南岛语(下文将详述)。因此,可以安全地假设拉皮塔陶器标志着南岛语系人抵达新几内亚地区。
那些南岛语系制陶者在邻近较大岛屿的小岛上做什么?他们可能以与新几内亚地区小岛上的现代制陶者直到最近仍然生活的方式相同的方式生活。1972年,我访问了位于西亚西岛群中马来小岛上的这样一个村庄,它位于中等大小的翁博伊岛附近,翁博伊岛又在较大的俾斯麦岛新不列颠岛附近。当我上岸到马来岛寻找鸟类时,对那里的人一无所知,迎接我的景象让我感到惊讶。这里不是通常的低矮小屋组成的小村庄,周围环绕着足以养活村庄的大片菜园,海滩上停着几艘独木舟,而是马来岛的大部分区域被一排排双层木屋并排占据,没有可用于菜园的土地——相当于新几内亚的曼哈顿市中心。海滩上排列着一排排大独木舟。事实证明,马来岛民除了是渔民外,还是专门的陶工、雕刻师和商人,他们以制作装饰精美的陶罐和木碗为生,用独木舟将它们运送到较大的岛屿,用他们的商品交换猪、狗、蔬菜和其他必需品。就连马来岛独木舟的木材也是通过与附近翁博伊岛上的村民交易获得的,因为马来岛没有大到足以制作独木舟的树木。
在欧洲航运出现之前,新几内亚地区岛屿之间的贸易被这些专门的独木舟制造陶工群体垄断,他们擅长在没有导航仪器的情况下航行,生活在近海小岛上或偶尔在大陆沿海村庄。到1972年我到达马来岛时,这些本土贸易网络已经崩溃或萎缩,部分原因是来自欧洲机动船和铝锅的竞争,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一些商人溺水的事故后禁止长距离独木舟航行。我猜测拉皮塔陶工是公元前1600年后几个世纪新几内亚地区的岛际商人。
南岛语系向新几内亚北海岸本身的传播,以及向更大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传播,主要发生在拉皮塔时期之后,因为拉皮塔遗址本身集中在俾斯麦小岛上。直到公元1年左右,源自拉皮塔风格的陶器才出现在新几内亚东南半岛的南侧。当欧洲人在19世纪末开始探索新几内亚时,新几内亚南海岸的其余所有地区仍然只有巴布亚语系的人口居住,尽管说南岛语的人群不仅已经在东南半岛定居,而且还在阿鲁群岛和凯伊群岛(距离新几内亚西部南海岸70-80英里)定居。因此,南岛人有数千年的时间可以从附近的基地殖民新几内亚的内陆和南海岸,但他们从未这样做过。即使是他们对北新几内亚海岸边缘的殖民化,在语言上的意义也大于遗传学上的意义:所有北部海岸人民的基因仍然主要是新几内亚人。最多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了南岛语言,可能是为了与连接各个社会的长途贸易者交流。
因此,南岛扩张在新几内亚地区的结果与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结果相反。在后一个地区,土著人口消失了——据推测是被入侵者驱赶、杀害、感染或同化了。在前一个地区,土著人口主要将入侵者拒之门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入侵者(南岛人)是相同的,而且如果被南岛人取代的原始印度尼西亚人口确实与新几内亚人有关(正如我之前所建议的),那么土著人口在基因上也可能彼此相似。为什么会有相反的结果?
当人们考虑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土著人口的不同文化环境时,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稀疏地居住着缺乏磨制石器的狩猎采集者。相比之下,粮食生产已经在新几内亚高地建立了数千年,并且可能也在新几内亚低地以及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建立了。新几内亚高地支撑着现代世界上石器时代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些地区。
南岛人在与那些已建立的新几内亚人口竞争时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南岛人赖以生存的一些作物,如芋头、山药和香蕉,可能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了。新几内亚人很容易将南岛人的鸡、狗,尤其是猪融入他们的粮食生产经济中。新几内亚人已经拥有磨制石器。他们对热带疾病的抵抗力至少与南岛人一样强,因为他们携带与南岛人相同的五种针对疟疾的遗传保护,而其中一些或全部基因是在新几内亚独立进化的。新几内亚人已经是熟练的航海者,尽管不如拉皮塔陶器的制造者那样熟练。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数万年前,新几内亚人就已经殖民了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而黑曜石(一种适合制作锋利工具的火山岩)的贸易在南岛人到来之前至少18000年就已经在俾斯麦群岛繁荣起来。新几内亚人似乎甚至最近还向西扩张,对抗南岛人的浪潮,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那里北哈马黑拉岛和帝汶岛上使用的语言是典型的巴布亚语言,与新几内亚西部的一些语言有关。
简而言之,南岛扩张的不同结果显著地说明了粮食生产在人类人口迁移中的作用。南岛粮食生产者迁移到两个可能彼此有关的土著居民占据的地区(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者,而新几内亚的居民已经是粮食生产者,并且已经发展出粮食生产的许多伴随物(密集的人口、疾病抵抗力、更先进的技术等等)。结果,虽然南岛扩张席卷了原始印度尼西亚人,但在新几内亚地区却未能取得多大进展,正如它在热带东南亚也未能对抗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和壮侗语系(Tai-Kadai)粮食生产者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追溯了南岛语族通过印度尼西亚的扩张,直到新几内亚和热带东南亚的海岸。在第19章中,我们将追溯其跨越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加的过程,而在第15章中我们看到生态困难阻止了南岛语族在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建立定居点。这次扩张的最后一个推进始于拉皮塔陶工远航向东进入太平洋,越过所罗门群岛,进入一个以前没有其他人类到达过的岛屿领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拉皮塔陶片、熟悉的猪、鸡和狗三件套,以及南岛语族的其他常见考古标志出现在斐济、萨摩亚和汤加等太平洋群岛上,这些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以东一千多英里处。在基督教时代早期,这些标志中的大部分(显著的例外是陶器)出现在东波利尼西亚的岛屿上,包括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进一步的长距离独木舟航行将定居者带到北部的夏威夷,东部的皮特凯恩岛和复活节岛,以及西南部的新西兰。这些岛屿今天的大多数原住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因此他们是拉皮塔陶工的直系后裔。他们说的南岛语系语言与新几内亚地区的语言密切相关,他们的主要作物是南岛语族的农作物包,包括芋头、山药、香蕉、椰子和面包果。
随着公元1400年左右对新西兰附近的查塔姆群岛的占领——这仅仅比欧洲”探险家”进入太平洋早一个世纪——亚洲人最终完成了探索太平洋的任务。他们持续了数万年的探索传统始于威沃尔的祖先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传播。它只有在耗尽了目标,几乎每个适合居住的太平洋岛屿都被占领后才结束。
对任何对世界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的人类社会都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环境如何塑造历史的例子。根据他们的地理家园,东亚和太平洋人民在获取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方面存在差异。一次又一次,能够获得粮食生产先决条件以及有利于从其他地方传播技术的地理位置的人们,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当一波殖民者扩散到不同的环境中时,他们的后代根据这些环境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发展。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华南地区发展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和技术,从华北地区接受了文字以及更多的技术和政治结构,并继续殖民热带东南亚和台湾,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在东南亚内部,在这些粮食生产的华南殖民者的后裔或亲属中,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山区雨林中的云比人(Yumbri)重新过上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而云比人的近亲越南人(说的语言与云比语属于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的同一个亚语族)仍然是红河三角洲的粮食生产者,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以金属为基础的帝国。同样,在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南岛语系移民农民中,婆罗洲雨林中的普南人(Punan)被迫转回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生活在爪哇肥沃火山土壤上的亲属仍然是粮食生产者,在印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王国,采用了文字,并在婆罗浮屠建造了伟大的佛教纪念碑。继续殖民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与东亚的冶金术和文字隔绝,因此没有文字或金属。然而,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经济在不同环境中经历了巨大的多样化。在一千年内,东波利尼西亚殖民者在查塔姆群岛重新过上了狩猎采集的生活,同时在夏威夷建立了一个具有集约化粮食生产的原国家(protostate)。
当欧洲人最终到达时,他们在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在热带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临时的殖民统治。然而,本土病菌和粮食生产者阻止了欧洲人大量定居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只有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最大和最偏远的岛屿,离赤道最远,因此处于最接近温带(类似欧洲)的气候——现在支撑着大量的欧洲人口。因此,与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东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仍然由东亚和太平洋人民占据。
过去13000年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替代,源于旧世界与新世界社会的近期碰撞。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其最戏剧性和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皮萨罗率领的一小支西班牙军队俘获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之时。阿塔瓦尔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在行政和技术上最先进的美洲原住民国家的绝对统治者。阿塔瓦尔帕的被俘象征着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因为导致这一事件的近因组合,也同样导致了欧洲对其他美洲原住民社会的征服。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次半球碰撞,应用自第三章以来我们所学到的知识。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并征服了美洲原住民的土地,而不是相反?我们的起点将是对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欧亚大陆和美洲原住民社会的比较。
我们的比较从食物生产开始,这是当地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征服背后的终极因素。美洲和欧亚大陆食物生产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涉及大型驯化哺乳动物物种。在第九章中,我们遇到了欧亚大陆的13个物种,它们成为了动物蛋白(肉类和奶制品)、羊毛和兽皮的主要来源,人员和货物陆路运输的主要方式,不可或缺的战争工具,以及(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生产的重要促进因素。在中世纪水车和风车开始取代欧亚大陆哺乳动物之前,它们也是超越人类肌肉力量的”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例如,用于转动磨石和操作提水装置。相比之下,美洲只有一种大型驯化哺乳动物,即羊驼/羊驼,仅限于安第斯山脉的小部分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海岸。虽然它被用于肉类、羊毛、兽皮和货物运输,但它从未产出供人类消费的奶制品,从未载过骑手,从未拉过车或犁,也从未作为动力来源或战争工具。
这是欧亚大陆和美洲原住民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原有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物种的灭绝(灭绝?)。如果不是这些物种灭绝,现代历史可能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当科尔特斯和他疲惫不堪的冒险者于1519年登陆墨西哥海岸时,他们可能会被数千名骑着驯化的美洲本土马匹的阿兹特克骑兵赶入大海。阿兹特克人可能不会死于天花,西班牙人反而可能被具有疾病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传播的美洲病菌消灭。依靠动物力量的美洲文明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性的结果在数千年前就因哺乳动物灭绝而被排除了。
这些灭绝使得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多得多的可驯化野生候选动物。大多数候选动物因半打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而自我排除,不适合被驯化。因此,欧亚大陆最终拥有13种大型驯化哺乳动物,而美洲只有一种非常局部的物种。两个半球也都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火鸡、豚鼠和疣鼻鸭在美洲非常局部地分布,狗在美洲分布更广;鸡、鹅、鸭、猫、狗、兔子、蜜蜂、蚕和其他一些物种在欧亚大陆。但所有这些小型驯化动物物种的重要性与大型动物相比都微不足道。
欧亚大陆和美洲在植物食物生产方面也存在差异,尽管这里的差距不如动物食物生产那么明显。1492年,农业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少数既没有作物也没有驯化动物的欧亚狩猎采集者包括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没有驯鹿的西伯利亚社会,以及散布在印度和热带东南亚森林中并与邻近农民进行贸易的小型狩猎采集群体。其他一些欧亚社会,特别是中亚牧民和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拉普人和萨摩耶德人,有驯化动物但很少或没有农业。几乎所有其他欧亚社会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农业在美洲也很普遍,但狩猎采集者占据的美洲面积比例大于欧亚大陆。美洲那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地区包括北美洲北部和南美洲南部的全部、加拿大大平原,以及北美洲西部的全部地区,除了美国西南部支持灌溉农业的小部分地区。令人震惊的是,没有粮食生产的美洲原住民地区,在今天欧洲人到来之后,包括了北美洲和南美洲一些最高产的农田和牧场:美国太平洋沿岸诸州、加拿大小麦带、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智利地中海地区。这些土地以前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乏可驯化的野生动物和植物,以及地理和生态障碍阻止了美洲其他地区的作物和少数家养动物物种到达。这些土地不仅对欧洲定居者,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对美洲原住民来说,一旦欧洲人引入合适的家养动物和作物,就变得富有生产力。例如,美洲原住民社会以其对马匹的精通而闻名,在某些情况下还精通养牛和牧羊,这发生在大平原、美国西部和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部分地区。那些骑马的平原战士和纳瓦霍牧羊人和织工现在在美国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印象中占据突出地位,但这种印象的基础只是在1492年之后才形成的。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大片地区维持粮食生产所缺少的唯一要素就是家养动物和作物本身。
在那些确实支持美洲原住民农业的美洲地区,与欧亚农业相比,它受到五个主要劣势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贫乏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多样化和富含蛋白质的谷物;手工种植单个种子,而不是撒播;用手耕作而不是用动物犁地,后者使一个人能够耕种更大的面积,也允许耕种一些肥沃但坚硬的土壤和草皮,这些土壤很难用手耕作(例如北美大平原的土壤);缺乏动物粪肥来提高土壤肥力;以及仅仅依靠人力,而不是动物力量,来完成农业任务,如脱粒、研磨和灌溉。这些差异表明,截至1492年,欧亚农业平均每人每小时劳动可能比美洲原住民农业产生更多的卡路里和蛋白质。
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社会和美洲原住民社会之间差异的主要根本原因。在征服背后的直接因素中,最重要的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差异最直接相关的是病菌。定期侵袭拥挤的欧亚社会的传染病,许多欧亚人因此发展出免疫或遗传抗性,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杀手: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结核病、斑疹伤寒、霍乱、疟疾等。与这份严峻的清单相比,可以确定归因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美洲原住民社会的唯一人群传染病是非梅毒性密螺旋体病。(正如我在第11章中解释的那样,梅毒是起源于欧亚大陆还是美洲仍不确定,而且在我看来,声称人类结核病在哥伦布之前就存在于美洲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有害病菌方面的这种大陆差异矛盾地源于有用家畜方面的差异。大多数导致拥挤人类社会传染病的微生物是从非常相似的祖先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这些祖先微生物导致家养动物的传染病,粮食生产者大约在10000年前开始与这些动物每天密切接触。欧亚大陆拥有许多家养动物物种,因此发展出许多这样的微生物,而美洲这两者都很少。美洲原住民社会进化出如此少的致命微生物的其他原因是,为流行病提供理想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比欧亚大陆晚数千年;而且支持城市社会的新大陆三个地区(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从未通过快速、大容量的贸易连接起来,这种贸易规模曾将鼠疫、流感和可能的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因此,即使是疟疾和黄热病,这些最终成为欧洲殖民美洲热带地区主要障碍,并对巴拿马运河建设构成最大障碍的传染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疾病,而是由旧大陆热带起源的微生物引起的,由欧洲人引入美洲。
与病菌相当,作为欧洲征服美洲背后的直接因素的是技术各个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源于欧亚大陆依赖粮食生产的人口密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化、相互作用和竞争社会的历史要长得多。可以挑出五个技术领域:
首先,在1492年时,所有复杂的欧亚社会都使用金属——最初是铜,然后是青铜,最后是铁——来制作工具。相比之下,尽管铜、银、金和合金在安第斯地区和美洲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装饰品,但石头、木材和骨头仍然是所有美洲原住民社会工具的主要材料,他们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使用铜制工具。
其次,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远比美洲强大。欧洲的武器是钢剑、长矛和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大炮,而盔甲和头盔也是由实心钢或锁子甲制成。美洲原住民没有钢,而是使用石头或木头(偶尔在安第斯地区使用铜)制成的棍棒和斧头、投石器、弓箭和棉甲,这些提供的保护和武器效果要差得多。此外,美洲原住民军队没有动物可以对抗马匹,马匹在冲锋和快速运输方面的价值给欧洲人带来了压倒性优势,直到一些美洲原住民社会自己也采用了马匹。
第三,欧亚社会在操作机器的动力来源方面享有巨大优势。最早超越人力的进步是使用牛、马和驴等动物来拉犁、转动轮子以碾磨谷物、提水、灌溉或排水。水车出现于罗马时代,然后在中世纪与潮汐磨坊和风车一起大量增加。通过齿轮系统,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引擎不仅用于碾磨谷物和输送水,还用于无数的制造目的,包括压榨糖、驱动鼓风炉风箱、研磨矿石、造纸、抛光石材、榨油、制盐、生产纺织品和锯木。通常将工业革命的开端定义为18世纪英国对蒸汽动力的利用,但事实上,基于水力和风力的工业革命早已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地方开始。截至1492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应用动物力、水力和风力的操作,在美洲仍然是由人力完成的。
早在车轮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它就已经成为大多数欧亚陆地运输的基础——不仅用于畜力车辆,还用于人力手推车,这使得一个或多个人仍然只使用人力就能运输比其他方式多得多的重量。车轮也被用于欧亚的制陶和钟表制造。这些车轮的用途在美洲都没有被采用,车轮在美洲只出现在墨西哥的陶瓷玩具中。
还要提到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社会发展出大型帆船,其中一些能够逆风航行和横渡海洋,配备有六分仪、磁罗盘、船尾舵和大炮。在载重量、速度、机动性和适航性方面,这些欧亚船只远远优于在新大陆最先进的社会——安第斯和中美洲社会之间进行贸易的木筏。这些木筏沿着太平洋海岸顺风航行。皮萨罗的船在他第一次向秘鲁航行时轻松追上并俘获了这样一艘木筏。
除了病菌和技术之外,欧亚社会和美洲原住民社会在政治组织上也有所不同。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有组织的国家统治之下。其中,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中国的国家,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13世纪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最初都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大型多语言联合体。因此,它们通常被称为帝国。许多欧亚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宗教,这些宗教有助于国家凝聚力,被用来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并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和群体社会主要局限于北极驯鹿牧民、西伯利亚狩猎采集者,以及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的狩猎采集飞地。
美洲有两个帝国,即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规模、人口、多语言构成、官方宗教以及通过征服较小国家而起源等方面都与欧亚的帝国相似。在美洲,这是仅有的两个能够像许多欧亚国家那样动员资源进行公共工程或战争的政治单位,而七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在1492年至1666年间拥有获取美洲殖民地的资源。美洲还有许多酋邦(其中一些实际上是小国家),分布在热带南美洲、阿兹特克统治之外的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美洲其余地区仅以部落或群体层级组织。
最后要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国家都有识字的官僚机构,在某些国家中,除官僚之外的相当一部分民众也识字。文字通过促进政治管理和经济交流、激励和引导探索与征服,以及提供延伸到遥远地方和时代的各种信息和人类经验,赋予了欧洲社会力量。相比之下,美洲的文字使用仅限于中美洲小范围地区的精英阶层。印加帝国采用了一种基于绳结的记账系统和记忆辅助工具(称为结绳quipu),但它无法像文字那样传递详细信息。
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相比美洲原住民社会享有巨大优势。这些是影响后哥伦布时代碰撞结果的主要因素。但公元1492年的这些差异只是历史轨迹的一个快照,这些轨迹在美洲至少延续了13000年,在欧亚大陆则延续了更长时间。特别是对于美洲来说,1492年的快照捕捉到的是美洲原住民独立轨迹的终点。现在让我们追溯这些轨迹的早期阶段。
表18.1总结了各半球主要”故乡”(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以及中美洲)关键发展出现的大致日期。它还包括了美国东部这个新世界次要故乡的轨迹,以及英格兰的轨迹——英格兰根本不是故乡,列出它是为了说明发展从新月沃地传播的速度有多快。
这个表格肯定会让任何有学识的学者感到震惊,因为它将极其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几个看似精确的日期。实际上,所有这些日期只是试图标记连续体上的任意点。例如,比某位考古学家发现的第一件金属工具的日期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工具由金属制成的时间,但金属工具必须多普遍才能被评为”广泛”?同一发展在同一故乡的不同地区出现的日期可能不同。例如,在安第斯地区,陶器在厄瓜多尔海岸(公元前3100年)出现的时间比在秘鲁(公元前1800年)早约1300年。有些日期,如酋邦兴起的日期,比陶器或金属工具等人工制品的日期更难从考古记录中推断。表18.1中的一些日期非常不确定,特别是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日期。然而,只要理解这个表格是一种简化,它对于比较各大陆历史还是很有用的。
该表显示,粮食生产开始在人类饮食中占据很大比例的时间,在欧亚故乡比美洲故乡早约5000年。必须立即提到一个警告:虽然欧亚大陆粮食生产的古老性毋庸置疑,但美洲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存在争议。特别是,考古学家经常引用墨西哥科克斯卡特兰洞穴、秘鲁吉塔雷罗洞穴和其他一些美洲遗址的驯化植物的更早日期,比表中给出的日期要早得多。这些说法现在正在被重新评估,原因有几个:最近对作物遗存本身的直接放射性碳定年在某些情况下得出了更晚的日期;先前报告的较早日期是基于被认为与植物遗存同时代的木炭,但可能并非如此;一些较早植物遗存作为作物还是仅作为采集的野生植物的地位不确定。尽管如此,即使美洲的植物驯化确实比表18.1所示日期开始得更早,农业肯定也是在比欧亚故乡晚得多的时候才成为美洲故乡大多数人类热量摄入和定居生活的基础。
| 采用的大致日期 | 新月沃地 | 中国 | 英格兰 |
|---|---|---|---|
| 植物驯化 | 公元前8500年 | 公元前7500年之前 | 公元前3500年 |
| 动物驯化 | 公元前8000年 | 公元前7500年之前 | 公元前3500年 |
| 陶器 | 公元前7000年 | 公元前7500年之前 | 公元前3500年 |
| 村落 | 公元前9000年 | 公元前7500年之前 | 公元前3000年 |
| 酋邦 | 公元前5500年 | 公元前4000年 | 公元前2500年 |
| 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或人工制品(铜和/或青铜) | 公元前4000年 | 公元前2000年 | 公元前2000年 |
| 国家 | 公元前3700年 | 公元前2000年 | 公元500年 |
此表给出了三个欧亚地区和四个美洲原住民地区广泛采用重大发展的大致日期。动物驯化的日期忽略了狗,因为狗的驯化早于欧亚大陆和美洲的食物生产性动物。酋邦(chiefdoms)是从考古证据中推断出来的,如分级墓葬、建筑和定居模式。该表大大简化了复杂的历史事实:许多重要的注意事项请参见正文。
正如我们在第5章和第10章中看到的,每个半球只有少数相对较小的区域作为”家园”,粮食生产首先在那里出现,然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这些家园是欧亚大陆的肥沃月牙地带(Fertile Crescent)和中国,以及美洲的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部。关键发展的传播速度在欧洲尤其清楚,这要归功于在那里工作的众多考古学家。如表18.1总结的英格兰情况,一旦粮食生产和村庄生活在经过长时间的滞后(5000年)后从肥沃月牙地带传来,英格兰随后采用酋邦、国家、书写,特别是金属工具的滞后时间要短得多:铜器和青铜器首次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滞后2000年,而广泛使用铁器工具仅滞后250年。显然,对于一个已经定居的农耕社会来说,从另一个这样的社会”借用”冶金术,要比游牧的狩猎采集者从定居农民那里”借用”粮食生产(或被农民取代)容易得多。
四组原因表明:较晚的开端、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更有限、更大的传播障碍,以及可能在美洲比在欧亚大陆有更小或更孤立的人口密集区域。
至于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人类占据欧亚大陆已有大约一百万年,远远长于他们在美洲生活的时间。根据第1章讨论的考古证据,人类仅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从阿拉斯加进入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前几个世纪作为克洛维斯猎人向南扩散到加拿大冰盖以南,并在公元前10000年到达南美洲最南端。即使有争议的美洲更早人类居住地点的说法被证明有效,那些假定的克洛维斯前居民由于未知原因仍然分布非常稀疏,并没有像旧世界那样启动更新世狩猎采集社会的激增,伴随着人口、技术和艺术的扩张。粮食生产已经在肥沃月牙地带开始出现,仅在克洛维斯衍生的狩猎采集者刚刚到达南美洲南部之后1500年。
这种欧亚大陆领先优势可能产生的几个后果值得考虑。首先,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之后是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人类填满?当我们计算可能涉及的数字时,会发现这种影响对美洲在食物生产村落方面落后5000年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一章给出的计算告诉我们,即使只有100名开拓性的美洲原住民越过加拿大边境进入美国本土,并且每年仅以1%的速度增长,他们也会在1000年内让美洲充满狩猎采集者。以每月仅一英里的速度向南扩散,这些先驱者在越过加拿大边境后仅700年就能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与占据先前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土地的民族的实际已知速度相比,这些假设的扩散速度和人口增长率都非常低。因此,美洲可能在最早殖民者到达后的几个世纪内就被狩猎采集者完全占据了。
第二,5000年滞后的很大一部分是否代表了第一批美洲人熟悉他们遇到的新的本地植物物种、动物物种和岩石来源所需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再次以占据先前不熟悉环境的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狩猎采集者和农民为类比——比如新西兰的毛利殖民者或新几内亚卡里穆伊盆地的图道厄殖民者——殖民者可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发现了最好的岩石来源,并学会了区分有用和有毒的野生植物和动物。
第三,欧亚人在发展适合当地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又如何呢?肥沃月湾和中国的早期农民继承了行为现代的智人数万年来为开发这些地区本地资源而发展的技术。例如,肥沃月湾的狩猎采集者一直在发展的用于利用野生谷物的石镰刀、地下储藏坑和其他技术,可供肥沃月湾的第一批谷物农民使用。相比之下,美洲的第一批定居者带着适合西伯利亚北极苔原的装备抵达阿拉斯加。他们必须自己发明适合他们遇到的每个新栖息地的装备。这种技术滞后可能对美洲原住民发展的延迟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迟背后一个更明显的因素是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正如我在第六章中讨论的,当狩猎采集者采用食物生产时,并不是因为他们预见到等待他们远代后裔的潜在利益,而是因为初期食物生产开始提供超越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早期食物生产在美洲与狩猎采集的竞争力不如在肥沃月湾或中国,部分原因是美洲几乎缺乏可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早期美洲农民仍然依赖野生动物获取动物蛋白,必然保持兼职狩猎采集者的身份,而在肥沃月湾和中国,动物驯化在时间上紧随植物驯化之后,创造了一个很快战胜狩猎采集的食物生产组合。此外,欧亚驯化动物通过提供肥料,最终通过拉犁,使欧亚农业本身更具竞争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特征也导致了美洲原住民食物生产竞争力较弱。这个结论对美国东部最为清楚,那里驯化的作物不到十几种,包括小粒种子谷物但没有大粒种子谷物、豆类、纤维作物或栽培果树或坚果树。对中美洲的主要谷物玉米来说也很清楚,玉米后来传播到美洲其他地方成为主导作物。肥沃月湾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几个世纪内以最小的变化演变成作物,而野生类蜀黍(teosinte)可能需要数千年才能演变成玉米,必须在其繁殖生物学和种子生产的能量分配方面经历剧烈变化,失去种子坚硬如岩石的外壳,以及穗轴大小的巨大增加。
因此,即使接受最近提出的美洲原住民植物驯化(domestication)开始的较晚日期,从驯化开始(约公元前3000-2500年)到中美洲、安第斯内陆和美国东部出现广泛的全年定居村落(公元前1800-500年)之间,也经过了约1500或2000年。美洲原住民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狩猎采集获取食物的小补充,仅能支撑稀疏的人口。如果接受传统的、更早的美洲植物驯化开始日期,那么在食物生产支撑起村落之前经过的时间是5000年而非1500或2000年。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村落的出现在时间上与食物生产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两个半球的部分地区,如旧世界的日本和肥沃新月地带,以及新世界的厄瓜多尔海岸和亚马逊地区,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本身已足够高效,在农业采用之前就能支撑村落。)新世界当地可获得的驯化物种所带来的限制,可以从美洲原住民社会在其他作物或动物到达时(无论是来自美洲其他地区还是来自欧亚大陆)自身发生的转变中得到很好的说明。例子包括玉米到达美国东部和亚马逊地区的影响、骆马在南部驯化后被安第斯北部采用的影响,以及马出现在北美和南美许多地区的影响。
除了欧亚大陆的先发优势和野生动植物物种外,欧亚大陆的发展还因为动物、植物、思想、技术和人口在欧亚大陆比在美洲更容易传播而加速,这是由几组地理和生态因素造成的。欧亚大陆的东西向主轴线与美洲的南北向主轴线不同,允许传播时不改变纬度和相关的环境变量。与欧亚大陆一致的东西向宽度相比,新世界在整个中美洲长度上都是收缩的,特别是在巴拿马。最重要的是,美洲被不适合食物生产或密集人口的区域分割得更加破碎。这些生态屏障包括:巴拿马地峡的雨林,将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和亚马逊社会分隔开;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将中美洲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德克萨斯州的干旱地区,将美国西南部与东南部分隔开;以及沙漠和高山,将原本适合食物生产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以及安第斯和亚马逊这些新世界中心之间,没有家畜、文字或政治实体的传播,作物和技术的传播也有限或缓慢。
这些美洲内部屏障的一些具体后果值得一提。食物生产从未从美国西南部和密西西比河谷传播到现代美国的粮仓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那里的美洲原住民社会仍然是狩猎采集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驯化物种。安第斯高地的骆马、豚鼠和马铃薯从未到达墨西哥高地,因此中美洲和北美洲除了狗之外没有家养哺乳动物。反过来,美国东部的家养向日葵从未到达中美洲,中美洲的家养火鸡从未到达南美洲或美国东部。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分别花了3000年和4000年,才走过从墨西哥农田到美国东部农田的700英里。玉米到达美国东部后,又过了七个世纪,才开发出适应北美气候的高产玉米品种,从而引发了密西西比文化的兴起。玉米、豆类和南瓜可能花了数千年才从中美洲传播到美国西南部。肥沃新月地带的作物向西和向东传播得足够快,以至于抢先阻止了同一物种在其他地方的独立驯化,或者近缘物种在其他地方的驯化,而美洲内部的屏障则导致了许多这样的作物平行驯化。
这些屏障对作物和牲畜传播的影响与对人类社会其他特征的影响一样显著。最终起源于东地中海的字母表传播到欧亚大陆所有复杂社会,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除了东亚地区采用了汉字书写系统的衍生形式。相比之下,新世界唯一的书写系统,即中美洲的书写系统,从未传播到可能采用它们的安第斯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在中美洲作为玩具部件发明的轮子,从未遇到在安第斯驯化的骆马,因而未能为新世界产生轮式运输。从东到西,旧世界的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横跨3000英里,蒙古帝国横跨6000英里。但中美洲的帝国和国家与北面700英里外的美国东部酋邦或南面1200英里外的安第斯帝国和国家没有政治关系,显然甚至从未听说过它们。
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地理上更为分散,这一点也反映在语言分布上。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除少数例外,欧亚大陆的所有语言可归入约十几个语系,每个语系包含多达数百种相关语言。例如,印欧语系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希腊语和印地语等约144种语言。这些语系中有相当一部分占据着大片连续区域——以印欧语系为例,其分布区域横跨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延伸至西亚大部和印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共同表明,每一个这样大范围的连续分布都源于某种祖先语言的历史扩张,随后在各地发生语言分化,形成一个相关语言的语系(表18.2)。大多数这类扩张似乎可归因于祖先语言的使用者——属于农业生产社会——相对于狩猎采集者所拥有的优势。我们在第16章和第17章已经讨论过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东亚语系的此类历史扩张。近千年来的主要扩张包括:印欧语言从欧洲传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亚,俄语从东欧横跨西伯利亚,以及突厥语(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从中亚向西传播到土耳其。
除了美洲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分布于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和美国西南部的纳-德内语系外,美洲缺少语言学家普遍认可的大规模语言扩张实例。大多数专门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语言学家,除了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纳-德内语系外,没有发现其他大型、清晰的语言分组。他们充其量认为证据只足以将其他美洲原住民语言(估计数量从600到2000种不等)归入一百多个语言群或孤立语言。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持有一种有争议的少数派观点,他将除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纳-德内语系外的所有美洲原住民语言归入一个单一的大语系,称为美印语系(Amerind),包含约十几个亚语系。
| 推断年代 | 语系或语言 | 扩张路径 | 最终驱动力 |
|---|---|---|---|
| 公元前6000年或公元前4000年 | 印欧语系 | 乌克兰或安纳托利亚→欧洲、中亚、印度 | 农业生产或马匹畜牧业 |
| 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 | 埃兰-达罗毗荼语系 | 伊朗→印度 | 农业生产 |
| 公元前4000年-现在 | 汉藏语系 | 青藏高原、中国北部→中国南部、热带东南亚 | 农业生产 |
|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 | 南岛语系 | 中国南部→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岛屿 | 农业生产 |
| 公元前3000年-公元1000年 | 班图语系 |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南非 | 农业生产 |
| 公元前3000年-公元1年 | 南亚语系 | 中国南部→热带东南亚、印度 | 农业生产 |
| 公元前1000年-公元1500年 | 侗台语系、苗瑶语系 | 中国南部→热带东南亚 | 农业生产 |
| 公元892年 | 匈牙利语 | 乌拉尔山脉→匈牙利 | 马匹畜牧业 |
| 公元1000年-公元1300年 |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 | 亚洲草原→欧洲、土耳其、中国、印度 | 马匹畜牧业 |
| 公元1480年-公元1638年 | 俄语 | 欧洲俄罗斯→亚洲西伯利亚 | 农业生产 |
格林伯格的一些亚语系,以及更传统的语言学家所认可的一些语言分组,可能最终证明是新大陆人口扩张的遗产,这些扩张部分由粮食生产驱动。这些遗产可能包括中美洲和美国西部的乌托-阿兹特克语系(Uto-Aztecan languages)、中美洲的奥托-曼格语系(Oto-Manguean languages)、美国东南部的纳奇兹-马斯科吉语系(Natchez-Muskogean languages),以及西印度群岛的阿拉瓦克语系(Arawak languages)。但语言学家在美洲原住民语言分组上难以达成一致,这反映了复杂的美洲原住民社会自身在新大陆内部扩张时所面临的困难。如果任何从事粮食生产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成功地带着他们的作物和牲畜进行大规模扩张,并在大片地区迅速取代狩猎采集者,他们就会像在欧亚大陆那样留下容易识别的语系遗产,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关系也就不会如此有争议了。
因此,我们已经确定了三组最终因素,它们使优势倒向了欧洲的美洲入侵者:欧亚大陆在人类定居上的长期领先优势;由于可驯化野生植物、特别是动物的更大可得性而产生的更有效的粮食生产;以及在大陆内部传播方面较少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第四个更具推测性的最终因素,来自美洲一些令人困惑的未发明现象:安第斯复杂社会中文字和轮子的未发明,尽管这些社会的时间深度与确实发明了这些东西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大致相当;以及轮子在中美洲仅限于玩具并最终消失,而它们本可以像在中国那样用于人力手推车。这些谜题让人想起小型孤立社会中同样令人困惑的未发明现象,或者说发明的消失,包括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日本、波利尼西亚群岛和美洲北极地区。当然,美洲总体上绝不算小:它们的总面积达到欧亚大陆的76%,而且截至公元1492年,它们的人口可能也占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但正如我们所见,美洲被分割成了彼此联系微弱的社会”岛屿”。也许美洲原住民轮子和文字的历史,以更极端的形式例证了真正岛屿社会所展现的原理。
在至少13,000年的独立发展之后,先进的美洲和欧亚社会终于在过去一千年内发生了碰撞。在此之前,旧世界和新世界人类社会之间的唯一接触,涉及白令海峡两侧的狩猎采集者。
美洲原住民没有试图殖民欧亚大陆,除了在白令海峡,那里有一小群来自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Inuit)(爱斯基摩人)在海峡对面的西伯利亚海岸定居下来。有记录的欧亚人首次试图殖民美洲,是诺斯人(Norse)在北极和亚北极纬度地区的尝试(图18.1)。来自挪威的诺斯人于公元874年殖民冰岛,然后来自冰岛的诺斯人于公元986年殖民格陵兰,最后来自格陵兰的诺斯人在公元1000年至1350年间反复访问北美东北海岸。在美洲发现的唯一诺斯人考古遗址位于纽芬兰,可能就是诺斯传奇故事中描述的文兰(Vinland)地区,但这些传奇故事还提到了显然更靠北的登陆地点,在拉布拉多和巴芬岛海岸。
冰岛的气候允许放牧和极其有限的农业,其面积足以支撑一个延续至今的诺斯后裔人口。但格陵兰的大部分地区被冰盖覆盖,即使是两个最有利的海岸峡湾,对于诺斯人的粮食生产来说也处于边缘状态。格陵兰诺斯人人口从未超过几千人。它一直依赖从挪威进口食物和铁,以及从拉布拉多海岸进口木材。与复活节岛和其他遥远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不同,格陵兰无法支撑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社会,尽管它确实在诺斯人占领期之前、期间和之后支撑了自给自足的因纽特狩猎采集人口。冰岛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少、太穷,无法继续支持格陵兰诺斯人人口。
在13世纪开始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中,北大西洋的降温使格陵兰的粮食生产,以及从挪威或冰岛到格陵兰的诺斯人航行,变得比以前更加边缘化。格陵兰人与欧洲人最后一次已知的接触发生在1410年,当时一艘冰岛船只因偏离航线而抵达。当欧洲人最终在1577年再次开始访问格陵兰时,其诺斯人殖民地已不复存在,显然在15世纪期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消失了。
但是,鉴于公元986-1410年期间的北欧船舶技术,北美海岸实际上超出了直接从挪威本土航行的船只的航程范围。北欧人的访问实际上是从格陵兰殖民地发起的,该殖民地与北美仅隔着200英里宽的戴维斯海峡。然而,这个微小的边缘殖民地支撑对美洲的探索、征服和定居的前景是零。甚至在纽芬兰发现的唯一北欧遗址显然也只不过是一个由几十人占据了几年的冬季营地。北欧传奇故事描述了被称为斯克雷林人(Skraelings)的人对他们文兰营地的攻击,这些人显然是纽芬兰印第安人或多塞特爱斯基摩人。
格陵兰殖民地这个中世纪欧洲最遥远的前哨的命运,仍然是考古学中最浪漫的谜团之一。最后的格陵兰北欧人是饿死了,试图航海离开,与爱斯基摩人通婚,还是死于疾病或爱斯基摩人的箭下?虽然这些近因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但北欧人殖民格陵兰和美洲失败的根本原因却非常清楚。它失败是因为来源地(挪威)、目标地(格陵兰和纽芬兰)以及时间(公元984-1410年)决定了欧洲在粮食生产、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潜在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在纬度太高而无法进行大量粮食生产的地方,少数北欧人的铁制工具在欧洲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微弱支持下,无法与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狩猎采集者的石器、骨器和木制工具相匹敌,后者是世界上北极生存技能的最伟大掌握者。
欧亚大陆第二次殖民美洲的尝试成功了,因为它涉及的来源地、目标地、纬度和时间使欧洲的潜在优势能够有效发挥。西班牙与挪威不同,足够富裕和人口众多,能够支持探索和资助殖民地。西班牙在美洲的登陆地点位于亚热带纬度,非常适合粮食生产,起初主要基于美洲原住民作物,但也包括欧亚家养动物,特别是牛和马。西班牙的跨大西洋殖民事业始于1492年,正值欧洲远洋船舶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世纪结束之时,那时已经融合了旧世界社会(伊斯兰、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开发的航海、帆船和船舶设计方面的进步。因此,在西班牙本土建造和配备人员的船只能够航行到西印度群岛;没有任何类似于扼杀北欧殖民的格陵兰瓶颈。西班牙的新世界殖民地很快被其他六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所加入。
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批定居点始于1492年哥伦布建立的定居点,位于西印度群岛。岛上印第安人在”被发现”时的估计人口超过一百万,在大多数岛屿上因疾病、流离失所、奴役、战争和随意谋杀而迅速灭绝。大约1508年,第一个殖民地在美洲大陆巴拿马地峡建立。对两个大型大陆帝国——阿兹特克和印加的征服分别在1519-1520年和1532-1533年进行。在这两次征服中,欧洲传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做出了重大贡献,杀死了皇帝本人以及大部分人口。即使是极少数骑马西班牙人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加上他们利用原住民人口内部分裂的政治技巧,完成了其余的工作。欧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征服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的原住民国家。
至于北美最先进的原住民社会,即美国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系统的社会,它们的毁灭主要是由早期欧洲探险家引入并在他们之前传播的病菌独自完成的。随着欧洲人在美洲各地扩散,许多其他原住民社会,如大平原的曼丹人(Mandans)和北极的萨德勒米乌特爱斯基摩人(Sadlermiut Eskimos),也在没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被疾病消灭。未被疾病消灭的人口众多的原住民社会以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相同的方式被摧毁——通过全面战争,这些战争越来越多地由专业欧洲士兵及其原住民盟友发动。这些士兵最初得到欧洲母国政治组织的支持,然后是新世界的欧洲殖民政府,最后是继承殖民政府的独立新欧洲国家。
较小的原住民社会被更随意地摧毁,通过私人公民进行的小规模突袭和谋杀。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狩猎采集者最初总数约为20万人,但他们分散在大约一百个部落中,没有一个需要通过战争来击败。这些部落中的大多数在1848-52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或之后不久被杀害或剥夺财产,当时大量移民涌入该州。举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北部的雅希部落,人数约2000人且缺乏火器,在武装白人定居者的四次突袭中被摧毁:1865年8月6日,17名定居者对雅希村庄进行的黎明突袭;1866年在峡谷中对雅希人的屠杀;1867年左右对追踪到洞穴中的33名雅希人的屠杀;以及1868年左右4名牛仔在另一个洞穴中困住约30名雅希人的最后屠杀。许多亚马逊印第安群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橡胶热潮期间被私人定居者以类似方式消灭。征服的最后阶段正在当前十年上演,因为亚诺马米人和其他仍然独立的亚马逊印第安社会正在屈服于疾病,被矿工谋杀,或被传教士或政府机构控制。
最终结果是,从大多数适合欧洲粮食生产和生理的温带地区消灭了人口众多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在北美,那些作为规模可观的完整社区幸存下来的人现在主要生活在保留地或其他被认为不适合欧洲粮食生产和采矿的土地上,如北极和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许多热带地区的美洲原住民已被来自旧世界热带地区的移民所取代(特别是非洲黑人,以及苏里南的亚洲印度人和爪哇人)。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部分地区,美洲原住民最初人数众多,即使在流行病和战争之后,今天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美洲原住民或混血。这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尤其如此,那里欧洲基因的女性甚至在生育方面都有生理困难,而且当地安第斯作物仍然为粮食生产提供最合适的基础。然而,即使在美洲原住民确实幸存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被旧世界的文化和语言大量取代。在北美最初使用的数百种美洲原住民语言中,除了187种外,所有语言都不再被使用,而这最后187种中的149种正在消亡,因为它们只被老年人使用,儿童不再学习。在大约40个新世界国家中,现在所有国家都将印欧语系语言或克里奥尔语作为官方语言。即使在幸存的美洲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看一看政治和商业领袖的照片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是欧洲人,而几个加勒比国家有非洲黑人领袖,圭亚那曾有亚洲印度人领袖。
美洲原住民人口已经减少了一个有争议的大百分比:对北美的估计高达95%。但美洲的总人口现在约为1492年的十倍,因为旧世界人民(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到来。美洲人口现在由来自除澳大利亚以外所有大陆的人民混合组成。过去500年的这种人口转移——除澳大利亚外任何大陆上最大规模的转移——其最终根源在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年之间的发展。
无论事先读过多少关于非洲的书,实际到那里的第一印象都是压倒性的。在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街道上,我看到了黑人赫雷罗人、黑人奥万博人、白人和纳马人,他们与黑人和白人都不同。他们不再只是教科书中的图片,而是我面前活生生的人。在温得和克外,曾经广泛分布的卡拉哈里布须曼人中的最后一批正在为生存而挣扎。但在纳米比亚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路牌:温得和克市中心的一条主要道路被称为戈林街!
我想,当然,没有哪个国家会如此被不悔改的纳粹统治,以至于以臭名昭著的纳粹国家专员和德国空军创始人赫尔曼·戈林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不,事实证明这条街是为了纪念赫尔曼的父亲海因里希·戈林,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后来成为纳米比亚)的创始国家专员。但海因里希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他的遗产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最恶毒的攻击之一,德国1904年对赫雷罗人的灭绝战争。今天,虽然邻国南非的事件更受世界关注,但纳米比亚也在努力应对其殖民历史并建立一个多种族社会。纳米比亚向我展示了非洲的过去与现在是多么密不可分。
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将非洲本地人等同于黑人,将白人非洲人视为近期入侵者,并将非洲种族历史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故事划等号。我们关注这些特定事实有一个明显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数美国人熟悉的唯一非洲本地人,因为他们作为奴隶被大量带到美国。但直到几千年前,现代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居住着非常不同的民族,所谓的非洲黑人本身也是异质的。即使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不仅居住着黑人,而且(我们将看到)居住着世界六大人类分支中的五个,其中三个仅局限于非洲本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语言仅在非洲使用。没有其他大陆能达到这种人类多样性(diversity)。
非洲多样化的民族源于其多样化的地理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从北温带延伸到南温带的大陆,同时还包含世界上一些最干旱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远长于其他任何地方:我们的远古祖先大约在700万年前起源于那里,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可能从那时起就在那里出现了。非洲众多民族之间长期的互动产生了其引人入胜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两次人口迁移——班图扩张(Bantu expansion)和印度尼西亚人对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所有这些过去的互动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谁在谁之前到达哪里的细节正在塑造今天的非洲。
这五个人类分支是如何到达非洲现在的位置的?为什么是黑人变得如此广泛分布,而不是美国人往往忘记存在的其他四个群体?我们如何能够从非洲的前文字时代中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而缺乏像教给我们罗马帝国扩张的书面证据?非洲史前史是一个宏大规模的谜题,目前仅部分解决。事实证明,这个故事与我们在前一章遇到的美国史前史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但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到公元1000年时,非洲已经拥有的五大人类群体是那些被普通人松散地称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Pygmies)、科伊桑人(Khoisan)和亚洲人的群体。图19.1描绘了他们的分布,而第19章后的肖像将提醒您他们在肤色、头发形态和颜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显著差异。黑人以前仅限于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仍然只生活在那里,而更多的白人和亚洲人生活在非洲以外而不是在非洲。这五个群体构成或代表了除澳大利亚原住民及其亲属之外的所有主要人类分支。
许多读者可能已经在抗议:不要通过将人们分类为任意的”种族”来刻板印象化!是的,我承认这些所谓的主要群体中的每一个都非常多样化。将祖鲁人、索马里人和伊博人这样不同的人归入”黑人”这一单一标题下,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将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尔人与欧洲的瑞典人归入”白人”这一单一标题下时,我们同样忽略了巨大的差异。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体之间的划分是任意的,因为每个这样的群体都与其他群体融合:地球上所有人类群体都与他们遇到的其他群体交配。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认识这些主要群体对于理解历史仍然如此有用,以至于我将使用群体名称作为简写,而不在每句话中重复上述警告。
在五个非洲群体中,许多黑人和白人人口的代表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所熟悉,不需要身体描述。即使到公元1400年,黑人也占据了非洲最大的地区:撒哈拉南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见图19.1)。虽然非洲血统的美国黑人主要来自非洲西海岸地区,但类似的民族传统上也占据着东非,向北到苏丹,向南到南非本身的东南海岸。白人,从埃及人和利比亚人到摩洛哥人,占据了非洲的北部海岸地区和撒哈拉北部。这些北非人很难与蓝眼睛金发的瑞典人混淆,但大多数普通人仍然会称他们为”白人”,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被称为”黑人”的南方民族更浅,头发更直。非洲的大多数黑人和白人依靠农业或畜牧业,或两者兼而有之,为生。
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两个群体,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包括没有作物或牲畜的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像黑人一样,俾格米人有深色皮肤和紧密卷曲的头发。然而,俾格米人与黑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体型更小,皮肤更偏红色而不是黑色,面部和身体毛发更多,前额、眼睛和牙齿更突出。俾格米人主要是狩猎采集者,广泛分散在中非雨林的各个群体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进行贸易(或为他们工作)。
霍伊桑人是美国人最不熟悉的群体,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们曾经分布在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包括被称为桑人的小型狩猎采集者,还包括被称为霍伊人的较大型牧民。(这些名称现在比更为人知的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更受欢迎。)霍伊人和桑人看起来(或曾经看起来)与非洲黑人完全不同:他们的皮肤呈黄色,头发非常紧密地卷曲,女性的臀部往往会积累大量脂肪(称为”臀脂过多症(steatopygia)“)。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霍伊人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欧洲殖民者射杀、驱逐或感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多数幸存者与欧洲人通婚,产生了在南非被称为有色人种或巴斯特人的人群。桑人同样遭到射杀、驱逐和感染,但少数幸存者在纳米比亚不适合农业的沙漠地区保持了他们的独特性,正如几年前广为流传的电影《上帝也疯狂》中所描绘的那样。
非洲白人在北部的分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东和欧洲的邻近地区生活着身体特征相似的民族。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在欧洲、近东和北非之间来回迁移。因此,在本章中我将不再过多讨论非洲白人,因为他们的起源并不神秘。相反,谜团涉及黑人、俾格米人和霍伊桑人,他们的分布暗示着过去的人口动荡。例如,目前20万俾格米人的零散分布,分散在1.2亿黑人中,表明俾格米猎人曾经广泛分布在赤道森林中,直到被黑人农民的到来所取代和孤立。霍伊桑人在南部非洲的分布区域对于一个在解剖学和语言上如此独特的民族来说小得令人惊讶。霍伊桑人是否也曾经分布更广,直到他们更北部的人群以某种方式被消灭?
我把最大的异常留到了最后。马达加斯加大岛距离东非海岸仅250英里,比其他任何大陆都更接近非洲,并且与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隔着整个印度洋。马达加斯加的人民被证明是两个元素的混合体。毫不奇怪,一个元素是非洲黑人,但另一个元素由从外貌上立即可识别为热带东南亚人的人组成。具体来说,马达加斯加所有人——亚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说的语言是南岛语(Austronesian),与4000多英里外横跨印度洋的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上使用的马安延语(Ma’anyan)非常相似。在马达加斯加数千英里范围内,没有其他任何与婆罗洲人相似的民族。
这些南岛人及其南岛语言和改良的南岛文化,在1500年欧洲人首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时就已经在那里定居了。这对我来说是整个世界人类地理学中最令人惊讶的单一事实。这就好像哥伦布到达古巴时,发现那里住着说着接近瑞典语的蓝眼睛、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附近的北美大陆上居住着说美洲印第安语言的美洲原住民。史前婆罗洲人究竟如何在没有地图或指南针的船上航行,最终到达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的案例告诉我们,人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外貌,可以为他们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仅仅通过观察马达加斯加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热带东南亚,但我们不会知道来自热带东南亚的哪个地区,我们也永远不会猜到婆罗洲。从非洲语言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我们从非洲面孔中还不知道的东西?
斯坦福大学伟大的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澄清了非洲1500种语言令人费解的复杂性,他认识到所有这些语言只属于五个语系(分布见图19.2)。习惯于认为语言学枯燥和技术性的读者可能会惊讶地了解到,图19.2为我们理解非洲历史做出了多么引人入胜的贡献。
如果我们首先比较图19.2和图19.1,我们会看到语系和解剖学定义的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粗略的对应关系:给定语系的语言往往由不同的人说。特别是,亚非语系(Afroasiatic)的使用者大多被证明是被归类为白人或黑人的人,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和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的使用者被证明是黑人,霍伊桑语系(Khoisan)的使用者是霍伊桑人,南岛语系(Austronesian)的使用者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与说这些语言的人一起进化。
隐藏在图19.2顶部的是我们的第一个惊喜,对于所谓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欧洲中心主义信徒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们被教导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欧洲带到辉煌的高度,并产生了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产生于说三种密切相关语言的民族中,称为闪米特语(Semitic languages):分别是亚拉姆语(基督和使徒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我们本能地将闪米特民族与近东联系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确定,闪米特语系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的语言家族——亚非语系(Afroasiatic)中六个或更多分支之一,该语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以及其他222种现存语言)都局限于非洲。即使闪米特语亚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语言,其19种现存语言中有12种仅限于埃塞俄比亚。这表明亚非语系起源于非洲,只有其中一个分支传播到了近东。因此,可能正是非洲孕育了《旧约》、《新约》和《古兰经》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而这些经典正是西方文明的道德支柱。
图19.2中的下一个惊喜似乎是一个细节,当我刚才告诉你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语言时,我并未对此发表评论。在非洲的五个人群——黑人、白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中——只有俾格米人没有任何独特的语言:每一群俾格米人都说着与邻近黑人农民群体相同的语言。然而,如果比较俾格米人所说的某种语言与黑人所说的同一种语言,俾格米人版本似乎包含一些具有独特发音的独特词汇。
当然,最初像俾格米人这样独特的人群,生活在像赤道非洲雨林这样独特的地方,肯定足够孤立,能够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家族。然而,今天那些语言已经消失,我们已经从图19.1中看到,俾格米人的现代分布高度分散。因此,分布和语言线索结合起来表明,俾格米人的家园被入侵的黑人农民吞没,剩余的俾格米人采用了他们的语言,仅在一些词汇和发音中留下了他们原始语言的痕迹。我们之前看到,马来西亚尼格利陀人(塞芒人)和菲律宾尼格利陀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们分别从包围他们的农民那里采用了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语言。
图19.2中尼罗-撒哈拉语系的分散分布同样暗示,这些语言的许多使用者已被亚非语系或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使用者吞没。但科伊桑语系的分布证明了一次更戏剧性的吞没。这些语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独特地使用咂音(clicks)作为辅音而闻名。(如果你对!Kung布须曼人这个名字感到困惑,那个感叹号并非表示过早的惊讶;它只是语言学家表示咂音的方式。)所有现存的科伊桑语言都局限于南部非洲,只有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是两种非常独特、充满咂音的科伊桑语言,名为哈扎语(Hadza)和桑达韦语(Sandawe),它们孤立地存在于坦桑尼亚,距离最近的南部非洲科伊桑语言超过1,000英里。
此外,科萨语(Xhosa)和南部非洲的其他一些尼日尔-刚果语言充满了咂音。更出乎意料的是,咂音或科伊桑词汇也出现在肯尼亚黑人所说的两种亚非语系语言中,它们距离现在的科伊桑人群比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桑达韦人还要远。所有这些都表明,科伊桑语言和民族以前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他们现在的南部非洲分布,直到他们也像俾格米人一样被黑人吞没,只留下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语言遗产。这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仅从对现存人群的体质研究中我们很难猜到这一点。
我把语言学最显著的贡献留到了最后。如果你再看一次图19.2,你会看到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在整个西非和亚赤道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显然没有给出任何线索表明该语系在这个巨大范围内的哪里起源。然而,格林伯格认识到,亚赤道非洲的所有尼日尔-刚果语言都属于一个称为班图语(Bantu)的单一语言亚群。该亚群占尼日尔-刚果语系1,032种语言的近一半,占尼日尔-刚果语系使用者(近2亿)的一半以上。但所有这500种班图语言彼此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被戏称为单一语言的500种方言。
总的来说,班图语言仅构成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个单一、低级别的亚族。其他176个亚族大多集中在西非,这只是整个尼日尔-刚果语系范围的一小部分。特别是,最独特的班图语言,以及与班图语言关系最密切的非班图尼日尔-刚果语言,都集中在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小区域。
显然,尼日尔-刚果语系起源于西非;其班图语分支起源于该范围的东端,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然后班图人从那个家园传播到亚赤道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传播的开始时间必定足够久远,以至于祖先的班图语有时间分化为500种子语言,但又足够近,以至于所有这些子语言仍然彼此非常相似。由于所有其他尼日尔-刚果语系使用者以及班图人都是黑人,我们无法仅从体质人类学的证据推断出谁向哪个方向迁移。
为了说明这种语言学推理,让我给你一个熟悉的例子:英语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最多的是在北美,其他人分散在全球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英语方言。如果我们对语言分布和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可能会猜测英语起源于北美,并由殖民者带到海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
但所有这些英语方言只构成了日耳曼语系的一个低阶亚群。所有其他亚群——各种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和荷兰语——都挤在欧洲西北部。特别是,弗里西语,另一种与英语关系最密切的日耳曼语言,仅限于荷兰和德国西部的一小片沿海地区。因此,语言学家会立即正确推断出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沿海地区,并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我们从有记载的历史中知道,英语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和六世纪由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那里带到英格兰的。
基本上同样的推理路线告诉我们,现在分布在非洲地图大部分地区的近2亿班图人,起源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连同北非闪米特人的起源和马达加斯加亚洲人的起源,这是另一个没有语言学证据我们无法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从科伊桑语言分布和缺乏独特的俾格米语言推断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布更广,直到他们被黑人吞没。(我使用”吞没”作为一个中性的全面性词汇,无论这个过程涉及征服、驱逐、混血、杀戮还是流行病。)我们现在从尼日尔-刚果语言分布中看到,进行吞没的黑人就是班图人。到目前为止考虑的物理和语言学证据让我们推断出这些史前的吞没,但它仍然没有为我们解开它们的谜团。只有我现在要呈现的进一步证据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另外两个问题:是什么优势使班图人能够取代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班图人何时到达以前的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家园?
为了探讨班图人优势的问题,让我们检查来自当前生活的剩余证据类型——来自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证据。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这些证据很重要,因为粮食生产导致了高人口密度、病菌(germs)、技术、政治组织和其他权力要素。那些由于地理位置的偶然性而继承或发展了粮食生产的民族,因此能够吞没地理条件较差的民族。
当欧洲人在15世纪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时,非洲人正在种植五组作物(图19.3),每一组对非洲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组仅在北非种植,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地。北非享有地中海气候(Mediterranean climate),其特点是降雨集中在冬季月份。(南加州也经历地中海气候,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和数百万其他南加州人的地下室经常在冬天被淹,但在夏天必然会干涸。)农业起源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享有同样的冬雨地中海模式。
因此,北非的原始作物都被证明是适应在冬雨中发芽和生长的作物,并且从考古证据中得知,它们最早在大约1万年前在肥沃新月地带被驯化。那些肥沃新月地带的作物传播到气候相似的北非邻近地区,为古埃及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们包括小麦、大麦、豌豆、豆类和葡萄等熟悉的作物。这些作物对我们来说很熟悉,正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气候相似的欧洲邻近地区,然后传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各地温带农业的一些主要作物。
当人们在非洲向南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带(Sahel)重新遇到降雨时,会注意到萨赫勒的降雨发生在夏季而不是冬季。即使适应冬雨的肥沃新月地带作物能够以某种方式穿越撒哈拉,它们在夏雨萨赫勒地带也很难种植。相反,我们发现两组非洲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出现在撒哈拉以南,并且适应夏雨和较少的季节性日照长度变化。一组包括祖先从西到东广泛分布在萨赫勒地带的植物,可能是在那里被驯化的。它们特别包括高粱(sorghum)和珍珠粟(pearl millet),它们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谷物。高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现在在所有大陆炎热干燥气候的地区种植,包括在美国。
另一组包括野生祖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植物,可能是在那里的高地被驯化的。大多数仍主要在埃塞俄比亚种植,美国人仍不了解——包括埃塞俄比亚的麻醉性恰特草(chat),其类似香蕉的假香蕉(ensete),其含油的努格(noog),用于酿造其国酒的手指谷子(finger millet),以及用于制作其国饼的称为苔麸(teff)的微小种子谷物。但每个沉迷于咖啡的读者都可以感谢古代埃塞俄比亚农民驯化了咖啡树。它一直局限于埃塞俄比亚,直到在阿拉伯流行,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维持着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远方国家的经济。
非洲作物的倒数第二组起源于西非潮湿气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一些作物,包括非洲稻,几乎一直局限在那里;另一些作物,如非洲山药,则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还有两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传播到了其他大陆。西非人早在可口可乐公司诱使美国人、进而诱使全世界的人饮用最初添加了可乐果提取物的饮料之前,就已经在咀嚼这种含咖啡因的果实作为麻醉剂了。
非洲作物的最后一批同样适应潮湿气候,但却带来了图19.3中最大的惊喜。香蕉、亚洲山药和芋头在1400年代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广泛分布,亚洲稻也已在东非海岸种植。但这些作物起源于东南亚热带地区。如果不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已经提醒我们注意非洲史前与亚洲的联系,它们在非洲的存在会让我们感到震惊。难道是从婆罗洲航行而来的南岛语族(Austronesian)人登陆东非海岸,将他们的作物赠予感激的非洲农民,带上非洲渔民,然后向着日出方向航行去殖民马达加斯加,却没有在非洲留下任何其他南岛语族的痕迹吗?
剩下的惊喜是,非洲所有的本土作物——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没有一种非洲作物起源于赤道以南。这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为什么来自赤道以北的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使用者能够取代非洲赤道地区的俾格米人(Pygmy)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Khoisan)。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未能发展农业,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农民有什么不足,而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南部非洲的野生植物大多不适合驯化。无论是班图人(Bantu)还是白人农民,尽管继承了数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都未能将南部非洲的本土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非洲的驯化动物物种可以比植物总结得更快,因为它们的数量非常少。我们确切知道在非洲驯化的唯一动物是一种类似火鸡的鸟,叫做珍珠鸡(guinea fowl),因为它的野生祖先仅限于非洲。家牛、驴、猪、狗和家猫的野生祖先原产于北非,但也存在于西南亚,所以我们还不能确定它们最早是在哪里被驯化的,尽管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驴和家猫的驯化日期倾向于埃及。最近的证据表明,牛可能在北非、西南亚和印度分别独立驯化,这三个种群都对现代非洲牛品种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非洲所有其余的家养哺乳动物必定是在其他地方驯化后作为家畜引入非洲的,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存在于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在西南亚驯化,鸡在东南亚驯化,马在俄罗斯南部驯化,骆驼可能在阿拉伯半岛驯化。
这份非洲家养动物清单最出人意料的特征又是一个否定性的。清单中不包括非洲闻名的任何一种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物种,而非洲拥有如此丰富的这类动物——斑马和角马、犀牛和河马、长颈鹿和水牛。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现实对非洲历史产生的影响,就像赤道以南非洲缺乏本土驯化植物一样充满了后果。
这次对非洲主要食物的快速浏览足以表明,其中一些食物从起源地出发,在非洲内部和外部都传播了很远的距离。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幸运”得多,因为他们从环境中继承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物种的组合。类比于以小麦和牛为食的英国殖民者吞并澳大利亚土著狩猎采集者,我们不得不怀疑,一些”幸运的”非洲人利用他们的优势吞并了他们的非洲邻居。现在,让我们终于转向考古记录,找出是谁在何时吞并了谁。
考古学能告诉我们关于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兴起的实际日期和地点吗?任何熟悉西方文明史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地认为,非洲的粮食生产始于古埃及的尼罗河谷,那个法老和金字塔的土地。毕竟,埃及到公元前3000年无疑是非洲最复杂社会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中心之一。然而事实上,非洲粮食生产最早的考古证据可能反而来自撒哈拉。
当然,今天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干旱到甚至无法支持草的生长。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更加湿润,拥有众多湖泊,野生动物丰富。在那个时期,撒哈拉人开始饲养牛并制作陶器,然后饲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开始驯化高粱和小米。撒哈拉的畜牧业早于粮食生产到达埃及的已知最早日期(公元前5200年),当时到达的是来自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畜的完整组合。粮食生产也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出现,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经从埃塞俄比亚越过现代边界进入肯尼亚北部。
虽然这些结论依据的是考古证据(archaeological evidence),但还有一种独立的方法可以确定栽培植物和家畜到达的时间:通过比较现代语言中对它们的称呼。对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的尼日利亚南部语言中植物术语的比较显示,这些词汇分为三组。首先是某种作物的词汇在所有这些尼日利亚南部语言中都非常相似的情况。这些作物被证明是西非山药、油棕和可乐果等植物——根据植物学和其他证据,这些植物被认为原产于西非并首次在那里被驯化。由于这些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现代尼日利亚南部语言都继承了相同的原始词汇集。
接下来是那些名称仅在尼日利亚南部语言的一个小亚组内保持一致的作物。这些作物被认为起源于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山药。显然,这些作物是在语言开始分化为亚组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南部的,因此每个亚组为这些新植物创造或接受了不同的名称,只有该特定亚组的现代语言继承了这些名称。最后是作物名称在语言组内完全不一致,而是沿着贸易路线传播的作物。这些被证明是新大陆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它们是在跨大西洋航运开始(公元1492年)之后被引入非洲的,并从那时起沿着贸易路线传播,通常带着葡萄牙语或其他外来名称。
因此,即使我们完全没有植物学或考古证据,仅从语言学证据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西非本土作物最先被驯化,印度尼西亚作物其次到达,最后是欧洲引入的作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Christopher Ehret)应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每个非洲语系的人们利用栽培植物和家畜的顺序。通过一种称为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的方法,基于词汇在历史时期变化速度的计算,比较语言学甚至可以得出驯化或作物到达的估计日期。
将作物的直接考古证据与更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推断出数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粱和小米的人说的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语言的祖先语言。同样,首次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说的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的祖先语言。最后,祖先亚非语系(Afroasiatic)语言的使用者可能参与了埃塞俄比亚本土作物的驯化,他们肯定将新月沃地作物引入了北非。
因此,从现代非洲语言中的植物名称得出的证据使我们能够一瞥数千年前非洲使用的三种语言的存在:祖先尼罗-撒哈拉语、祖先尼日尔-刚果语和祖先亚非语。此外,我们可以从其他语言学证据一瞥祖先科伊桑语(Khoisan)的存在,尽管不是从作物名称得出的(因为祖先科伊桑人没有驯化任何作物)。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非洲今天拥有1,500种语言,它足够大,可以在数千年前拥有超过四种祖先语言。但所有其他语言一定消失了——要么是因为说这些语言的人幸存下来但失去了他们的原始语言,如俾格米人(Pygmies),要么是因为人们自己消失了。
现代非洲四个本土语系(即除了最近到达的马达加斯加南岛语系之外的四个)的存续并不是因为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内在优越性。相反,这必须归因于一个历史偶然(historical accident):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亚非语的祖先使用者恰好生活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了栽培植物和家畜,这让他们繁衍壮大,要么取代其他民族,要么强加他们的语言。少数现代科伊桑语使用者的存续主要是因为他们隔离在南部非洲不适合班图农业的地区。
在我们追溯科伊桑人如何在班图浪潮之外存续之前,让我们看看考古学告诉我们关于非洲另一次伟大的史前人口迁移——南岛人对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探索马达加斯加的考古学家现在已经证明,南岛人至少在公元800年之前就已经到达,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在那里,南岛人遇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奇异的活体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独特,就好像它们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马达加斯加长期隔离期间进化而来的。它们包括巨大的象鸟、被称为狐猴(lemurs)的原始灵长类动物,体型像大猩猩,还有侏儒河马。马达加斯加最早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铁制工具、牲畜和作物的遗迹,因此殖民者不仅仅是一小船被吹离航线的渔民;他们组成了一次全面的远征。这次史前4,000英里的远征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线索来自古代水手航海指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该书由一位生活在埃及的匿名商人于公元100年左右撰写。这位商人描述了连接印度、埃及和东非海岸的已经繁荣的海上贸易。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东非沿海定居点出土了大量中东(有时甚至是中国!)产品,如陶器、玻璃和瓷器。商人们等待有利的风向,让他们在东非和印度之间直接穿越印度洋。当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抵达肯尼亚海岸的欧洲人时(1498年),他遇到了斯瓦希里(Swahili)贸易定居点,并找到了一位向导,引导他走上那条通往印度的直航路线。
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同样活跃的海上贸易。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族殖民者通过东部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抵达印度,然后加入了通往东非的西向贸易路线,在那里他们与非洲人汇合并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语族人和东非人的这种结合在马达加斯加基本属于南岛语系的语言中延续至今,其中包含来自肯尼亚沿海班图语言的借词。但在肯尼亚语言中没有相应的南岛语借词,南岛语族人在东非的其他痕迹也非常稀少:主要只是非洲可能继承的印度尼西亚乐器(木琴和齐特琴(zithers))遗产,当然还有那些在非洲农业中变得如此重要的南岛语族作物。因此,人们不禁怀疑,南岛语族人是否没有经由印度和东非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较容易路线,而是以某种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横渡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后来才融入东非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人文地理最令人惊讶的事实仍然存在一些谜团。
考古学能告诉我们关于非洲史前史上另一次重大人口迁移——班图扩张——的什么信息?我们从现代民族及其语言的双重证据中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一直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黑人大陆。相反,这些证据表明,俾格米人(Pygmies)曾经广泛分布在中非雨林中,而科伊桑人(Khoisan)则广泛分布在赤道以南非洲较干燥的地区。考古学能检验这些假设吗?
对于俾格米人,答案是”还不能”,仅仅因为考古学家尚未从中非森林中发现古代人类骨骼。对于科伊桑人,答案是”可以”。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范围以北的赞比亚,考古学家发现了可能类似现代科伊桑人的人类头骨,以及类似科伊桑人在欧洲人到来时仍在南部非洲制作的石器。
至于班图人如何取代那些北方的科伊桑人,考古和语言证据表明,祖先班图农民从西非内陆稀树草原向南扩张到其更潮湿的沿海森林,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图19.4)。在所有班图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的词汇表明,当时班图人已经拥有牛和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如山药(yams),但他们缺乏金属,仍然从事大量捕鱼、狩猎和采集。当他们进入森林时,他们甚至因采采蝇(tsetse flies)传播的疾病而失去了牛。随着他们扩散到刚果盆地的赤道森林地带,开垦花园并增加人口,他们开始吞并俾格米狩猎采集者并将他们压缩到森林本身。
到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东侧进入东非大裂谷和大湖区更开阔的地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亚非语系(Afroasiatic)和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农民和牧民的大熔炉,他们在较干燥的地区种植小米(millet)和高粱(sorghum)并饲养牲畜,还有科伊桑狩猎采集者。由于他们从西非家园继承的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班图人能够在东非不适合所有先前居民的潮湿地区耕作。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推进的班图人已经到达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从他们的尼罗-撒哈拉和亚非语系邻居那里获得小米和高粱(以及这些作物的尼罗-撒哈拉语名称),并重新获得牛。他们还获得了铁,这种金属刚刚开始在非洲萨赫勒(Sahel)地带冶炼。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撒哈拉以南非洲炼铁的起源仍不清楚。这个早期日期与近东炼铁技术到达北非海岸迦太基(Carthage)的日期非常接近,令人怀疑。因此,历史学家通常假设冶金知识是从北方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另一方面,至少从公元前2000年起,西非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就一直在进行铜冶炼。这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金的前身。加强这一假设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铁匠的炼铁技术与地中海的技术如此不同,以至于表明是独立发展的:非洲铁匠发现了如何在他们的村庄熔炉中产生高温并制造钢铁,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Bessemer)熔炉早了2000多年。
随着铁制工具被引入到他们的湿润气候作物中,班图人终于在当时的赤道以南非洲地区组装出了一套无可阻挡的军事-工业组合。在东非,他们仍然需要与众多的尼罗-撒哈拉语系和亚非语系的铁器时代农民竞争。但在南方,有2000英里的土地仅零星分布着缺乏铁器和农作物的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在几个世纪内,通过近代史前时期最迅速的殖民扩张之一,班图农民一路横扫到了纳塔尔,即现在南非东海岸。
这无疑是一次快速而戏剧性的扩张,但很容易将其过度简化,将所有科伊桑人想象成被蜂拥而至的班图部落践踏的对象。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在班图人到来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获得了绵羊和牛。最初的班图先驱者可能人数很少,他们选择适合其山药农业的湿润森林地区,跳过干旱地区,将其留给科伊桑牧民和狩猎采集者。这些科伊桑人与班图农民之间无疑建立了贸易和婚姻关系,各自占据不同的相邻栖息地,就像今天赤道非洲的俾格米狩猎采集者和班图农民仍在做的那样。只有随着班图人口增长并将牛和干旱气候谷物纳入其经济体系,他们才逐渐填补了那些被跳过的地区。但最终结果仍然相同:班图农民占据了大部分原科伊桑领地;那些前科伊桑居民的遗产仅剩下散布在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咂嘴音,以及等待考古学家发现的埋藏头骨和石器;还有一些南部非洲班图人的科伊桑式外貌。
那些消失的科伊桑人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科伊桑人可能生活了数万年的地方,现在是班图人。我们只能通过类比现代目睹的事件来猜测,当手持钢铁的白人农民与澳大利亚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这些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者相遇时。我们知道,狩猎采集者以多种方式被迅速消灭:他们被驱逐,男性被杀害或奴役,女性被充作妻子,两性都感染了农民的流行病。非洲这类疾病的一个例子是疟疾,它由在农民村庄周围繁殖的蚊子传播,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对其产生了遗传抗性,而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可能还没有。
然而,图19.1显示的近代非洲人口分布提醒我们,班图人并未征服所有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在不适合班图农业的南部非洲地区幸存下来。最南端的班图人科萨人止步于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距开普敦以东500英里。并非好望角本身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毕竟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相反,开普地区属于冬雨的地中海气候,班图人的夏雨作物无法生长。到1652年荷兰人带着源自近东的冬雨作物抵达开普敦时,科萨人仍未越过菲什河。
这个看似细微的植物地理学细节对当今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后果是,一旦南非白人迅速杀害、感染或驱赶了开普的科伊桑人口,白人就可以正确地声称他们比班图人更早占据开普,因此对其拥有优先权。这一主张不必认真对待,因为开普科伊桑人的优先权并未阻止白人剥夺他们。更严重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兰定居者只需应对稀疏的科伊桑牧民人口,而非密集的装备铁器的班图农民人口。当白人最终于1702年向东扩张在菲什河遭遇科萨人时,一段绝望的战斗开始了。尽管欧洲人那时可以从开普的安全基地调遣部队,但他们的军队花了九次战争和175年时间,以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的速度推进,才征服了科萨人。如果最初抵达的几艘荷兰船只就面临如此激烈的抵抗,白人怎么可能在开普立足呢?
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部分源于一个地理偶然。开普科伊桑人的家园恰好包含很少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恰好从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夏雨作物;而欧洲人恰好从近10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冬雨作物。正如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的”戈林街”标志提醒我的那样,非洲的过去深深印记在非洲的现在。
这就是班图人能够吞并科伊桑人,而不是反过来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转向非洲史前之谜中的剩余问题:为什么是欧洲人殖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并非相反,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是人类进化数百万年来的唯一摇篮,也可能是解剖学意义上现代智人的故乡。除了非洲巨大的先发优势之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和栖息地,以及世界上最高的人类多样性。一位在10,000年前访问地球的外星人,如果预测欧洲最终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的一系列附庸国,也是情有可原的。
非洲与欧洲碰撞结果背后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他们与美洲原住民的遭遇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享有枪支和其他技术、广泛的识字能力以及维持昂贵的探索和征服计划所必需的政治组织这三重优势。这些优势几乎在碰撞开始时就显现出来: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首次到达东非海岸仅四年后,他就带着一支装备着大炮的舰队返回,迫使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该港口控制着津巴布韦的黄金贸易。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之前发展出这三个优势呢?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三者在历史上都源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但与欧亚大陆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生产被延迟了,这是因为非洲可驯化的本土动植物物种稀少,适合本土粮食生产的面积要小得多,以及其南北走向的轴线,这阻碍了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可能除了少数来自北非的。因此,家畜直到新兴欧亚文明开始利用它们数千年后才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最初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但我们在第9章中看到,野生动物要被驯化,必须足够温顺,服从人类,喂养成本低,对疾病免疫,并且生长迅速,在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的本土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通过所有这些测试的大型野生动物物种之一。它们在非洲的等同物——如非洲水牛、斑马、丛林猪、犀牛和河马——从未被驯化,即使在现代也是如此。
当然,一些大型非洲动物偶尔被驯服过。汉尼拔在他对罗马的失败战争中征用了驯服的非洲象,古埃及人可能驯服过长颈鹿和其他物种。但这些驯服的动物实际上都没有被驯化——也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选择性繁殖并进行基因修饰以使其对人类更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被驯化并骑乘,它们不仅会养活军队,还会提供不可阻挡的骑兵来冲破欧洲骑兵的队伍。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部队本可以推翻罗马帝国。但这从未发生过。
第二个因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亚大陆在可驯化植物方面的差异,尽管不那么极端。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确实产生了本土作物,但品种远少于欧亚大陆。由于适合植物驯化的野生起始材料种类有限,即使是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肥沃月湾晚了几千年才开始。
因此,就植物和动物驯化而言,先发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是非洲。第三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只有欧亚大陆的一半左右。此外,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被农民和牧民占据的赤道以北撒哈拉以南地区只占其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为40亿。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相互竞争的社会和发明,因此发展速度更快。
非洲与欧亚大陆相比更新世后发展速度较慢背后的剩余因素是这些大陆主轴的不同方向。与美洲一样,非洲的主轴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是东西走向(图10.1)。当沿着南北轴移动时,会穿越气候、栖息地、降雨量、日照长度以及作物和牲畜疾病差异很大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一地区驯化或获得的作物和动物很难转移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作物和动物在相距数千英里但处于相同纬度、拥有相似气候和日照长度的欧亚社会之间很容易移动。
农作物和牲畜沿着非洲南北轴线缓慢传播甚至完全停滞,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例如,成为埃及主食的地中海作物需要冬雨和季节性的日照长度变化才能发芽。这些作物无法向南传播到苏丹以南地区,因为那里是夏雨且几乎没有季节性日照变化。埃及的小麦和大麦从未到达好望角的地中海气候区,直到1652年欧洲殖民者带来它们,科伊桑人从未发展出农业。同样,适应夏雨和很少或没有季节性日照长度变化的萨赫勒作物被班图人带到了南部非洲,但无法在好望角本身生长,从而阻止了班图农业的推进。香蕉和其他热带亚洲作物非常适合非洲的气候,如今是热带非洲农业中最高产的主食之一,但无法通过陆路到达非洲。它们显然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才到达,远在它们在亚洲被驯化之后,因为它们不得不等待横跨印度洋的大规模船运。
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阻碍了牲畜的传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蝇携带锥虫,非洲本地野生哺乳动物对此具有抗性,但对引入的欧亚和北非牲畜物种却是毁灭性的。班图人从没有采采蝇的萨赫勒地区获得的牛未能在班图人穿越赤道森林的扩张中存活下来。尽管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经到达埃及,并在不久后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它们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才穿越撒哈拉沙漠,推动了西非骑兵王国的兴起,而且它们从未向南穿越采采蝇地带。虽然牛、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已经到达塞伦盖蒂的北部边缘,但牲畜花了超过2000年才穿越塞伦盖蒂到达南部非洲。
人类技术沿着非洲南北轴线传播的速度同样缓慢。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苏丹和撒哈拉记录的陶器,直到公元1年左右才到达好望角。尽管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发展出书写系统,并以字母形式传播到努比亚的麦罗埃王国,尽管字母书写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但书写在非洲其他地区并未独立产生,而是由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部带入的。
简而言之,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与欧洲和非洲人民本身的差异无关,正如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相反,它是由于地理和生物地理的偶然因素——特别是各大陆不同的面积、轴线以及野生动植物物种的组合。也就是说,非洲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轨迹最终源于地产的差异。
人类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亚力的问题触及了当前人类状况的核心,以及更新世后的人类历史。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各大陆的简短考察,我们该如何回答亚力?
我会对亚力说:不同大陆人民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人民本身的先天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我预计,如果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欧亚大陆的人口能在更新世晚期互换,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现在将占据美洲、澳大利亚以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原住民现在将成为澳大利亚被压迫的零散人口。人们起初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个断言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实验是想象的,我关于其结果的主张无法被验证。但历史学家仍然能够通过回顾性测试来评估相关假设。例如,可以检验当欧洲农民被移植到格陵兰或美国大平原时,以及当最终源自中国的农民移民到查塔姆群岛、婆罗洲的雨林、或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土壤时发生了什么。这些测试证实,相同的祖先人群最终要么灭绝,要么回归狩猎采集生活,要么继续建立复杂的国家,这取决于他们的环境。同样,澳大利亚原住民狩猎采集者被不同地移植到弗林德斯岛、塔斯马尼亚或澳大利亚东南部后,最终要么灭绝,要么成为拥有现代世界最简单技术的狩猎采集者,要么成为集约管理高产渔业的运河建造者,这取决于他们的环境。
当然,各大陆在影响人类社会轨迹的无数环境特征上存在差异。但仅仅列出每一个可能差异的清单并不能构成对亚力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只有四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因素包括各大陆上可作为驯化起点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food production)对于积累食物剩余至关重要,这些剩余可以养活非粮食生产专业人员,也有助于建立大量人口,即使在发展出任何技术或政治优势之前,仅凭数量就能获得军事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所有在小型萌芽酋邦(chiefdom)水平之上发展出的经济复杂、社会分层、政治集中的社会,都是建立在粮食生产基础上的。
但大多数野生动植物物种已被证明不适合驯化:粮食生产一直基于相对较少的牲畜和作物物种。事实证明,各大陆可供驯化的野生候选物种数量差异很大,这是因为大陆面积不同,同时(就大型哺乳动物而言)晚更新世(Late Pleistocene)灭绝事件的影响也不同。这些灭绝在澳大利亚和美洲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结果,非洲最终在生物学上的资源禀赋略逊于面积大得多的欧亚大陆,美洲则更少,澳大利亚更是如此,亚力(Yali)的新几内亚也是如此(面积只有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一,所有原生大型哺乳动物都在晚更新世灭绝了)。
在每个大陆上,动植物驯化都集中在少数几个特别有利的核心区域(homeland),这些区域只占大陆总面积的一小部分。在技术创新和政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远比自己发明的多。因此,大陆内部的传播(diffusion)和迁移对其社会的发展贡献很大,从长远来看,这些社会往往会分享彼此的发展成果(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这是因为毛利(Maori)新西兰火枪战争(Musket Wars)这样简单形式所展示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初缺乏优势的社会要么从拥有优势的社会那里获得优势,要么(如果未能做到)被那些社会取代。
因此,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各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因为它的主轴是东西走向,生态和地理障碍相对较少。对于作物和牲畜的迁移来说,这个推理很直接,因为它们强烈依赖于气候,因此也依赖于纬度。但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技术创新的传播,因为这些创新在不加修改的情况下最适合特定环境。在非洲,传播速度较慢,在美洲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大陆的主轴是南北走向,存在地理和生态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传播也很困难,崎岖的地形和绵长的高山脊梁阻止了向政治和语言统一方向的任何重大进展。
与这些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因素相关的是第三组因素,它们影响大陆之间的传播,这也可能有助于建立本地的驯化物种和技术储备。洲际传播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因为有些大陆比其他大陆更孤立。在过去6000年里,从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容易,为非洲提供了大部分牲畜物种。但半球间传播对美洲原住民的复杂社会没有贡献,美洲在低纬度地区被广阔的海洋与欧亚大陆隔离,在高纬度地区则被地理和仅适合狩猎采集的气候隔离。对于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水障与欧亚大陆隔离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欧亚大陆唯一被证实的贡献是澳洲野犬(dingo)。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包括大陆面积或总人口规模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更多的竞争社会、更多可供采用的创新——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留创新的压力,因为未能这样做的社会往往会被竞争社会淘汰。这种命运降临到了非洲俾格米人(pygmy)和许多其他被农民取代的狩猎采集人群身上。相反,这也降临到了顽固保守的格陵兰诺斯(Norse)农民身上,他们被爱斯基摩(Eskimo)狩猎采集者取代,后者的生存方法和技术在格陵兰条件下远优于诺斯人。在世界各大陆中,欧亚大陆的面积和竞争社会数量最大,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小得多,塔斯马尼亚(Tasmania)尤其如此。美洲尽管总面积很大,但被地理和生态分割,实际上作为几个联系不佳的较小大陆运作。
这四组因素构成了可以客观量化且无可争议的重大环境差异。虽然有人可以质疑我认为新几内亚人平均比欧亚人更聪明的主观印象,但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远小于欧亚大陆,大型动物物种也远少于欧亚大陆。但提及这些环境差异在历史学家中会引来”地理决定论”的标签,这会引起反感。这个标签似乎带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比如人类的创造力毫无价值,或者我们人类是被气候、动植物无助地编程的被动机器人。当然,这些担忧是错误的。没有人类的创造力,我们今天所有人仍会像一百万年前的祖先那样,用石器切肉并生吃。所有人类社会都有富有创造力的人。只是有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材料,以及更有利于利用发明的条件,而其他环境则没有。
这些对亚力问题的回答比亚力本人期望的更长、更复杂。然而,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它们过于简短和过度简化。将所有大陆13,000年的历史压缩到一本400页的书中,平均每个大陆每150年约一页,使得简洁和简化不可避免。然而,这种压缩带来了补偿性的好处:对地区的长期比较能产生单一社会短期研究无法获得的洞察。
自然,亚力问题引发的许多议题仍未解决。目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部分答案以及未来的研究议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发展的理论。现在的挑战是将人类历史发展为一门科学,与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公认的历史科学并列。因此,通过展望历史学科的未来,并概述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来结束本书似乎是合适的。
本书最直接的延伸将是进一步量化,从而更有说服力地确立四组似乎最重要的因素中洲际差异的作用。为了说明驯化起始材料的差异,我提供了每个大陆大型野生陆生草食性和杂食性哺乳动物总数(表9.2)以及大籽谷物总数(表8.1)的数字。一个延伸是汇编大籽豆科植物(豆类)的相应数字,如豆子、豌豆和野豌豆。此外,我提到了使哺乳动物驯化候选者不合格的因素,但我没有列出每个大陆上每个因素使多少候选者不合格。这样做会很有趣,尤其是对非洲而言,那里不合格候选者的百分比高于欧亚大陆:哪些不合格因素在非洲最重要,是什么选择了它们在非洲哺乳动物中的高频率?还应汇编定量数据来测试我的初步计算,这些计算表明欧亚大陆、美洲和非洲主轴线上的传播速度不同。
第二个延伸将是比本书更小的地理尺度和更短的时间尺度。例如,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以下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在欧亚大陆内部,是欧洲社会而不是肥沃新月地带、中国或印度的社会殖民了美洲和澳大利亚,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并在现代世界成为政治和经济主导?一位生活在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之间任何时期的历史学家,如果当时试图预测未来的历史轨迹,肯定会将欧洲的最终主导地位标记为最不可能的结果,因为在这10,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是这三个旧大陆地区中最落后的。从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前500年希腊和随后意大利的崛起,西欧亚大陆几乎所有主要创新——动物驯化、植物驯化、文字、冶金、车轮、国家等——都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或其附近。直到公元900年左右水磨广泛使用之后,阿尔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欧洲对旧大陆技术或文明没有任何重大贡献;相反,它是东地中海、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发展的接受者。即使在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学和技术的流动主要是从从印度延伸到北非的伊斯兰社会流入欧洲,而不是相反。在这些世纪里,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粮食生产几乎与肥沃新月地带同时启动。
那么,为什么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最终将它们数千年的巨大领先优势输给了后来起步的欧洲?当然,人们可以指出欧洲崛起背后的近因:其商人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发明专利保护、未能发展出专制君主和沉重的税收,以及其希腊-犹太-基督教批判性实证探究(empirical inquiry)传统。然而,对于所有这些近因,必须提出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近因本身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肥沃新月地带?
对于肥沃月牙地区,答案是明确的。一旦它失去了因当地可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的集中分布而享有的先发优势,肥沃月牙地区就不再拥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这一先发优势的消失可以详细追溯,表现为强大帝国的西移。在公元前四千年肥沃月牙地区国家兴起之后,权力中心最初仍留在肥沃月牙地区,在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等帝国之间轮转。随着公元前四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从希腊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社会,权力最终第一次不可逆转地向西转移。随着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征服希腊,权力进一步西移,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它最终再次转移到西欧和北欧。
这些转移背后的主要因素一旦将现代肥沃月牙地区与古代对它的描述进行比较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天,“肥沃月牙”和”世界粮食生产领导者”这些说法是荒谬的。前肥沃月牙地区的大片区域现在是沙漠、半沙漠、草原,或是严重侵蚀或盐碱化的不适合农业的地形。该地区一些国家基于石油这一单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短暂财富,掩盖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根本贫困和养活自己的困难。
然而在古代,肥沃月牙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希腊,都被森林覆盖。该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到侵蚀的灌木丛或沙漠的转变已经被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阐明。它的林地被清理用于农业,或被砍伐以获取建筑木材,或被焚烧作为柴火或用于制造石膏。由于降雨量低,因此初级生产力低(与降雨量成正比),植被的再生长无法跟上其破坏的速度,特别是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随着树木和草地覆盖的移除,侵蚀继续进行,山谷淤积,而在低降雨环境中的灌溉农业导致盐分积累。这些过程始于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现代。例如,现代约旦古代纳巴泰王国首都佩特拉附近的最后一片森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汉志铁路期间被砍伐。
因此,肥沃月牙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地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通过破坏自己的资源基础而实施了生态自杀。随着每个东地中海社会依次削弱自己,权力向西转移,从最古老的社会开始,即东部的社会(肥沃月牙地区)。北欧和西欧幸免于这种命运,不是因为其居民更明智,而是因为他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更强健的环境中,降雨量更高,植被能够快速再生。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在粮食生产到来7000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够支持高产的集约农业。实际上,欧洲从肥沃月牙地区获得了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而肥沃月牙地区随后逐渐失去了其作为权力和创新主要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肥沃月牙地区如何失去其对欧洲的巨大早期领先优势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领先地位?它的落后最初令人惊讶,因为中国享有无可争议的优势:粮食生产的兴起几乎与肥沃月牙地区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以及从海岸到青藏高原高山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多样化的作物、动物和技术;一个巨大而富饶的区域,养育着世界上最多的区域人口;以及一个不如肥沃月牙地区干燥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近10000年后仍能支持高产的集约农业,尽管其环境问题今天正在增加,且比西欧更严重。
这些优势和先发优势使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主要技术首创的长长清单包括铸铁、指南针、火药、纸张、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的许多其他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洋控制方面也领先世界。在15世纪初,它派出宝船船队,每支船队由数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组成,总船员多达28000人,横渡印度洋远至非洲东海岸,比哥伦布的三艘小船横渡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早了几十年。为什么中国船只没有绕过非洲南端向西殖民欧洲,而是瓦斯科·达·伽马的三艘小船向东绕过好望角,开启了欧洲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殖民美洲西海岸?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将其技术领先地位输给了以前如此落后的欧洲?
中国宝船船队的终结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七支这样的船队从中国启航。随后,由于一场典型的地方政治异常事件——这种事件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船队被暂停了:中国朝廷两派势力(宦官及其反对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前一派与派遣和统领船队有关联。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时,他们停止了派遣船队,最终拆除了造船厂,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让人想起1880年代扼杀伦敦公共电力照明发展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任何国家出于地方政治问题而采取的无数倒退步骤。但在中国有所不同,因为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停止了整个中国的船队。这一临时决定变得不可逆转,因为没有造船厂继续建造船只来证明那个临时决定的愚蠢,也没有作为重建其他造船厂的焦点。
现在把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与探险船队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启航时发生的情况对比一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个意大利出生的人,先是效忠于法国的安茹公爵,然后是葡萄牙国王。当后者拒绝了他向西探索所需的船只请求时,哥伦布转向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后者也拒绝了,然后是梅迪纳-塞利伯爵,同样拒绝了,最后是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哥伦布的第一次请求,但最终同意了他的再次恳求。如果欧洲统一在前三位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位之下,它对美洲的殖民可能就胎死腹中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在第五次尝试中成功说服了欧洲数百位王公中的一位来资助他。一旦西班牙因此启动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流入西班牙,又有六个国家加入了殖民美洲的行列。欧洲的大炮、电力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其他创新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每一项起初都因特殊原因在欧洲的某些地区被忽视或反对,但一旦在一个地区被采用,最终就会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
欧洲不统一的这些后果与中国统一的后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朝廷不时决定停止其他活动,而不仅仅是海外航行:它放弃了精密水力纺纱机的发展,在14世纪从工业革命的边缘后退,在引领世界钟表制造之后拆毁或几乎废除了机械钟,并在15世纪后期之后从机械装置和技术总体上撤退了。这些统一的潜在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再次爆发,特别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期,当时一个或少数几个领导人的决定关闭了整个国家的学校系统长达五年。
中国的频繁统一和欧洲的永久不统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中国最具生产力的地区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统一。中国从识字之初就只有一个书写系统,很长时间以来只有一种主要语言,两千年来有着实质性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从未接近过政治统一:14世纪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邦国,公元1500年分裂成500个小邦国,在1980年代降至最少25个国家,而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增加到近40个。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都有自己改良的字母表,文化多样性甚至更大。今天继续阻碍欧洲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进行适度统一尝试的分歧,是欧洲根深蒂固的不统一承诺的症状。
因此,理解中国在政治和技术优势上输给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理解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答案再次从地图中得到启示(见附录)。欧洲拥有高度曲折的海岸线,有五个大型半岛,它们在隔离程度上接近岛屿,每个都发展出独立的语言、民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要平滑得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足够大,能够维护其政治独立性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民族,其中一个(不列颠)足够大且足够近,成为欧洲主要的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岛屿,台湾和海南,面积都不到爱尔兰的一半;在台湾近几十年崛起之前,两者都不是主要的独立力量;而日本的地理隔离使其在最近之前比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更加孤立于亚洲大陆。欧洲被高山(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喀尔巴阡山和挪威边境山脉)分割成独立的语言、民族和政治单元,而中国青藏高原以东的山脉作为障碍要弱得多。中国的心脏地带由两个长长的可通航河流系统(长江和黄河)在肥沃的冲积平原上从东到西连接在一起,并且由这两个河流系统之间相对容易的连接(最终由运河连接)从北到南连接起来。因此,中国很早就被两个巨大的高生产力地理核心区所主导,这两个核心区本身只是微弱地相互分离,最终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核心。欧洲最大的两条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规模较小,连接的欧洲地区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核心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长期主导其他核心区,每个都是长期独立国家的中心。
一旦中国在公元前221年最终统一,就再也没有其他独立国家有机会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尽管公元前221年之后分裂时期多次出现,但它们总是以重新统一告终。但欧洲的统一抵制了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等坚定征服者的努力;即使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也从未控制过欧洲一半以上的面积。
因此,地理上的连通性和适度的内部障碍给了中国最初的优势。华北、华南、沿海和内陆为最终统一的中国贡献了不同的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征。例如,小米种植、青铜技术和文字起源于华北,而水稻种植和铸铁技术出现在华南。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中,我强调了在没有巨大障碍的情况下发生的技术传播(diffusion)。但中国的连通性最终成为一种劣势,因为一个专制者的决定可能并且确实反复阻止了创新。相比之下,欧洲的地理巴尔干化导致了数十或数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创新中心。如果一个国家不追求某项特定创新,另一个国家会追求,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落后。欧洲的障碍足以阻止政治统一,但不足以阻止技术和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一个专制者能像在中国那样关闭整个欧洲的创新龙头。
这些比较表明,地理连通性对技术演化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从很长远来看,技术可能在连通性适度的地区发展最快,既不太高也不太低。过去1000年中国、欧洲以及可能的印度次大陆的技术发展历程,分别体现了高、中、低连通性的净效应。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历史的不同进程。例如,肥沃月牙地带、中国和欧洲在面对中亚游牧民族骑马入侵的长期威胁方面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游牧群体(蒙古人)最终摧毁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没有一个亚洲游牧民族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外的西欧森林中建立统治。环境因素还包括肥沃月牙地带在地理上的中间位置,控制着连接中国和印度到欧洲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远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文明的位置,使中国成为一个大陆内的巨大虚拟岛屿。中国的相对孤立与其对技术的采纳和拒绝特别相关,这让人想起塔斯马尼亚和其他岛屿的拒绝(第13章和第15章)。但这个简短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期历史模式的相关性,以及与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相关性。
肥沃月湾和中国的历史也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会改变,过去的优势地位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优势地位。人们甚至可能会怀疑,本书中使用的地理推理是否在现代世界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现在想法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传播到世界各地,货物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空运在大陆之间运输。似乎全新的规则适用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因此新的强国正在崛起——比如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
然而,经过思考,我们发现所谓的新规则只是旧规则的变体。是的,1947年在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跨越8000英里在日本启动了一个电子工业——但它并没有跨越更短的距离在扎伊尔或巴拉圭建立新的工业。崛起为新强国的国家仍然是那些在几千年前就被纳入基于粮食生产的旧统治中心的国家,或者是被来自这些中心的人重新定居的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强国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因为他们的人口已经有了悠久的识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粮食生产中心——肥沃月湾和中国——仍然主导着现代世界,要么通过它们的直接继承国(现代中国),要么通过位于受这两个中心早期影响的邻近地区的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欧洲),要么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定居或统治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主导世界的前景依然暗淡。公元前8000年历史进程之手对我们的影响依然深重。
在回答亚力的问题的其他相关因素中,文化因素和个人的影响占据重要地位。首先谈谈前者,人类的文化特征在世界各地差异很大。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文化差异是环境差异的产物,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了许多例子。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与环境无关的地方文化因素的可能意义。一个次要的文化特征可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暂时的地方原因而产生,然后被固定下来,接着使一个社会倾向于更重要的文化选择,正如混沌理论在其他科学领域的应用所暗示的那样。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历史的不确定因素之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
举一个例子,我在第13章提到了打字机的QWERTY键盘。它最初是从许多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被采用的,原因是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早期打字机制造、打字机销售、1882年在辛辛那提创办速记和打字学院的朗利小姐的决定,以及朗利小姐的明星打字学生弗兰克·麦格林的成功有关的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麦格林在1888年一场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击败了朗利小姐的非QWERTY竞争对手路易斯·陶布。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许多阶段,决定本可以选择另一种键盘;美国的环境并没有使QWERTY键盘比其竞争对手更有优势。然而,一旦做出决定,QWERTY键盘就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个世纪后它也被用于计算机键盘设计。同样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现在已经消失在遥远的过去,可能是苏美尔人采用基于12而不是10的计数系统(导致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天、12个月一年和360度一圈)的原因,与广泛流行的中美洲基于20的计数系统(导致其历法使用260个命名日的两个并发周期和365天一年)形成对比。
打字机、时钟和日历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影响采用它们的社会的竞争成功。但很容易想象它们本可以产生影响。例如,如果美国的QWERTY键盘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被采用——比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得多的Dvorak键盘——那么19世纪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可能会对20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一项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当教授汉语发音的字母转录(称为拼音)时,他们学习写作的速度比教授传统汉字时更快,传统汉字有数千个符号。有人认为,后者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分大量具有不同含义但发音相同的汉语词汇(同音词)。如果是这样的话,汉语中同音词的丰富可能对中国社会识字的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国的环境似乎不太可能选择一种富含同音词的语言。是语言或文化因素导致了复杂的安第斯文明未能发展出文字这一令人困惑的失败吗?印度的环境是否有任何因素倾向于形成僵化的社会经济种姓制度(caste),并对印度技术的发展产生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是否有任何因素倾向于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这也可能深刻影响了历史?为什么传教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欧洲人和西亚人殖民和征服的推动力,而不是中国人?
这些例子说明了关于文化特性的广泛问题,这些特性与环境无关,最初并不重要,但可能演变成有影响力且持久的文化特征。它们的重要性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未解答问题。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的影响后仍然令人困惑的历史模式上。
个体的影响
那么特异的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呢?一个我们熟悉的现代例子是1944年7月20日,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和柏林同时发生的起义险些失败。这两个行动都是由一些德国人策划的,他们确信战争无法获胜,希望在那时寻求和平,当时德国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位于俄罗斯边境内。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置得离他坐的椅子更近一点,他可能已经被炸死。如果希特勒确实被杀,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时结束,现代东欧地图和冷战的进程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更鲜为人知但更具决定性的是1930年夏天的一起交通事故,在希特勒在德国夺权前两年多,当时他乘坐的汽车坐在”死亡座位”(右前乘客座位)上,与一辆重型拖车相撞。拖车及时刹车,避免了碾过希特勒的汽车并压死他。由于希特勒的精神病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纳粹的政策和成功,如果卡车司机晚刹车一秒钟,最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可能会大不相同。
人们可以想到其他一些个体,他们的特性显然像希特勒一样影响了历史: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皇帝帕查库蒂(Pachacuti)、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Shaka),等等。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而不是”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普世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在这里工作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对政治的内部运作有长期的第一手经验:“政治家的任务是听到上帝穿越历史的脚步声,并在他经过时试图抓住他的衣摆。”
与文化特性一样,个人特性为历史进程投下了不确定因素(wild cards)。它们可能使历史无法用环境力量,甚至任何可概括的原因来解释。然而,就本书而言,它们几乎不相关,因为即使是伟人理论最热心的支持者也很难用几个伟人来解释历史的最广泛模式。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确实推动了西欧亚大陆已有的识字、生产粮食、装备铁器的国家的进程,但他与西欧亚大陆在澳大利亚仍然只支持缺乏金属工具的非识字狩猎采集部落时就已经支持识字、生产粮食、装备铁器的国家这一事实无关。尽管如此,特异个体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广泛和持久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历史作为科学
历史学科通常不被认为是科学,而是更接近人文学科。充其量,历史被归类为社会科学,其中它被评为最不科学的学科。虽然政府领域通常被称为”政治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指的是”经济科学”,但历史系很少将自己标记为”历史科学系”。大多数历史学家不认为自己是科学家,并且在公认的科学及其方法论方面接受的培训很少。历史只不过是一堆细节的感觉被许多格言所捕捉:“历史只是一个该死的事实接着另一个该死的事实”,“历史或多或少是废话”,“历史没有规律,就像万花筒没有规律一样”,等等。
人们不能否认,从研究历史中提取一般原则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提取一般原则更困难。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困难并非致命的。类似的困难也适用于其他历史学科,尽管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是安全的,包括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不幸的是,人们对科学的印象通常基于物理学和其他一些具有类似方法论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往往无知地蔑视那些不适合这些方法论的领域,因此必须寻求其他方法论——比如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但请记住,“科学”一词的意思是”知识”(来自拉丁语scire,“知道”,和scientia,“知识”),通过最适合特定领域的任何方法获得。因此,我非常同情人类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
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等)有许多共同特征,使它们与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非历史科学区别开来。我想指出四个方面:方法论(methodology)、因果关系(causation)、预测(prediction)和复杂性(complexity)。
在物理学中,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室实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操纵所要研究的参数,同时执行保持该参数恒定的平行对照实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其他参数恒定,重复实验操纵和对照实验,并获得定量数据。这一策略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也很有效,在许多人心目中如此认同科学,以至于实验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但实验室实验显然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几乎不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人们无法中断星系形成,启动和停止飓风和冰河时代,通过实验在几个国家公园里灭绝灰熊,或者重演恐龙进化的过程。相反,人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在这些历史科学中获取知识,例如观察、比较和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稍后我将讨论这一点)。
历史科学关注的是近因(proximate)和终极因(ultimate)的因果链。在大多数物理学和化学中,“终极因”、“目的”和”功能”的概念是无意义的,但它们对于理解一般的生命系统和特别是人类活动至关重要。例如,一位进化生物学家研究北极野兔,其皮毛颜色从夏季的棕色变为冬季的白色,不会仅仅满足于从皮毛色素的分子结构和生物合成途径来识别皮毛颜色的平凡近因。更重要的问题涉及功能(伪装以防捕食者?)和终极因(自然选择从具有季节性不变皮毛颜色的祖先野兔种群开始?)。同样,欧洲历史学家不会仅仅满足于描述1815年和1918年欧洲的状况,即在代价高昂的泛欧战争后刚刚实现和平。理解导致两个和平条约的不同事件链对于理解为什么在1918年后几十年内再次爆发了一场代价更高的泛欧战争,而在1815年后却没有,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化学家不会为两个气体分子的碰撞指定目的或功能,也不会寻求碰撞的终极因。
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涉及预测。在化学和物理学中,检验对系统理解的试金石是能否成功预测其未来行为。同样,物理学家往往看不起进化生物学和历史学,因为这些领域似乎未能通过这一测试。在历史科学中,人们可以提供事后解释(例如,为什么6600万年前地球上的小行星撞击可能导致恐龙灭绝而许多其他物种没有灭绝),但事先预测更加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实际的过去事件来指导我们,我们将不确定哪些物种会被驱逐灭绝)。然而,历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确实对未来发现的数据将向我们展示关于过去事件的内容进行预测和检验。
使预测尝试复杂化的历史系统特性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人们可以指出,人类社会和恐龙极其复杂,其特征是大量相互反馈的独立变量。因此,组织较低层次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较高层次出现涌现(emergent)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30年希特勒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一位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亿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这些人被杀害或受伤。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同意生物系统最终完全由其物理性质决定并遵守量子力学定律,但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确定性因果关系并不转化为可预测性。量子力学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引入的有胎盘捕食者灭绝了如此多的澳大利亚有袋动物物种,或者为什么协约国而不是同盟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每个冰川、星云、飓风、人类社会和生物物种,甚至有性繁殖物种的每个个体和细胞,都是独特的,因为它受到如此多的变量的影响,并由如此多的可变部分组成。相比之下,对于物理学家的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学家的分子,该实体的所有个体都彼此相同。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在宏观层面制定普遍的确定性定律(deterministic laws),但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制定统计趋势(statistical trends)。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预测,在我工作的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接下来出生的1000名婴儿中,男孩不会少于480个或多于520个。但我无法提前知道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会是男孩。同样,历史学家注意到,如果当地人口足够庞大和密集,并且有剩余粮食生产的潜力,部落社会可能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酋邦(chiefdoms),而不是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但每个这样的地方人口都有其独特的特征,结果是酋邦确实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地出现了,但在新几内亚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高地却没有。
描述历史系统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尽管它们最终具有确定性,但长长的因果链可能将最终效果与该科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分开。例如,恐龙可能是被一颗小行星撞击而灭绝的,而这颗小行星的轨道完全由经典力学定律决定。但如果在6700万年前有古生物学家存在,他们也无法预测恐龙即将灭绝,因为小行星属于与恐龙生物学相距甚远的科学领域。同样,公元1300-1500年的小冰河期导致了格陵兰诺斯人的灭绝,但没有历史学家,甚至可能连现代气候学家都无法预测小冰河期的到来。
因此,历史学家在建立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时所面临的困难,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面临的困难大体相似。在不同程度上,这些领域都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无法进行重复的、受控的实验干预,大量变量导致的复杂性,每个系统的独特性,因此无法制定普遍规律,以及预测涌现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和未来行为的困难。历史中的预测,就像其他历史科学一样,在大空间尺度和长时间跨度上最为可行,因为数百万个小规模短暂事件的独特特征会被平均化。正如我可以预测接下来1000个新生儿的性别比,但无法预测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性别一样,历史学家可以识别那些使美洲和欧亚社会在分离发展13000年后碰撞的广泛结果不可避免的因素,但无法预测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1960年10月一场电视辩论中某位候选人说了什么的细节可能会将选举胜利给予尼克松而非肯尼迪,但无论谁说了什么都无法阻止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征服。
人类历史的研究者如何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经验中获益?一种已被证明有用的方法涉及比较方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虽然研究星系形成的天文学家和人类历史学家都无法在受控的实验室实验中操纵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在某些假定因果因素的存在或缺失(或强或弱效应)方面不同的系统。例如,流行病学家虽然被禁止实验性地给人们喂食大量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盐摄入量已经存在巨大差异的人群来识别高盐摄入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家虽然无法实验性地为人类群体提供数个世纪的不同资源丰度,但仍然通过比较生活在资源丰度自然不同的岛屿上的近期波利尼西亚人口,来研究资源丰度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人类历史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的自然实验远不止五大有人居住大陆之间的比较。比较还可以利用在相当程度上孤立发展出复杂社会的大型岛屿(如日本、马达加斯加、美洲原住民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新几内亚、夏威夷等),以及数百个较小岛屿上的社会和各大陆内的区域社会。
任何领域的自然实验,无论是生态学还是人类历史,本质上都容易受到潜在方法论批评。这些批评包括除了感兴趣的变量之外的其他自然变异的混淆效应,以及从观察到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推断因果链的问题。这些方法论问题已经在一些历史科学中得到了详细讨论。特别是流行病学,这门通过比较人群(通常通过回顾性历史研究)来推断人类疾病的科学,长期以来成功地采用了正式化程序来处理与人类社会历史学家面临的类似问题。生态学家也对自然实验的问题投入了大量关注,这是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必须采用的方法,因为直接实验干预以操纵相关生态变量可能是不道德的、非法的或不可能的。进化生物学家最近一直在开发越来越复杂的方法,从已知进化历史的不同植物和动物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简而言之,我承认理解人类历史比理解历史不重要且个体变量较少的科学领域的问题要困难得多。然而,用于分析历史问题的成功方法已经在几个领域中被开发出来。因此,恐龙、星云和冰川的历史通常被公认为属于科学领域而非人文学科。但内省(introspection)使我们对其他人类方式的洞察远胜于对恐龙的洞察。因此我乐观地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像研究恐龙一样科学地进行——并且通过教导我们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什么可能塑造我们的未来,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益。
《枪炮、病菌与钢铁》(GGS)探讨的是为什么复杂人类社会的兴起在过去13,000年中于不同大陆展现出不同的进程。我在1996年完成了手稿的修订工作,并于1997年出版。此后,我主要投入到其他项目的工作中,特别是关于社会崩溃的下一本书。因此,在时间和研究重点上,我现在与GGS的写作已相隔七年。回顾这本书,它的表现如何?自出版以来,有哪些变化或延伸扩展了书中的结论?在我承认带有偏见的眼光看来,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经受住了考验,自出版以来最有趣的发展涉及将这个故事延伸到现代世界和近代历史的四个方面。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大陆上的社会发展出不同的形态,是因为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生物学的差异。先进技术、集中的政治组织以及复杂社会的其他特征,只能在能够积累食物盈余的密集定居人口中出现——这些人口的食物依赖于约公元前8,500年开始兴起的农业。但对农业兴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大陆的分布极不均匀。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集中在全球仅有的九个小区域,这些区域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发源地。这些发源地的原始居民因此在发展枪炮、病菌和钢铁方面获得了先机。这些发源地居民的语言和基因,以及他们的牲畜、作物、技术和文字系统,在古代和现代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过去六年左右,考古学家、遗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专家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但并未改变其主要轮廓。让我举三个例子。GGS地理覆盖范围中最大的空白之一涉及日本,关于日本的史前史,我在1996年几乎没有提及。最近的遗传证据表明,现代日本人是类似于GGS中讨论的其他农业扩张的产物:约公元前400年开始,朝鲜农民扩张到日本西南部,然后沿日本群岛向东北推进。移民带来了集约化水稻农业和金属工具,他们与日本原始居民(与现代阿伊努人有关)混合,产生了现代日本人,就像扩张的肥沃月湾农民与欧洲原始狩猎采集人口混合产生现代欧洲人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最初认为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通过墨西哥东北部和德克萨斯州东部的最直接路线到达美国东南部。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这条路线对农业来说太干旱了;这些作物实际上走了一条更长的路线,从墨西哥传播到美国西南部,引发了那里阿纳萨齐社会的兴起,然后从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通过大平原的河谷向东传播到美国东南部。
最后一个例子,在第10章中,我对比了沿美洲南北轴线同一或相关植物的频繁重复独立驯化和缓慢传播,与欧亚大陆作物主要的单次驯化和快速东西向传播。这两种对比模式的更多例子不断出现,但现在看来,欧亚大陆五大家畜中的大部分或全部也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经历了重复的独立驯化——不像欧亚大陆的植物,但像美洲的植物。
这些和其他发现为我们理解农业的兴起如何引发古代世界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的兴起增添了细节,这些细节继续让我着迷。然而,建立在GGS基础上的最大进展涉及延伸到并非本书主要关注点的领域。自出版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拦住我,告诉我他们注意到GGS的古代大陆进程与他们研究的现代或近代进程之间的相似或对比。我将告诉你其中四个启示:简要地说,新西兰火枪战争(Musket Wars)的启发性例子;“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更详细地说,古代世界竞争与现代商业世界竞争之间的相似性;以及GGS与为什么今天一些社会富裕而另一些贫穷的相关性。
在1996年,我在第13章中用一个简短的段落描述了19世纪新西兰历史中的一个现象,称为火枪战争,作为强大的新技术如何传播的例证。火枪战争是1818年至1830年代之间新西兰土著毛利人部落之间一系列复杂的、不太为人理解的部落战争——欧洲枪支通过这些战争在以前用石器和木制武器相互作战的部落之间传播。此后出版的两本书增进了我们对新西兰历史那个混乱时期的理解,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并使其与GGS的相关性更加明确。
在1800年代初期,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捕鲸者开始访问新西兰。新西兰在600年前已被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民占据,这些人被称为毛利人。最早的欧洲访客集中在新西兰的北端。那些最早接触欧洲人的北部毛利部落因此成为最早获得火枪的部落,这使他们相对于所有其他缺乏火枪的部落拥有了巨大的军事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来清算与邻近部落的宿怨,这些部落是他们的传统敌人。但他们也将火枪用于一种新型战争:对数百英里外的毛利部落进行远距离突袭,以便在获取奴隶和威望方面超越对手。
在使远距离突袭成为可能方面,与欧洲火枪同等重要的是欧洲引入的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马铃薯每英亩或每个农民的粮食产量比基于红薯的传统毛利农业高出许多倍。之前阻止毛利人进行长距离突袭的主要限制是两个相关问题:长时间在外作战的战士的粮食供应,以及依赖这些准战士留在家中种植红薯的妇女和儿童的家中人口的粮食供应。马铃薯解决了这个瓶颈。因此,火枪战争一个不那么英勇的名称应该是马铃薯战争。
无论它们被称为什么,火枪/马铃薯战争被证明极具破坏性,杀死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始毛利人口。当一个拥有大量火枪和马铃薯的部落攻击一个很少或没有火枪和马铃薯的部落时,死亡人数最高。在那些不是最早获得火枪和马铃薯的部落中,一些部落在能够获得它们之前几乎被消灭,而其他部落则努力获得它们,从而恢复了之前的军事平衡。这些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是毛利部落对莫里奥里部落的征服和大规模杀戮,如第2章所述。
火枪/马铃薯战争说明了贯穿过去10,000年历史的主要过程:拥有枪支、病菌和钢铁,或拥有早期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每个人都分享了新的优势。随着欧洲人向其他大陆扩张,近代历史提供了无数的例子。在许多地方,非欧洲当地人从未有机会获得枪支,最终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然而,日本确实成功地获得了(实际上是重新获得)枪支,保持了其独立性,并在50年内使用其新枪支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击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北美平原印第安人、南美阿劳卡尼亚印第安人、新西兰毛利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枪支,并用它们长期阻止欧洲征服,尽管他们最终被击败。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尽最大努力通过获得第一世界的技术和农业优势来赶上第一世界。这种技术和农业的传播,最终源于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在过去10,000年中肯定在无数其他时间和地点发生过。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西兰的火枪/马铃薯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虽然这些战争是仅限于新西兰的纯粹地方现象,但它们具有全球性意义,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如此清晰的例子,在空间和时间上如此狭窄地局限,涵盖了许多其他类似的地方现象。在引入新西兰北端后的大约二十年内,火枪和马铃薯已经传播了900英里到新西兰的南端。在过去,农业、文字和改进的前枪械武器花了更长的时间传播更远的距离,但人口替代和竞争的基本社会过程本质上是相同的。现在我们想知道核武器是否会通过同样经常充满暴力的过程在世界各地扩散,从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八个国家开始。
自1997年以来积极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可以称为”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大陆之间的差异:即为什么是一些欧亚人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在过去的千年中扩张到世界各地的问题。然而,我意识到许多读者也会想知道”为什么在欧亚人中,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其他群体扩张?“我知道我的读者不会让我在不对这个明显的问题说任何话的情况下结束《枪炮、病菌与钢铁》。
因此,我在书的后记中简要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背后的根本原因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提出的直接因素(例如,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兴起,欧洲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兴起,英国的森林砍伐加上其煤炭储量等)更深层。在这些和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佳分裂原则”(Optimal Fragmentation Principle):导致中国早期统一并在此后大部分时间保持统一的根本地理因素,而欧洲则一直保持分裂。欧洲的分裂确实促进了技术、科学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中国的统一则没有,因为分裂通过促进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为创新者(innovator)提供替代支持来源和免受迫害的避难所。
历史学家们后来向我指出,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和中国的相对实力,都比我叙述中描绘的更为复杂。可以有效归类为”欧洲”或”中国”的政治/社会领域的地理边界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变化。至少在15世纪之前,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欧洲,未来也可能再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指一个短暂的现象,没有深层的解释。政治分裂(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影响比仅仅提供建设性竞争论坛更为复杂:例如,竞争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想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它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思想和人员跨越分裂边界流动的自由度,以及这些分裂片段是彼此独立还是只是互相的复制品。分裂是否”最优”也可能因所使用的最优化衡量标准而异;对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可能对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幸福并不最优。
我的感觉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仍然倾向于用近因解释(proximate explanations)来解释欧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进程。例如,在最近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Jack Goldstone强调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动机科学(engine science)“的重要性,即将科学应用于机器和发动机的开发。Goldstone写道:”所有前工业经济体在能源方面都面临两个问题:数量和集中度。任何前工业经济体可用的机械能数量都受限于水流、可以喂养的动物或人,以及可以捕获的风。在任何地理固定的区域,这个数量都是严格受限的……很难夸大第一个设计出从化石燃料中提取有用功的方法的经济体或军事/政治力量所获得的优势……正是蒸汽动力在纺织、水上和地面运输、制砖、脱粒、炼铁、铲掘、建筑以及各种制造过程中的应用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发动机科学的丰富发展远非欧洲文明的必然发展,而是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恰好出现的特定的、即使是高度偶然的情况的偶然结果。“如果这一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寻找深层的地理或生态解释将不会有成效。
与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GS)后记中表达的观点相似的少数派观点,已被Graeme Lang详细论证:“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科学在这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降雨]农业在欧洲没有为国家提供角色,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远离当地社区,当欧洲的农业革命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农业剩余时,这允许了相对自治的城镇以及大学等城市机构在中世纪晚期集中制国家兴起之前的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灌溉和水利控制]农业则有利于在主要河谷早期发展出侵入性和强制性的国家,而城镇及其机构从未达到欧洲所发现的地方自治程度。其次,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相反,中国的地理环境促进了最终在广阔地区的征服和统一,随后是帝国统治下相对稳定的长期时期。由此产生的国家体系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需的大部分条件……上述解释当然过于简化。然而,这种解释的优点之一是,它避免了那些不深入到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或文化差异的解释中经常出现的循环论证。这类解释总是可以用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来挑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在那些社会或文化因素方面有所不同?然而,最终植根于地理和生态的解释已经触及了基岩。”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协调这些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问题的不同方法仍然是一个挑战。答案可能对如何最好地治理当今的中国和欧洲具有重要影响。例如,从Lang和我的角度来看,中国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当时少数误入歧途的领导人能够关闭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学校系统长达五年,可能不是一个独特的一次性异常事件,而可能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灾难,除非中国能够在其政治体系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相反,欧洲在今天急于实现政治和经济统一的过程中,必须深思如何避免拆除其过去五个世纪成功背后的根本原因。
最近将《枪炮、病菌与钢铁》(GGS)的信息延伸到现代世界的第三个方面,对我来说是最出乎意料的。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比尔·盖茨对其给予了好评,然后我开始收到其他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的来信,他们指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讨论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与商业世界中群体历史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这些通信涉及以下广泛的问题:组织人类群体、组织和企业以最大化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和财富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你的群体应该有一个集中的领导(极端情况下是独裁者),还是应该有分散的领导甚至是无政府状态?你的人员集合应该组织成一个单一的群体,还是分解成少数或大量的群体?你应该在群体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还是在它们之间竖起保密的墙?你应该竖起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来对抗外部,还是应该让你的企业接受自由竞争?
这些问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和许多类型的群体中。它们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组织:记住关于最佳政府形式是仁慈的独裁、联邦制度还是无政府状态的长期争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公司的组织中。我们如何解释微软最近如此成功,而IBM虽然以前成功,却落后了,但随后大幅改变了其组织并提高了成功率这一事实?我们如何解释不同工业带的不同成功?当我还是个在波士顿长大的男孩时,波士顿周围的工业带128号公路在科学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领先世界。但128号公路已经落后,现在硅谷是创新的中心。硅谷和128号公路上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可能导致了这些不同的结果。
当然,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力也存在著名的差异,如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商业部门的生产力和财富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韩国钢铁业在效率上与我们相当,但所有其他韩国行业都落后于美国同行。这些不同韩国行业的不同组织方式是什么,导致了它们在同一国家内的生产力差异?
显然,关于组织成功差异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个人的特质。例如,微软的成功肯定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才能有关。即使有优越的公司组织,如果领导者无能,微软也不会成功。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或者从长远来看,或者平均而言,什么形式的人类群体组织是最好的?
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结语中对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历史的比较,为应用于整个国家技术创新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正如上一节所解释的,我推断,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刺激了地理上分散的欧洲的创新,而缺乏这种竞争阻碍了统一的中国的创新。这是否意味着比欧洲更高程度的政治分裂会更好?可能不是:印度在地理上甚至比欧洲更分散,但在技术上的创新能力较弱。这向我提出了最优碎片化原则(Optimal Fragmentation Principle):创新在具有某种最优中间程度碎片化的社会中进展最快:过于统一的社会处于不利地位,过于分散的社会也是如此。
这一推论引起了比尔·刘易斯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其他高管的共鸣,这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领先咨询公司,对世界各地的国家和行业经济进行比较研究。这些高管对他们的商业经验与我的历史推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印象深刻,以至于他们向公司的数百名合伙人每人赠送了一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并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巴西和其他国家经济的报告副本。他们也发现竞争和群体规模在刺激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下是我从与麦肯锡高管的对话和他们的报告中收集到的一些结论:
我们美国人经常幻想德国和日本的工业超级高效,在生产力上超过美国工业。实际上,这并不正确:平均而言,在所有行业中,美国的工业生产力高于日本或德国。但这些平均数字掩盖了每个国家行业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与组织方式的差异有关——这些差异非常有启发性。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自麦肯锡关于德国啤酒行业和日本食品加工行业的案例研究。
德国人酿造出色的啤酒。每次我和妻子飞往德国探访时,我们都会带上一个空行李箱,这样就能装满德国啤酒瓶带回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享用。然而德国啤酒行业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只有美国啤酒行业的43%。与此同时,德国的金属加工和钢铁行业的生产力却与美国同行相当。既然德国人显然完全有能力把行业组织得很好,为什么在啤酒方面就做不到呢?
原因在于德国啤酒行业受困于小规模生产。德国有一千家小型啤酒公司,它们免受彼此竞争的影响,因为每家德国啤酒厂实际上都拥有地方垄断(monopoly)地位,同时它们也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美国有67家主要啤酒厂,年产230亿升啤酒。德国全部1000家啤酒厂加起来的产量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因此美国啤酒厂的平均产量是德国啤酒厂的31倍。
这一事实源于当地口味和德国政府政策。德国啤酒饮用者对本地品牌极其忠诚,因此德国没有类似我们百威、米勒或库尔斯的全国性品牌。相反,大多数德国啤酒都在距离酿造厂30英里范围内消费。因此德国啤酒行业无法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中获益。在啤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大幅下降。制作啤酒的冷藏设备越大,啤酒装瓶流水线越长,啤酒制造成本就越低。那些德国小型啤酒公司效率相对较低。没有竞争,只有一千个地方垄断。
德国饮酒者的地方啤酒忠诚度因德国法律而得到强化,这些法律使外国啤酒难以在德国市场竞争。德国政府有所谓的啤酒纯度法,明确规定啤酒中可以添加什么成分。不出所料,这些政府纯度规定是基于德国啤酒厂在啤酒中添加的成分,而不是美国、法国和瑞典啤酒厂喜欢添加的成分。由于这些法律,出口到德国的外国啤酒不多,而且由于效率低下和价格高昂,出口到国外的德国优质啤酒远少于你原本预期的数量。(在你反对说德国Löwenbräu啤酒在美国广泛销售之前,请阅读你在这里喝的下一瓶Löwenbräu的标签:它不是在德国生产的,而是在北美按许可证生产的,在具有北美生产力和规模效率的大型工厂中生产。)
德国的肥皂行业和消费电子行业同样效率低下;它们的公司既不面临彼此的竞争,也不面临外国竞争,因此它们没有学习国际行业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你上次购买德国制造的进口电视机是什么时候?)但这些劣势并未影响德国金属和钢铁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德国大公司必须相互竞争并在国际上竞争,因此被迫学习最佳国际实践。
我从麦肯锡报告中最喜欢的另一个例子涉及日本食品加工行业。我们美国人往往对日本效率感到paranoid(偏执),日本在某些行业的效率确实令人生畏——但在食品加工方面却不然。日本食品加工行业的效率只有我们的32%,令人失望。日本有67000家食品加工公司,而人口是日本两倍的美国只有21000家——因此美国食品加工公司的平均规模是日本同行的六倍。为什么日本食品加工行业像德国啤酒行业一样,由拥有地方垄断地位的小公司组成?基本上,答案是相同的两个原因:当地口味和政府政策。
日本人对新鲜食品极为狂热。美国超市的牛奶容器上只有一个日期:保质期。当我和妻子与妻子的一位日本表亲一起参观东京超市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日本牛奶容器上有三个日期:牛奶生产日期、到达超市日期和保质期。日本的牛奶生产总是在午夜零点零一分开始,这样早上上市的牛奶就可以标注为今天的牛奶。如果牛奶在晚上11点59分生产,容器上的日期就必须表明牛奶是昨天生产的,没有日本消费者会购买它。
因此,日本食品加工公司享有地方垄断地位。日本北部的牛奶生产商无法指望在日本南部竞争,因为运输牛奶到那里需要额外一两天时间,在消费者眼中这是致命的劣势。这些地方垄断因日本政府而得到强化,政府通过实施10天检疫等限制来阻碍外国加工食品的进口。(想象一下,那些回避标注为只有一天的食品的日本消费者对10天前的食品会有什么感觉。)因此日本食品生产公司既不面临国内竞争也不面临外国竞争,它们没有学习生产食品的最佳国际方法。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食品价格非常高:最好的牛肉每磅200美元,而鸡肉每磅25美元。
其他一些日本产业的组织方式与食品加工业截然不同。例如,日本的钢铁、金属、汽车、汽车零部件、相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公司竞争激烈,其生产力高于美国同行。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行业,与日本食品加工业一样,没有面临竞争,没有应用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因此生产力低于美国相应行业。(如果你环顾家中,很可能会发现你的电视机和相机,也许还有汽车,都是日本产品,但你的计算机和肥皂却不是。)
最后,让我们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比较美国国内不同的产业带或企业。自从《枪炮、病菌与钢铁》(GGS)出版以来,我花了很多时间与来自硅谷和128号公路的人交流,他们告诉我这两个产业带在企业精神方面有很大不同。硅谷由许多相互激烈竞争的公司组成。尽管如此,仍有大量合作——思想、人员和信息在公司之间自由流动。相比之下,我被告知,128号公路的企业彼此之间更加保密和隔离,就像日本的牛奶生产公司一样。
微软和IBM之间的对比又如何呢?自从《枪炮、病菌与钢铁》(GGS)出版以来,我在微软结识了一些朋友,了解了这家公司独特的组织方式。微软有许多单元,每个单元由5到10人组成,单元之间自由沟通,这些单元不受微观管理;它们在追求自己的想法方面被允许有很大的自由度。微软这种不寻常的组织方式——本质上被分解成许多相互竞争的半独立单元——与IBM的组织方式形成对比,IBM在几年前由更加隔离的小组组成,导致IBM失去了竞争能力。后来IBM聘请了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他大刀阔斧地改变了现状:IBM现在有了更像微软的组织方式,我被告知IBM的创新能力因此得到了改善。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也许能够提取出一个关于团队组织的一般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能力,你既不想要过度统一,也不想要过度分散。相反,你希望你的国家、行业、产业带或公司被分解成相互竞争的团队,同时保持相对自由的沟通——就像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其50个州之间存在内在的竞争。
《枪炮、病菌与钢铁》(GGS)的另一个延伸涉及世界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什么一些国家(如美国和瑞士)富裕,而其他国家(如巴拉圭和马里)贫穷?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多倍。这不仅仅是一个为经济学教授提供就业机会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贫穷国家就可以专注于改变使它们贫穷的因素,并采用使其他国家富裕的因素。
显然,部分答案取决于人类制度(institutions)的差异。这一观点最清晰的证据来自几对国家,它们基本上拥有相同的环境,但制度截然不同,与这些制度相关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同。四个明显的例子是韩国与朝鲜、前西德与前东德、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以及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比较。在这些国家对中,常被用来解释前者更富裕的许多”良好制度”包括有效的法治、合同执行、私有财产权保护、缺乏腐败、暗杀频率低、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投资激励等等。
毫无疑问,良好制度确实是解释国家财富差异的部分答案。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更进一步,认为良好制度是压倒性的最重要解释。许多政府、机构和基金会将其政策、对外援助和贷款建立在这一解释之上,将在贫穷国家发展良好制度作为首要任务。
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良好制度观点是不完整的——不是错误的,只是不完整——如果贫穷国家要变得富裕,还需要解决其他重要因素。这种认识有其自身的政策含义。人们不能仅仅向巴拉圭和马里等贫穷国家引入良好制度,就期望这些国家采用这些制度并达到美国和瑞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良好制度观点的批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承认除良好制度外其他近因变量(proximate variables)的重要性,如公共卫生、土壤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力的限制以及环境脆弱性。另一种类型涉及良好制度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仅仅将良好制度(institutions)视为一种近因影响是不够的,其起源不应被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实践意义。良好制度并非一个随机变量,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以同等概率出现,无论是在丹麦还是在索马里。相反,在我看来,过去良好制度的产生总是源于一条漫长的历史链条,从根植于地理的终极原因到制度这一近因变量。如果我们希望现在能在缺乏良好制度的国家快速建立这些制度,就必须理解这条链条。
在我写《枪炮、病菌与钢铁》时,我评论道:“今天崛起的新兴国家仍然是那些数千年前就被纳入基于粮食生产的旧统治中心的国家,或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定居的国家……公元前8000年历史进程的影响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经济学家的两篇新论文(Olsson和Hibbs的研究,以及Bockstette、Chanda和Putterman的研究)对这种假定的历史重压进行了详细检验。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那些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的地区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高于历史较短的国家。这种效应解释了国民生产总值方差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只在那些国民生产总值仍然较低或最近才较低的国家中,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的地区(如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增长率也高于历史较短的国家(如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尽管一些历史较短的国家拥有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
这些历史效应有许多明显的原因,例如国家社会和农业的长期经验意味着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市场经济的经验等等。从统计上看,历史的这种终极效应部分是通过良好制度这一熟悉的近因来实现的。但在控制了通常的良好制度衡量标准之后,历史仍然存在很大的影响。因此必定还存在其他中介的近因机制。因此,一个关键问题将是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详细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条链条前进。
简而言之,《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题在我看来不仅是古代世界的驱动力量,也是现代世界研究的成熟领域。
我很高兴能够感谢许多人对本书的贡献。我在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老师向我介绍了历史的魅力。我对许多新几内亚朋友的巨大感激将从我频繁引用他们的经历中显而易见。我同样感激(并免除他们对我错误的责任)我的许多科学家朋友和专业同事,他们耐心地解释了各自学科的微妙之处并审阅了我的草稿。特别是Peter Bellwood、Kent Flannery、Patrick Kirch和我的妻子Marie Cohen阅读了整个手稿,Charles Heiser Jr.、David Keightley、Bruce Smith、Richard Yarnell和Daniel Zohary每人阅读了几章。几个章节的早期版本曾作为文章发表在《发现》杂志和《自然历史》杂志上。国家地理学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支持了我在太平洋岛屿的实地考察。我很幸运有John Brockman和Katinka Matson作为我的代理人,Lori Iversen和Lori Rosen作为我的研究助理和秘书,Ellen Modecki作为我的插图师,以及Donald Lamm(W. W. Norton出版社)、Neil Belton和Will Sulkin(Jonathan Cape出版社)、Willi Köhler(Fischer出版社)、Marc Zabludoff、Mark Wheeler和Polly Shulman(《发现》杂志)以及Ellen Goldensohn和Alan Ternes(《自然历史》杂志)作为我的编辑。
这些建议是为那些有兴趣进一步阅读的人准备的。因此,除了关键书籍和论文外,我还优先选择了提供早期文献综合列表的参考文献。期刊标题(斜体)后面是卷号,冒号后是首页和末页页码,然后是出版年份(括号中)。
与本书大多数章节相关的参考文献中,有一部巨著是L. Luca Cavalli-Sforza、Paolo Menozzi和Alberto Piazza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本非凡的书近似于关于每个人的一切历史,因为作者在介绍每个大陆时都以该大陆的地理、生态和环境的便捷摘要开始,随后是其民族的史前史、历史、语言、体质人类学和文化。L. Luca Cavalli-Sforza和Francisco Cavalli-Sforza的《人类大迁徙》(马萨诸塞州雷丁:Addison-Wesley出版社,1995年)涵盖了类似内容,但是为普通读者而非专家撰写的。
另一个便捷的资料来源是名为《人类图解史》(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umankind)的系列丛书,共五卷,由Göran Burenhult编辑(旧金山: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3-94年)。该系列的五卷分别为《最早的人类》(The First Humans)、《石器时代的人们》(People of the Stone Age)、《旧大陆文明》(Old World Civilizations)、《新大陆和太平洋文明》(New World and Pacific Civilizations)以及《今日传统民族》(Traditional Peoples Today)。
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不同日期)出版的几个系列丛书提供了特定地区或时代的历史。其中一个系列的书名为《剑桥X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X]),其中X分别指非洲、早期内亚、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日本、拉丁美洲、波兰和东南亚。另一个系列是《剑桥X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X]),其中X分别指非洲、中国、日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俄罗斯和前苏联、澳大利亚、中东和北非,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和邻近国家。还有其他系列包括《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和《剑桥印度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关于世界语言的三部百科全书式著作是Barbara Grimes的《民族语:世界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第13版(达拉斯:夏季语言学研究所,1996年),Merritt Ruhlen的《世界语言指南》(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C. F. Voegelin和F. M. Voegelin的《世界语言分类与索引》(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纽约:Elsevier出版社,1977年)。
在大型比较历史著作中,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2卷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4-54年)尤为突出。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一部出色的欧亚文明史,特别是西欧亚文明史。同一作者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尽管书名如此,实际上也侧重于西欧亚文明,V. Gordon Childe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修订版(巴尔的摩:企鹅图书,1954年)也是如此。另一部侧重于西欧亚的比较历史著作是C. D. Darlington的《人类与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Man and Society)(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1969年),作者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认识到我所讨论的大陆历史与驯化之间的一些相同联系。Alfred Crosby的两本书是关于欧洲海外扩张的杰出研究,重点关注随之而来的植物、动物和病菌:《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学后果》(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1492)(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Greenwood出版社,1972年)和《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年》(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Marvin Harris的《食人者与国王: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8年),以及Marshall Sahlins和Elman Service编辑的《进化与文化》(Evolution and Culture)(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是从文化人类学家视角撰写的比较历史著作。Ellen Semple的《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纽约:Holt出版社,1911年)是早期研究地理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一个例子。其他重要的历史研究列在尾声部分的延伸阅读中。我的著作《第三种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纽约: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2年),特别是其第14章关于欧亚大陆和美洲比较历史的内容,为我思考本书提供了起点。
最知名或最具争议的近期关于群体智力差异的参与者是Richard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的《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纽约:Free Press出版社,1994年)。
关于早期人类进化的优秀著作包括Richard Klein的《人类生涯》(The Human Care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Roger Lewin的《争议之骨》(Bones of Contention)(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1989年),Paul Mellars和Chris Stringer编辑的《人类革命:现代人类起源的行为与生物学视角》(The Human Revolution: Behaviour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s)(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89年),Richard Leakey和Roger Lewin的《起源的再思考》(Origins Reconsidered)(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92年),D. Tab Rasmussen编辑的《人类与人性的起源与进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Humans and Humanness)(波士顿:Jones and Bartlett出版社,1993年),Matthew Nitecki和Doris Nitecki编辑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起源》(Origins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纽约:Plenum出版社,1994年),以及Chris Stringer和Robin McKie的《非洲出走》(African Exodus)(伦敦:Jonathan Cape出版社,1996年)。三本专门讨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通俗著作是Christopher Stringer和Clive Gamble的《寻找尼安德特人》(In Search of the Neanderthals)(纽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93年),Erik Trinkaus和Pat Shipman的《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als)(纽约:Knopf出版社,1993年),以及Ian Tattersall的《最后的尼安德特人》(The Last Neanderthal)(纽约:Macmillan出版社,1995年)。
人类起源的遗传学证据是前言中已引用的L. Luca Cavalli-Sforza等人的两本书的主题,也是我的著作《第三种黑猩猩》第一章的内容。两篇包含遗传学证据最新进展的技术论文是J. L. Mountain和L. L. Cavalli-Sforza的”通过核DNA限制性多态性的分支分析推断人类进化”(Inference of human evolution through cladistic analysis of nuclear DNA restriction polymorphism),《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1:6515-19(1994年),以及D. B. Goldstein等人的”基于微卫星的遗传学绝对定年和现代人类的起源”(Genetic absolute dating based on microsatellit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同上92:6723-27(1995年)。
关于人类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殖民,以及那里大型动物的灭绝的参考文献,列在第15章的延伸阅读中。特别是Tim Flannery的《未来的食客》(The Future Eaters)(纽约:Braziller出版社,1995年),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讨论了这些主题,并解释了关于澳大利亚已灭绝大型哺乳动物最近仍然存活的说法所存在的问题。
关于更新世晚期和近期大型动物灭绝的标准文本是Paul Martin和Richard Klein主编的《第四纪灭绝》(Quaternary Extinctions)(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4年)。更近期的更新包括Richard Klein的”早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案例”,见J. E. Jacobsen和J. Firor主编的《人类对环境的影响》(Hum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第13-34页(博尔德,科罗拉多州:Westview出版社,1992年),以及Anthony Stuart的”北欧亚和北美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灭绝”,《生物学评论》(Biological Reviews) 66:453-62(1991年)。David Steadman在他的论文”太平洋岛屿鸟类的史前灭绝:生物多样性与动物考古学的结合”中总结了伴随人类定居太平洋岛屿而来的灭绝浪潮的最新证据,《科学》(Science) 267:1123-31(1995年)。
关于美洲的定居、伴随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议的通俗读物有Brian Fagan的《伟大的旅程:古代美洲的人口迁移》(The Great Journey: The Peopling of Ancient America)(纽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87年),以及我的书《第三种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的第18章,这两本书都提供了许多其他参考文献。Ronald Carlisle主编的《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人:冰河时代的起源》(Americans before Columbus: Ice-Age Origins)(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8年)包括J. M. Adovasio及其同事关于Meadowcroft遗址克洛维斯文化之前证据的章节。C. Vance Haynes Jr.是克洛维斯地层(Clovis horizon)和据报道的克洛维斯文化之前遗址的专家,他的论文包括”放射性碳测年对新大陆人口迁移地质年代学的贡献”,见R. E. Taylor、A. Long和R. S. Kra主编的《四十年后的放射性碳》(Radiocarbon after Four Decades)第354-74页(纽约:Springer出版社,1992年),以及”克洛维斯-福尔松地质年代学与气候变化”,见Olga Soffer和N. D. Praslov主编的《从Kostenki到克洛维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印第安适应》(From Kostenki to Clovis: Upper Paleolithic Paleo-Indian Adaptations)第219-36页(纽约:Plenum出版社,1993年)。关于Pedra Furada遗址的克洛维斯文化之前主张由N. Guidon和G. Delibrias在”碳-14年代表明32000年前美洲就有人类”中论述,《自然》(Nature) 321:769-71(1986年),以及David Meltzer等人的”关于巴西Pedra Furada的更新世人类居住”,《古物》(Antiquity) 68:695-714(1994年)。与克洛维斯文化之前争论相关的其他出版物包括T. D. Dillehay等人的”南美洲最早的狩猎采集者”,《世界史前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6:145-204(1992年),T. D. Dillehay的《蒙特维德:智利的更新世晚期遗址》(Monte Verde: A Late Pleistocene Site in Chile)(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出版社,1989年),T. D. Dillehay和D. J. Meltzer主编的《最早的美洲人:探索与研究》(The First Americans: Search and Research)(博卡拉顿:CRC出版社,1991年),Thomas Lynch的”南美洲的冰川时代人类?——批判性回顾”,《美国古物》(American Antiquity) 55:12-36(1990年),John Hoffecker等人的”白令陆桥的殖民与新大陆的人口迁移”,《科学》259:46-53(1993年),以及A. C. Roosevelt等人的”亚马逊的古印第安洞穴居民:美洲的人口迁移”,《科学》272:373-84(1996年)。
两本明确关注波利尼西亚岛屿间文化差异的杰出著作是Patrick Kirch的《波利尼西亚酋长制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同一作者的《湿与干》(The Wet and the D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Peter Bellwood的《波利尼西亚人》(The Polynesians)修订版(伦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87年)的大部分内容也涉及这个问题。关于特定波利尼西亚岛屿的著名书籍包括Michael King的《毛里奥里人》(Moriori)(奥克兰:Penguin出版社,1989年),关于查塔姆群岛,Patrick Kirch的《羽毛神与鱼钩》(Feathered Gods and Fishhooks)(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关于夏威夷,Patrick Kirch和Marshall Sahlins的《阿纳胡鲁》(Anahulu)(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也是关于夏威夷,Jo Anne Van Tilburg的《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出版社,1994年),以及Paul Bahn和John Flenley的《复活节岛,地球岛》(Easter Island, Earth Island)(伦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1992年)。
我对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叙述综合了以下目击者的记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和佩德罗·皮萨罗,以及皮萨罗的同伴米格尔·德·埃斯特特、克里斯托瓦尔·德·梅纳、鲁伊斯·德·阿尔塞和弗朗西斯科·德·塞雷斯。埃尔南多·皮萨罗、米格尔·德·埃斯特特和弗朗西斯科·德·塞雷斯的记述由克莱门茨·马卡姆翻译,收录于《秘鲁发现报告》,哈克卢伊特学会,第1辑,第47卷(纽约,1872年);佩德罗·皮萨罗的记述由菲利普·米恩斯翻译,《秘鲁王国的发现与征服记》(纽约:科尔特斯学会,1921年);克里斯托瓦尔·德·梅纳的记述由约瑟夫·辛克莱翻译,《秘鲁征服记,由皮萨罗远征队成员记录》(纽约,1929年)。鲁伊斯·德·阿尔塞的记述重印于《马德里皇家历史学院公报》102:327-84(1933年)。约翰·赫明的优秀著作《印加帝国的征服》(圣迭戈: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0年)全面叙述了这次俘获以及整个征服过程,并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19世纪关于这次征服的记述,威廉·H·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纽约,1847年),至今仍极具可读性,位列历史写作经典之列。相应的现代和19世纪经典的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的记述分别是休·托马斯的《征服:蒙特祖玛、科尔特斯与旧墨西哥的陷落》(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3年)和威廉·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纽约,1843年)。征服阿兹特克人的当代目击者记述由科尔特斯本人撰写(重印为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科尔特斯致皇帝的五封信》[纽约:诺顿出版社,1969年])以及科尔特斯的许多同伴撰写(重印于帕特里夏·德·富恩特斯编,《征服者们》[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这七章关于粮食生产的参考文献将合并列出,因为许多参考文献适用于多个章节。
五个重要来源都很出色且内容丰富,探讨了粮食生产如何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演化而来:肯特·弗兰纳里,“农业的起源”,《人类学年度评论》2:271-310(1973年);杰克·哈兰,《作物与人类》,第2版(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美国农学会,1992年);理查德·麦克尼什,《农业与定居生活的起源》(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2年);戴维·林多斯,《农业的起源:进化视角》(圣迭戈:学术出版社,1984年);以及布鲁斯·史密斯,《农业的出现》(纽约:科学美国人图书馆,1995年)。关于粮食生产总体的其他重要参考文献包括两本多作者合著:彼得·乌科和G·W·丁布尔比编,《植物和动物的驯化与开发》(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9年),以及查尔斯·里德编,《农业起源》(海牙:穆顿出版社,1977年)。卡尔·绍尔,《农业起源与传播》(纽约:美国地理学会,1952年)是早期比较旧世界和新世界粮食生产的经典之作,而埃里希·艾萨克,《驯化地理学》(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0年)探讨了植物和动物驯化的地点、时间和方式问题。
在专门关于植物驯化的参考文献中,丹尼尔·佐哈里和玛丽亚·霍普夫的《旧世界植物的驯化》,第2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最为突出。它提供了世界任何地区植物驯化最详细的记述。对于西欧亚大陆种植的每种重要作物,该书总结了关于其驯化和后续传播的考古和遗传证据。
关于植物驯化的重要多作者著作包括C·韦斯利·考恩和帕蒂·乔·沃森编,《农业的起源》(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2年),戴维·哈里斯和戈登·希尔曼编,《觅食与耕作:植物利用的进化》(伦敦:昂温海曼出版社,1989年),以及C·巴里戈齐编,《栽培植物的起源与驯化》(阿姆斯特丹:爱思唯尔出版社,1986年)。小查尔斯·海瑟撰写的两本引人入胜的植物驯化通俗读物是《从种子到文明:食物的故事》,第3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关于植物与人类》(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5年)。J·斯马特和N·W·西蒙兹编,《作物植物的进化》,第2版(伦敦:朗文出版社,1995年)是总结世界所有主要作物和许多次要作物信息的标准参考卷。三篇优秀论文描述了野生植物在人类栽培下自动演化的变化:马克·布卢姆勒和罗杰·伯恩,“驯化的生态遗传学与农业起源”,《当代人类学》32:23-54(1991年);小查尔斯·海瑟,“无意识选择的各个方面与栽培植物的进化”,《育种学》37:77-81(1988年);以及丹尼尔·佐哈里,“植物在驯化下的进化模式”,收录于W·F·格兰特编,《植物生物系统学》(蒙特利尔:学术出版社,1984年)。马克·布卢姆勒,“独立发明论与植物驯化的最新遗传证据”,《经济植物学》46:98-111(1992年),评估了同一野生植物物种多次驯化的证据,相对于单一起源随后传播的情况。
关于动物驯化相关的通用著作,世界野生哺乳动物的标准百科全书参考作品是Ronald Nowak编著的《Walker’s Mammals of the World》第5版(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Juliet Clutton-Brock的《Domesticated Animals from Early Times》(伦敦: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1981年)对所有重要的驯化哺乳动物进行了出色的总结。I. L. Mason编著的《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伦敦:朗文出版社,1984年)是一部多作者合著的著作,分别讨论了每种重要的驯化动物。Simon Davis的《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对考古遗址中哺乳动物骨骼所能提供的信息进行了出色的阐述。Juliet Clutton-Brock编著的《The Walking Larder》(伦敦:Unwin-Hyman出版社,1989年)收录了31篇论文,探讨了世界各地人类如何驯化、放牧、狩猎动物以及被动物狩猎的情况。关于驯化动物的一部德语综合著作是Wolf Herre和Manfred Röhrs的《Haustiere zoologisch gesehen》(斯图加特:Fischer出版社,1990年)。Stephen Budiansky的《The Covenant of the Wild》(纽约: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92年)是一部关于动物驯化如何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中自动演化而来的通俗读物。关于驯化动物如何被用于耕作、运输、获取羊毛和奶的一篇重要论文是Andrew Sheratt的”Plough and pastoralism: Aspects of the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收录于Ian Hodder等人编著的《Pattern of the Past》第261–305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关于世界特定地区粮食生产的记述包括:Pliny的《Natural History》第17–19卷(Loeb古典文库版,拉丁文与英文对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这是一部对罗马农业实践进行详尽记录的迷你百科全书;Albert Ammerman和L. L. Cavalli-Sforza的《The Neolithic Transition and the Genetics of Populations in Europ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分析了粮食生产从新月沃地向西穿越欧洲的传播;Graeme Barker的《Prehistoric Farming in Europ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以及Alasdair Whittle的《Neolithic Europe: A Surve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涉及欧洲地区;Donald Henry的《From Foraging to Agriculture: The Levant at the End of the Ice Age》(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涉及地中海东岸沿岸地区;以及D. E. Yen的”Domestication: Lessons from New Guinea”,收录于Andrew Pawley编著的《Man and a Half》第558–69页(奥克兰:波利尼西亚学会,1991年),涉及新几内亚。Edward Schafer的《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描述了唐朝时期输入中国的动物、植物和其他物品。
以下是关于世界特定地区植物驯化和作物的记述。关于欧洲和新月沃地:Willem van Zeist等人编著的《Progress in Old World Palaeoethnobotany》(鹿特丹:Balkema出版社,1991年)以及Jane Renfrew的《Paleoethnobotany》(伦敦:Methuen出版社,1973年)。关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以及印度次大陆:Steven Weber的《Plants and Harappan Subsistence》(新德里:美国印度研究所,1991年)。关于新大陆作物:Charles Heiser, Jr.的”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World domesticated plants: Summary”,载于《Economic Botany》44(3 suppl.): 111–16(1990年),以及同一作者的”Origins of some cultivated New World plants”,载于《Annual Reviews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0:309–26(1979年)。关于一个可能记录了中美洲从狩猎采集向早期农业过渡的墨西哥遗址:Kent Flannery编著的《Guilá Naquitz》(纽约:学术出版社,1986年)。关于印加时期安第斯地区种植的作物及其今日潜在用途的记述:国家研究委员会的《Lost Crops of the Incas》(华盛顿特区:国家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关于美国东部和/或西南部的植物驯化:Bruce Smith的”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载于《Science》246:1566–71(1989年);William Keegan编著的《Emergent Horticultural Economies of the Eastern Woodlands》(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1987年);Richard Ford编著的《Prehistoric Food Production in North America》(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1985年);以及R. G. Matson的《The Origins of Southwestern Agriculture》(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年)。Bruce Smith的”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Americas”,载于《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3:174–84(1995年),讨论了基于极小植物样本的加速器质谱测年法的修正观点,认为美洲农业的起源比以前认为的要晚得多。
以下是关于世界特定地区动物驯化和家畜的记述。关于中欧和东欧:S. Bökönyi的《History of Domestic Mammal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布达佩斯:Akadémiai Kiadö出版社,1974年)。关于非洲:Andrew Smith的《Pastoralism in Africa》(伦敦:Hurst出版社,1992年)。关于安第斯地区:Elizabeth Wing的”Domestication of Andean mammals”,收录于F. Vuilleumier和M. Monasterio编著的《High Altitude Tropical Biogeography》第246–64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
关于特定重要作物的参考文献包括以下内容。Thomas Sodestrom等人编著的《禾本科系统学与进化》(Grass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87年)是一部关于禾本科植物的综合性多作者著作,禾本科植物孕育了我们的谷物,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Hugh Iltis的”从大刍草到玉米:灾难性的性转变”(From teosinte to maize: The catastrophic sexual transmutation),《科学》222:886-94(1983年),阐述了玉米从其野生祖先大刍草进化过程中所涉及的繁殖生物学方面的剧烈变化。严文明的”中国最早的水稻农业遗存”(China’s earliest rice agricultural remains),《印度-太平洋史前学会会刊》10:118-26(1991年),讨论了中国南方早期的水稻驯化。Charles Heiser, Jr.的两本书是关于特定作物的通俗读物:《向日葵》(The Sunflower)(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6年)和《葫芦之书》(The Gourd Book)(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9年)。
许多论文或书籍专门论述特定的驯化动物物种。R. T. Loftus等人的”牛的两次独立驯化的证据”(Evidence for two independent domestications of cattl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91:2757-61(1994年),利用线粒体DNA证据证明牛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印度次大陆被独立驯化。关于马:Juliet Clutton-Brock的《马力》(Horse Power)(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Richard Meadow和Hans-Peter Uerpmann编著的《古代世界的马科动物》(Equids in the Ancient World)(威斯巴登:Reichert出版社,1986年),Matthew J. Kust的《历史中的人与马》(Man and Horse in History)(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普鲁塔克出版社,1983年),以及Robin Law的《马在西非历史中的地位》(The Hors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关于猪:Colin Groves的《猪的祖先:猪属的分类学与系统发育》(Ancestors for the Pigs: Taxonomy and Phylogeny of the Genus Sus)(第3号技术公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史前学系[1981年])。关于美洲驼:Kent Flannery、Joyce Marcus和Robert Reynolds的《瓦马尼的羊群》(The Flocks of the Wamani)(圣地亚哥:学术出版社,1989年)。关于狗:Stanley Olsen的《家犬的起源》(Origins of the Domestic Dog)(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John Varner和Jeannette Varner的《征服之犬》(Dogs of the Conquest)(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3年),描述了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期间使用狗作为军事武器杀害印第安人。Clive Spinnage的《羚羊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telopes)(纽约:Facts on File出版社,1986年),介绍了羚羊的生物学知识,因此为理解为什么这些看似明显的驯化候选者实际上都没有被驯化提供了起点。Derek Goodwin的《家禽》(Domestic Birds)(伦敦:博物馆出版社,1965年),总结了已被驯化的鸟类物种,R. A. Donkin的《疣鼻栖鸭》(The Muscovy Duck Cairina moschata domestica)(鹿特丹:Balkema出版社,1989年),讨论了新大陆仅有的两种被驯化的鸟类之一。
最后,校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的复杂性在以下文献中得到讨论:G. W. Pearson的”如何应对校准”(How to cope with calibration),《古物》61:98-103(1987年),R. E. Taylor编著的《四十年后的放射性碳:跨学科视角》(Radiocarbon after Four Decade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纽约:施普林格出版社,1992年),M. Stuiver等人的”校准”(Calibration),《放射性碳》35:1-244(1993年),S. Bowman的”使用放射性碳:更新”(Using radiocarbon: An update),《古物》68:838-43(1994年),以及R. E. Taylor、M. Stuiver和C. Vance Haynes, Jr.的”晚更新世放射性碳时间尺度的校准:克洛维斯和福尔索姆年龄估计”(Calibration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radiocarbon time scale: Clovis and Folsom age estimates),《古物》第70卷(1996年)。
关于疾病对人类群体影响的扣人心弦的描述,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有多种译本)。
关于历史上疾病的三部经典著作是Hans Zinsser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35年),Geddes Smith的《降临我们的瘟疫》(A Plague on Us)(纽约:联邦基金会,1941年),以及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纽约花园城:Doubleday出版社,1976年)。最后一本书由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非医生撰写,在促使历史学家认识疾病的影响方面特别有影响力,Alfred Crosby在序言的延伸阅读中列出的两本书也是如此。
Friedrich Vogel和Arno Motulsky的《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第2版(柏林:施普林格出版社,1986年),这本人类遗传学的标准教科书,是关于疾病对人类群体的自然选择以及针对特定疾病的遗传抗性发展的便捷参考。Roy Anderson和Robert May的《人类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s of Human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对疾病动力学、传播和流行病学的清晰数学处理。MacFarlane Burnet的《传染病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3年),是一位杰出医学研究者的经典著作,而Arno Karlen的《人类与微生物》(Man and Microbes)(纽约:Putnam出版社,1995年),是最近的一部通俗读物。
专门讨论人类传染病进化的书籍和文章包括Aidan Cockburn的《传染病:它们的进化与根除》(Infectious Diseases: Their Evolution and Eradication)(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Thomas出版社,1967年);同一作者的”我们的传染病从哪里来?“(Where did our infectious diseases come from?),载于《部落社会中的健康与疾病》(Health and Disease in Tribal Societies)第103-13页,CIBA基金会研讨会,第49号(阿姆斯特丹:Elsevier出版社,1977年);George Williams和Randolph Nesse的”达尔文医学的黎明”(The dawn of Darwinian medicine),《生物学季评》66:1-62(1991年);以及Paul Ewald的《传染病的进化》(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Francis Black, “原始社会中的传染病,” 科学 187:515–18 (1975), 讨论了地方性疾病和急性疾病对小型孤立社会的影响及其在这些社会中维持的差异。Frank Fenner, “粘液瘤病毒和穴兔:两个殖民物种,” pp. 485–501 in H. G. Baker and G. L. Stebbins, eds., 殖民物种的遗传学 (纽约: Academic Press, 1965), 描述了粘液瘤病毒在澳大利亚兔子中的传播和演化。Peter Panum, 1846年法罗群岛麻疹流行期间的观察 (纽约: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40), 说明了急性流行病如何在孤立的无抵抗力人群中迅速杀死或使整个人群免疫。Francis Black, “岛屿人群中麻疹的地方性流行:临界社区规模及其进化意义,” 理论生物学杂志 11:207–11 (1966), 利用这些麻疹流行来计算维持麻疹所需的最小人口规模。Andrew Dobson, “寄生虫诱导的宿主行为改变的种群生物学,” 生物学季刊评论 63:139–65 (1988), 讨论了寄生虫如何通过改变宿主行为来增强自身的传播。Aidan Cockburn and Eve Cockburn, eds., 木乃伊、疾病和古代文化 (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展示了从木乃伊中可以了解到的关于疾病过去影响的知识。
关于疾病对先前未接触人群影响的记述,Henry Dobyns, 他们的数量变得稀少 (诺克斯维尔: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收集证据支持欧洲引入的疾病杀死了多达95%的美洲原住民这一观点。随后支持这一有争议论点的书籍或文章包括John Verano and Douglas Ubelaker, eds., 美洲的疾病与人口统计 (华盛顿特区: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Ann Ramenofsky, 死亡的载体 (阿尔伯克基: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Russell Thornton, 美洲印第安人大屠杀与生存 (诺曼: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和Dean Snow, “与前哥伦布时期北美印第安人口规模相关的微观年代学和人口学证据,” 科学 268:1601–4 (1995)。两篇关于欧洲引入疾病导致夏威夷波利尼西亚人口减少的记述是David Stannard, 恐怖之前:西方接触前夕夏威夷的人口 (檀香山: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和O. A. Bushnell, 文明的礼物:夏威夷的病菌与种族灭绝 (檀香山: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1902–3年冬季痢疾流行几乎灭绝Sadlermiut爱斯基摩人的事件由Susan Rowley描述, “Sadlermiut人:神秘还是被误解?” pp. 361–84 in David Morrison and Jean-Luc Pilon, eds., 北极史前的线索 (赫尔: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1994)。相反的现象,即欧洲人因在海外遇到的疾病而死亡,由Philip Curtin讨论, 迁移导致的死亡:19世纪欧洲与热带世界的遭遇 (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在关于特定疾病的记述中,Stephen Morse, ed., 新兴病毒 (纽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包含许多关于人类”新”病毒性疾病的有价值章节;Mary Wilson et al., eds., 演化中的疾病, 纽约科学院年刊, vol. 740 (纽约, 1995)也是如此。其他疾病的参考文献包括以下内容。关于鼠疫:Colin McEvedy, “鼠疫,” 科学美国人 258(2): 118–23 (1988)。关于霍乱:Norman Longmate, 霍乱之王 (伦敦: Hamish Hamilton, 1966)。关于流感:Edwin Kilbourne, 流感 (纽约: Plenum, 1987), 和Robert Webster et al., “甲型流感病毒的演化与生态学,” 微生物学评论 56:152–79 (1992)。关于莱姆病:Alan Barbour and Durland Fish, “莱姆病的生物学和社会现象,” 科学 260:1610–16 (1993), 和Allan Steere, “莱姆病:对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威胁,”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91:2378–83 (1994)。
关于人类疟疾寄生虫的进化关系:Thomas McCutchan等人,“由DNA结构确定的疟原虫(Plasmodium)物种的进化亲缘关系”,《科学》(Science)225:808–11(1984),以及A. P. Waters等人,“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似乎是鸟类和人类宿主之间横向转移的结果”,《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88:3140–44(1991)。关于麻疹病毒的进化关系:E. Norrby等人,“牛瘟病毒是否是麻疹病毒属(Morbillivirus)的原始病毒?”《病毒学访谈》(Intervirology)23:228–32(1985),以及Keith Murray等人,“一种在马和人类中引起致命疾病的麻疹病毒”,《科学》268:94–97(1995)。关于百日咳(pertussis),也称为whooping cough:R. Gross等人,“百日咳毒素的遗传学”,《分子微生物学》(Molecular Microbiology)3:119–24(1989)。关于天花:Donald Hopkins,《王子与农民:历史上的天花》(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F. Vogel和M. R. Chakravartti,“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印度)农村人口的ABO血型与天花”,《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3:166–80(1966);以及我的文章”基因上的痘疫”,《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99(2):26–30(1990)。关于猴痘,一种与天花相关的疾病:Zdeněk Ježek和Frank Fenner,《人类猴痘》(Human Monkeypox)(巴塞尔:Karger出版社,1988)。关于梅毒:Claude Quétel,《梅毒史》(History of Syphilis)(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关于肺结核:Guy Youmans,《肺结核》(Tuberculosis)(费城:Saunders出版社,1979)。关于人类肺结核在哥伦布抵达前就存在于美洲原住民中的说法:支持方,Wilmar Salo等人,“在哥伦布时代之前的秘鲁木乃伊中鉴定出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DNA”,《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91:2091–94(1994);反对方,William Stead等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何时首次在新大陆发生?”《美国呼吸与重症监护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Critical Care Medicine)151:1267–68(1995)。
提供文字及特定文字系统概述的书籍包括David Diringer的《文字》(Writing)(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82),I. J. Gelb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Geoffrey Sampson的《文字系统》(Writing System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John DeFrancis的《可见的语言》(Visible Speech)(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9),Wayne Senner主编的《文字的起源》(The Origins of Writing)(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1),以及J. T. Hooker主编的《解读过去》(Reading the Past)(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版社,1990)。David Diringer的《字母表》(The Alphabet)第3版,2卷(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68)是关于重要文字系统的全面叙述,附有描绘每种系统文本的图版。Jack Goody的《野蛮心智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以及Robert Logan的《字母表效应》(The Alphabet Effect)(纽约:Morrow出版社,1986),讨论了一般读写能力和特别是字母表的影响。Nicholas Postgate等人的”早期文字的证据:实用性还是仪式性?“《古物》(Antiquity)69:459–80(1995)讨论了早期文字的用途。
以下书籍提供了关于破译以前无法识别文字的激动人心的记述:Maurice Pope的《破译的故事》(The Story of Decipherment)(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75),Michael Coe的《破解玛雅密码》(Breaking the Maya Code)(纽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92),John Chadwick的《线形文字B的破译》(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Yves Duhoux、Thomas Palaima和John Bennet主编的《破译中的问题》(Problems in Decipherment)(鲁汶:Peeters出版社,1989),以及John Justeson和Terrence Kaufman的”埃皮-奥尔梅克象形文字的破译”,《科学》259:1703–11(1993)。
Denise Schmandt-Besserat的两卷本《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2)提出了她关于苏美尔文字起源于近5000年历程中的陶土标记(clay tokens)的有争议的重建。Hans Nissen等人主编的《古代簿记》(Archaic Bookkeeping)(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描述了代表楔形文字本身最早阶段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Joseph Naveh的《字母表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the Alphabet)(莱顿:Brill出版社,1982)追溯了东地中海地区字母表的出现。Gernot Windfuhr的”乌加里特的楔形文字符号”,《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29:48–51(1970)讨论了引人注目的乌加里特字母表。Joyce Marcus的《中美洲文字系统:四个古代文明中的宣传、神话和历史》(Mesoamerican Writing Systems: Propaganda, Myth, and History in Four Ancient Civilization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以及Elizabeth Boone和Walter Mignolo的《无字之书写》(Writing without Word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4),描述了中美洲文字系统的发展和用途。William Boltz的《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与早期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纽黑文:美国东方学会,1994),以及同一作者的”早期中国文字”,《世界考古学》(World Archaeology)17:420–36(1986),对中国文字做了同样的研究。最后,Janet Klausner的《塞阔亚的礼物》(Sequoyah’s Gift)(纽约:HarperCollins出版社,1993)是一本儿童可读、但对成人同样有趣的书,讲述了塞阔亚发展切罗基音节文字的故事。
技术史的标准详细著作是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等人的八卷本《技术史》(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4-84)。单卷本的技术史包括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的《丰塔纳技术史》(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94),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以及特雷弗·威廉姆斯(Trevor Williams)的《发明的历史》(纽约:事实档案出版社,1987)。R. A. 布坎南(R. A. Buchanan)的《机器的力量》(伦敦:企鹅图书,1994)是一部简短的技术史,聚焦于公元1700年以来的几个世纪。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财富的杠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探讨了为什么技术发展速度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技术的进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提出了技术变革的进化观点。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的扩散》第三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83)总结了关于创新传播的现代研究,包括QWERTY键盘。大卫·霍洛韦(David Holloway)的《斯大林与原子弹》(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剖析了蓝图复制、思想扩散(通过间谍活动)和独立发明对苏联原子弹的相对贡献。
区域技术史著作中最杰出的是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系列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以来已出版5卷16部分,还有十几部分即将出版。艾哈迈德·哈桑(Ahmad al-Hassan)和唐纳德·希尔(Donald Hill)的《伊斯兰技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以及K. D. 怀特(K. D. White)的《希腊和罗马技术》(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84)总结了这些文化的技术史。
两个显著的例子涉及某些相对孤立的社会采用然后放弃在与其他社会竞争中可能有用的技术,包括日本在公元1543年采用火器后又放弃,以及中国在公元1433年后放弃其大型远洋舰队。前一个案例由诺埃尔·佩林(Noel Perrin)在《放弃枪支》(波士顿:霍尔出版社,1979)中描述,后者由路易丝·莱瓦西斯(Louise Levathes)在《当中国统治海洋》(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4)中描述。W. H. B. 里弗斯(W. H. B. Rivers)的《心理学与民族学》(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26)第190-210页中题为”有用技艺的消失”的文章给出了太平洋岛民中的类似例子。
关于技术史的文章可以在《技术与文化》季刊上找到,该刊物自1959年以来由技术史学会出版。约翰·斯陶登迈尔(John Staudenmaier)的《技术的讲述者》(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分析了该刊物前二十年的论文。
为对技术史感兴趣的人提供材料的具体领域包括电力、纺织和冶金。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权力网络》(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讨论了1880年至1930年西方社会电气化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因素。达瓦·索贝尔(Dava Sobel)的《经度》(纽约:沃克出版社,1995)描述了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的航海天文钟的发展,这解决了在海上确定经度的问题。E. J. W. 巴伯(E. J. W. Barber)的《史前纺织品》(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阐述了欧亚大陆从9000多年前开始的布料历史。广泛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冶金史著作包括罗伯特·马丁(Robert Maddin)的《金属和合金使用的开端》(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西奥多·沃蒂姆(Theodore Wertime)和詹姆斯·穆利(James Muhly)编辑的《铁器时代的到来》(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R. D. 彭哈卢里克(R. D. Penhallurick)的《古代的锡》(伦敦:金属学会,1986),詹姆斯·穆利的”铜和锡”,《康涅狄格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刊》43:155-535(1973),以及艾伦·富兰克林(Alan Franklin)、杰奎琳·奥林(Jacqueline Olin)和西奥多·沃蒂姆的《寻找古代的锡》(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78)。地方区域的冶金史著作包括R. F. 泰勒科特(R. F. Tylecote)的《欧洲冶金早期史》(伦敦:朗文出版社,1987),以及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的《中国古代的铁与钢》(莱顿:布里尔出版社,1993)。
第14章
人类社会四分类为游群(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和国家(states),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埃尔曼·瑟维斯的两本书:《原始社会组织》(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纽约:诺顿出版社,1975年)。莫顿·弗里德的《政治社会的演化》(纽约:兰登书屋,1967年)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对社会进行了相关分类。关于国家和社会演化的三篇重要综述文章是肯特·弗兰纳里的”文明的文化演化”,《生态学与系统学年度评论》3:399-426(1972年),同一作者的”史前社会演化”,第1-26页,收录于卡罗尔和梅尔文·恩伯编辑的《人类学研究前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95年),以及亨利·赖特的”国家起源的最新研究”,《人类学年度评论》6:379-97(1977年)。罗伯特·卡内罗在”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733-38(1970年)中论证,在土地生态受限的条件下,国家通过战争而产生。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将国家起源与大规模灌溉和水利管理联系起来。威廉·桑德斯、亨利·赖特和罗伯特·亚当斯在《论复杂社会的演化》(马里布:昂德纳出版社,1984年)中的三篇论文提出了关于国家起源的不同观点,而罗伯特·亚当斯的《城市社会的演化》(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6年)对比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的国家起源。
关于世界特定地区社会演化的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来源包括罗伯特·亚当斯的《城市中心地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J·N·波斯特盖特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中美洲方面有理查德·布兰顿等人的《古代中美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乔伊斯·马库斯与肯特·弗兰纳里的《萨波特克文明》(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96年);安第斯地区有理查德·伯格的《查文与安第斯文明的起源》(纽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92年)和乔纳森·哈斯等人编辑的《安第斯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美洲酋邦方面有罗伯特·德伦南和卡洛斯·乌里韦编辑的《美洲的酋邦》(拉纳姆,马里兰州:美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波利尼西亚社会参见第2章引用的书籍;祖鲁国家参见唐纳德·莫里斯的《长矛的洗礼》(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社,1966年)。
涵盖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史前史的书籍包括艾伦·索恩和罗伯特·雷蒙德的《边缘人:太平洋的人类迁徙》(北赖德:安格斯与罗伯逊出版社,1989年),J·彼得·怀特和詹姆斯·奥康奈尔的《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萨胡尔大陆的史前史》(悉尼:学术出版社,1982年),吉姆·艾伦等人编辑的《巽他大陆与萨胡尔大陆》(伦敦:学术出版社,1977年),M·A·史密斯等人编辑的《萨胡尔大陆回顾》(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93年),以及蒂姆·弗兰纳里的《未来的食客》(纽约:布拉齐勒出版社,1995年)。这些书中的第一本和第三本还讨论了东南亚岛屿的史前史。最近关于澳大利亚本身历史的著作是约瑟芬·弗洛德的《梦幻时代的考古学》修订版(悉尼:柯林斯出版社,1989年)。关于澳大利亚史前史的其他一些重要论文包括里斯·琼斯的”第五大陆:关于澳大利亚人类殖民的问题”,《人类学年度评论》8:445-66(1979年),理查德·罗伯茨等人的”澳大利亚北部5万年前人类居住遗址的热释光测年”,《自然》345:153-56(1990年),以及吉姆·艾伦和西蒙·霍尔达韦的”澳大利亚更新世放射性碳测定的污染问题”,《古物》69:101-12(1995年)。罗伯特·阿滕伯勒和迈克尔·阿尔珀斯编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类生物学》(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2年)总结了新几内亚的考古学以及语言和遗传学。
至于北美拉尼西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位于新几内亚东北和东部)的史前史,可以在上述索恩和雷蒙德、弗兰纳里以及艾伦等人的书中找到讨论。将北美拉尼西亚最早占领年代向前推的论文包括斯蒂芬·威克勒和马修·斯普里格斯的”美拉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的更新世人类占领”,《古物》62:703-6(1988年),吉姆·艾伦等人的”北美拉尼西亚新爱尔兰人类占领的更新世年代”,《自然》331:707-9(1988年),吉姆·艾伦等人的”热带岛屿太平洋的人类更新世适应:来自大澳大利亚外围新爱尔兰的最新证据”,《古物》63:548-61(1989年),以及克里斯蒂娜·帕夫利德斯和克里斯·戈斯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西新不列颠雨林中的3万5千年前遗址”,《古物》68:604-10(1994年)。关于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沿新几内亚海岸扩张的参考文献可在第17章的延伸阅读中找到。
关于欧洲殖民后澳大利亚历史的两本书是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致命海岸》(纽约:Knopf出版社,1987年)和迈克尔·坎农(Michael Cannon)的《澳大利亚探险史》(悉尼:读者文摘出版社,1987年)。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本身的研究有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roome)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悉尼:Allen and Unwin出版社,1982年)和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的《边疆》(悉尼:Allen and Unwin出版社,1987年)。阿瑟·维希曼(Arthur Wichmann)的三卷本著作《新几内亚发现史》(莱顿:Brill出版社,1909-12年)是一部极为详尽的新几内亚历史,从最早的文字记录到1902年。一本更简短易读的著作是加文·索特(Gavin Souter)的《新几内亚:最后的未知之地》(悉尼:Angus and Robertson出版社,1964年)。鲍勃·康诺利(Bob Connolly)和罗宾·安德森(Robin Anderson)的《首次接触》(纽约:Viking出版社,1987年)动人地描述了新几内亚高地人与欧洲人的首次相遇。
关于新几内亚巴布亚语系(即非南岛语系)语言的详细论述,参见斯蒂芬·伍尔姆(Stephen Wurm)的《大洋洲巴布亚语言》(图宾根:Gunter Narr出版社,1982年)和威廉·福利(William Foley)的《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关于澳大利亚语言,参见斯蒂芬·伍尔姆的《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语言》(海牙:Mouton出版社,1972年)和R. M. W. 迪克森(Dixon)的《澳大利亚语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
关于新几内亚植物驯化和粮食生产起源文献的入门资料可参见杰克·戈尔森(Jack Golson)的”布尔默二期:新几内亚高地的早期农业”,载于安德鲁·波利(Andrew Pawley)编《一个半人》(奥克兰:波利尼西亚学会,1991年),第484-91页;以及D. E. 延(Yen)的”波利尼西亚栽培植物和品种:起源问题”,载于保罗·考克斯(Paul Cox)和桑德拉·巴纳克(Sandra Banack)编《岛屿、植物与波利尼西亚人》(波特兰:Dioscorides出版社,1991年),第67-95页。
许多文章和书籍致力于探讨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对澳大利亚的贸易访问只产生了有限的文化变化。C. C. 麦克奈特(Macknight)的”望加锡人与原住民”,《大洋洲》42:283-321(1972年),讨论了望加锡人的访问,而D. 沃克(Walker)编的《桥梁与屏障:托雷斯海峡的自然与文化史》(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2年)讨论了托雷斯海峡的联系。这两种联系也在上述弗拉德(Flood)、怀特和奥康奈尔(White and O’Connell)以及艾伦等人(Allen et al.)的书中讨论。
关于塔斯马尼亚人的早期目击者记录收录在N. J. B. 普洛姆利(Plomley)的《鲍丹探险队与1802年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霍巴特:Blubber Head出版社,1983年)、N. J. B. 普洛姆利的《友好使命: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1829-1834年塔斯马尼亚日记与文件》(霍巴特:塔斯马尼亚历史研究协会,1966年)以及爱德华·杜伊克(Edward Duyker)的《塔斯马尼亚的发现:阿贝尔·扬松·塔斯曼和马克-约瑟夫·马里翁·迪弗雷纳1642年和1772年探险日记摘录》(霍巴特:圣大卫公园出版社,1992年)中。讨论隔离对塔斯马尼亚社会影响的论文包括里斯·琼斯(Rhys Jones)的”塔斯马尼亚悖论”,载于R. V. S. 赖特(Wright)编《作为文化标记的石器工具》(堪培拉: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所,1977年),第189-284页;里斯·琼斯的”为什么塔斯马尼亚人停止吃鱼?“,载于R. 古尔德(Gould)编《民族考古学探索》(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1-48页;D. R. 霍顿(Horton)的”塔斯马尼亚适应”,《人类》12:28-34(1979年);I. 沃尔特斯(Walters)的”为什么塔斯马尼亚人停止吃鱼?:理论思考”,《人工制品》6:71-77(1981年);以及里斯·琼斯的”塔斯马尼亚考古学”,《人类学年度评论》24:423-46(1995年)。罗宾·西姆(Robin Sim)在弗林德斯岛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她的文章”巴斯海峡金岛和弗诺岛地区的史前人类占据”中有所描述,载于玛乔丽·沙利文(Marjorie Sullivan)等编《北方考古学》(达尔文:北澳大利亚研究所,1994年),第358-74页。
之前章节引用的相关文献包括关于东亚粮食生产(第4-10章)、中国文字(第12章)、中国技术(第13章)以及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总体内容(第15章)。詹姆斯·马蒂索夫(James Matisoff)的”汉藏语言学:现状与未来展望”,《人类学年度评论》20:469-504(1991年),回顾了汉藏语系及其更广泛的关系。赤泽威(Takeru Akazawa)和埃默克·萨特马里(Emoke Szathmáry)编《史前蒙古人种扩散》(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丹尼斯·埃特勒(Dennis Etler)的”中国人类生物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综述”,《人类生物学》64:567-85(1992年),讨论了中国或东亚关系和扩散的证据。艾伦·索恩(Alan Thorne)和罗伯特·雷蒙德(Robert Raymond)的《边缘上的人类》(北赖德:Angus and Robertson出版社,1989年)描述了太平洋民族的考古学、历史和文化,包括东亚人和太平洋岛民。阿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和苏珊·瑟坚特森(Susan Serjeantson)编《太平洋的殖民:遗传轨迹》(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9年),根据推断的殖民路线和历史解释了太平洋岛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几内亚人的遗传学。基于牙齿结构的证据由克里斯蒂·特纳三世(Christy Turner III)在”基于牙齿变异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东亚人口历史”,《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73:305-21(1987年)和”亚洲的牙齿与史前史”,《科学美国人》260 (2): 88-96(1989年)中进行了解释。
在考古学的区域性论述中,中国的部分由张光直著《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David Keightley 编辑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以及 David Keightley 的《考古学与心智:中国的形成》,《表征》18:91–128(1987年)所涵盖。Mark Elvin 的《中国过去的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研究了中国自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关于东南亚的便捷考古学论述包括 Charles Higham 的《东南亚大陆考古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关于朝鲜,Sarah Nelson 的《朝鲜考古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热带东南亚,Peter Bellwood 的《印度-马来群岛史前史》(悉尼:学术出版社,1985年);关于马来半岛,Peter Bellwood 的《马来半岛的文化和生物分化:过去一万年》,《亚洲视角》32:37–60(1993年);关于印度次大陆,Bridget 和 Raymond Allchin 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文明的兴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关于岛屿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特别强调拉皮塔文化(Lapita),《古物》63:547–626(1989年)中的五篇系列文章以及 Patrick Kirch 的《拉皮塔人:大洋洲世界的祖先》(伦敦: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1996年);关于整个南岛语系(Austronesian)的扩张,Andrew Pawley 和 Malcolm Ross 的《南岛历史语言学与文化史》,《人类学年评》22:425–59(1993年),以及 Peter Bellwood 等人的《南岛民族:比较和历史视角》(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95年)。
Geoffrey Irwin 的《太平洋的史前探索和殖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波利尼西亚航海、导航和殖民的论述。新西兰和东波利尼西亚定居时间的争论见 Atholl Anderson 的《新西兰殖民的年代学》,《古物》65:767–95(1991年),以及《东波利尼西亚殖民研究的当前方法》,《波利尼西亚学会期刊》104:110–32(1995年),以及 Patrick Kirch 和 Joanna Ellison 的《人类殖民偏远大洋岛屿的古环境证据》,《古物》68:310–21(1994年)。
本章的许多相关延伸阅读将在其他章节下列出:第3章中关于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征服,第4–10章中关于植物和动物驯化,第11章中关于传染病,第12章中关于文字,第13章中关于技术,第14章中关于政治制度,以及第16章中关于中国。关于粮食生产开始日期的全球便捷比较见 Bruce Smith 的《农业的出现》(纽约:科学美国人图书馆,1995年)。
除了前面章节中给出的参考文献外,表18.1中总结的历史轨迹的一些讨论如下。关于英格兰:Timothy Darvill 的《史前不列颠》(伦敦:Batsford 出版社,1987年)。关于安第斯地区:Jonathan Haas 等人的《安第斯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Michael Moseley 的《印加人及其祖先》(纽约: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1992年);以及 Richard Burger 的《查文文化与安第斯文明的起源》(纽约: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1992年)。关于亚马逊地区:Anna Roosevelt 的《帕尔马纳》(纽约:学术出版社,1980年),以及 Anna Roosevelt 等人的《巴西亚马逊史前贝冢中的第八个千年陶器》,《科学》254:1621–24(1991年)。关于中美洲:Michael Coe 的《墨西哥》第三版(纽约: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1984年),以及 Michael Coe 的《玛雅人》第三版(纽约: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1984年)。关于美国东部:Vincas Steponaitis 的《美国东南部史前考古学,1970–1985》,《人类学年评》15:363–404(1986年);Bruce Smith 的《美国东南部考古学:从道尔顿到德索托,公元前10,500–500年》,《世界考古学进展》5:1–92(1986年);William Keegan 编辑的《东部林地的新兴园艺经济》(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1987年);Bruce Smith 的《北美东部农业起源》,《科学》246:1566–71(1989年);Bruce Smith 的《密西西比文化的出现》(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0年);以及 Judith Bense 的《美国东南部考古学》(圣地亚哥:学术出版社,1994年)。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简明参考资料是 Philip Kopper 的《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北美印第安人史密森手册》(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86年)。Bruce Smith 的《美洲农业的起源》,《进化人类学》3:174–84(1995年)讨论了关于新世界粮食生产开始的早期与晚期日期的争议。
任何倾向于认为新大陆的粮食生产和社会受限于美洲原住民自身的文化或心理,而非可供驯化的野生物种局限性的人,应该参考三篇关于大平原印第安社会因马的到来而发生转变的记述:Frank Row,《印第安人与马》(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John Ewers,《黑脚族:西北平原的袭击者》(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8),以及Ernest Wallace和E. Adamson Hoebel,《科曼奇人:南部平原的领主》(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6)。
在关于语系传播与粮食生产兴起关系的讨论中,欧洲的经典研究是Albert Ammerman和L. L. Cavalli-Sforza的《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与欧洲人口遗传学》(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而Peter Bellwood的”南岛语系的扩散与语言起源”,《科学美国人》265(1): 88-93 (1991),则对南岛语系领域做了同样的研究。引用世界各地实例的研究包括L. L. Cavalli-Sforza等人的两本书以及Merritt Ruhlen的书,它们在序言的延伸阅读中被引用。两本对印欧语系扩张持截然相反解释的书为进入这一有争议的文献提供了入口:Colin Renfrew的《考古学与语言:印欧语系起源之谜》(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J. P. Mallory的《寻找印欧人》(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关于俄罗斯横跨西伯利亚扩张的资料来源有George Lantzeff和Richard Pierce的《向东扩张帝国》(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3),以及W. Bruce Lincoln的《征服一个大陆》(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至于美洲原住民语言,承认许多独立语系的多数派观点以Lyle Campbell和Marianne Mithun的《美洲原住民语言》(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79)为代表。相反的观点将所有美洲原住民语言(除了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纳-德内语系)归入美印语系,由Joseph Greenberg的《美洲语言》(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和Merritt Ruhlen的《世界语言指南》第1卷(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提出。
关于欧亚大陆运输用轮子的起源和传播的标准记述是M. A. Littauer和J. H. Crouwel的《古代近东的轮式车辆和骑乘动物》(Leiden: Brill, 1979),以及Stuart Piggott的《最早的轮式运输》(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3)。
关于格陵兰和美洲的诺斯殖民地兴衰的书籍包括Finn Gad的《格陵兰历史》第1卷(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1),G. J. Marcus的《征服北大西洋》(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Gwyn Jones的《诺斯大西洋传奇》第2版(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以及Christopher Morris和D. James Rackham编辑的《北大西洋的诺斯及后期定居与生计》(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92)。Samuel Eliot Morison的两卷著作提供了早期欧洲人航海到新大陆的精湛记述:《欧洲发现美洲:北方航程》,公元500-1600年(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和《欧洲发现美洲:南方航程》,公元1492-1616年(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欧洲海外扩张的开端由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哥伦布之前: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探索与殖民,1229-1492》(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探讨。不容错过的是哥伦布本人对历史上最著名航程的逐日记述,重印为Oliver Dunn和James Kelley, Jr.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美洲航程日记,1492-1493》(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作为本书中大多数冷静叙述人们如何征服或屠杀其他民族的解毒剂,可以阅读关于北加利福尼亚亚希部落毁灭及其唯一幸存者伊希现身的经典记述:Theodora Kroeber的《伊希在两个世界》(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美洲及其他地区原住民语言的消失是Robert Robins和Eugenius Uhlenbeck的《濒危语言》(Providence: Berg, 1991),Joshua Fishman的《逆转语言转移》(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以及Michael Krauss的”世界语言危机”,《语言》68:4-10 (1992)的主题。
第19章
关于非洲大陆的考古学、史前史和历史的书籍包括:Roland Oliver 和 Brian Fagan 的《铁器时代的非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Roland Oliver 和 J. D. Fage 的《非洲简史》第5版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J. D. Fage 的《非洲史》(London: Hutchinson, 1978),Roland Oliver 的《非洲经验》(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Thurstan Shaw 等人编辑的《非洲考古学:食物、金属和城镇》(New York: Routledge, 1993),以及 David Phillipson 的《非洲考古学》第2版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Christopher Ehret 和 Merrick Posnansky 编辑的《非洲历史的考古学和语言学重建》(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总结了非洲过去的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之间的关联。疾病的作用由 Gerald Hartwig 和 K. David Patterson 编辑的《非洲历史中的疾病》(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8) 讨论。
关于粮食生产,第4-10章列出的许多延伸阅读都讨论了非洲。还值得注意的有:Christopher Ehret 的”论埃塞俄比亚农业的古老性”,《非洲历史杂志》20:161–77 (1979);J. Desmond Clark 和 Steven Brandt 编辑的《从狩猎者到农民:非洲粮食生产的原因和后果》(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Art Hansen 和 Della McMillan 编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食物》(Boulder, Colo.: Rienner, 1986);Fred Wendorf 等人的”撒哈拉地区8000年前的植物利用”,《自然》359:721–24 (1992);Andrew Smith 的《非洲的畜牧业》(London: Hurst, 1992);以及 Andrew Smith 的”非洲畜牧业的起源和传播”,《人类学年度评论》21:125–41 (1992)。
关于马达加斯加的信息,两个起点是 Robert Dewar 和 Henry Wright 的”马达加斯加的文化史”,《世界史前史杂志》7:417–66 (1993),以及 Pierre Verin 的《马达加斯加北部的文明史》(Rotterdam: Balkema, 1986)。Otto Dahl 的《从加里曼丹到马达加斯加的迁徙》(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详细研究了关于马达加斯加殖民来源的语言学证据。A. M. Jones 的《非洲与印度尼西亚:木琴和其他音乐及文化因素的证据》(Leiden: Brill, 1971) 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与东非接触的可能音乐证据。关于马达加斯加早期定居的重要证据来自现已灭绝动物的年代测定骨骼,Robert Dewar 在 Paul Martin 和 Richard Klein 编辑的《第四纪灭绝》(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4) 第574–93页”马达加斯加的灭绝:亚化石动物群的消失”中进行了总结。R. D. E. MacPhee 和 David Burney 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已灭绝侏儒河马改造股骨的年代测定”,《考古科学杂志》18:695–706 (1991) 中报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后续化石发现。David Burney 的”马达加斯加中部全新世晚期植被变化”,《第四纪研究》28:130–43 (1987) 从古植物学证据评估了人类殖民的开始。
Tjeerd van Andel 等人的”阿戈利德南部五千年的土地使用和滥用”,《赫斯珀里亚》55:103–28 (1986),Tjeerd van Andel 和 Curtis Runnels 的《超越卫城:希腊的乡村过去》(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 Curtis Runnels 的”古希腊的环境退化”,《科学美国人》272(3): 72–75 (1995) 探讨了环境退化与希腊文明衰落之间的联系。Patricia Fall 等人在 Julio Betancourt 等人编辑的《啮齿动物粪堆》(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第408–27页”来自中东的蹄兔化石粪堆:古植被和人类干扰的记录”中,对佩特拉的衰落做了同样的研究,Robert Adams 的《城市腹地》(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则对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了类似研究。
E. L. Jones 的《欧洲奇迹》第2版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对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历史差异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Louise Levathes 的《当中国统治海洋时》(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描述了导致中国宝船舰队停航的权力斗争。第16章和第17章的延伸阅读为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其他参考文献。
Bennett Bronson 在 Norman Yoffee 和 George Cowgill 编辑的《古代国家和文明的崩溃》(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第196–218页”蛮族在国家衰落中的作用”中讨论了中亚游牧民对欧亚大陆定居农民复杂文明的影响。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与历史的可能相关性由 Michael Shermer 在论文”驱除拉普拉斯妖:混沌与反混沌,历史与元历史”,《历史与理论》34:59–83 (1995) 中讨论。Shermer 的论文还为 QWERTY 键盘的胜利提供了参考书目,Everett Rogers 的《创新扩散》第3版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也是如此。
Otto Wagener 作为希特勒座驾的乘客,对 1930 年几乎致希特勒于死地的交通事故进行了目击记录,这份记录可以在他的回忆录中找到。这些回忆录由 Henry Turner, Jr. 编辑成书,书名为《希特勒:一位知己的回忆录》(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8)。Turner 在 David Wetzel 主编的《德国历史:思想、制度与个人》(纽约:Praeger 出版社,1996)一书中的”希特勒对历史的影响”章节继续推测,如果希特勒在 1930 年去世会发生什么。
许多对长期历史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撰写了杰出著作,包括 Sidney Hook 的《历史中的英雄》(波士顿:Beacon 出版社,1943),Patrick Gardiner 主编的《历史理论》(纽约:Free 出版社,1959),Fernand Braudel 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纽约:Harper and Row 出版社,1979),Fernand Braudel 的《论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Peter Novick 的《那个崇高的梦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以及 Henry Hobhouse 的《变革的力量》(伦敦:Sedgewick and Jackson 出版社,1989)。
生物学家 Ernst Mayr 的几篇著作讨论了历史科学与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差异,特别涉及生物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对比,但 Mayr 所说的许多内容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他的观点可以在《进化与生命的多样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第 25 章,以及《迈向生物学新哲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第 1-2 章中找到。
流行病学家在不对人进行实验室实验的情况下,如何得出关于人类疾病因果关系结论的方法,在标准流行病学教材中有所讨论,例如 A. M. Lilienfeld 和 D. E. Lilienfeld 的《流行病学基础》第 3 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从生态学家的角度对自然实验的使用进行了探讨,见我在 Jared Diamond 和 Ted Case 主编的《群落生态学》(纽约:Harper and Row 出版社,1986)中撰写的”概述:实验室实验、野外实验和自然实验”章节,第 3-22 页。Paul Harvey 和 Mark Pagel 的《进化生物学中的比较方法》(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分析了如何通过比较物种来提取结论。
两篇文章和一本书总结了过去六年来关于植物和动物驯化、语系传播以及语系传播与粮食生产关系的发现:Jared Diamond,“植物和动物驯化的进化、后果和未来”,《自然》418:34-41(2002);Jared Diamond 和 Peter Bellwood,“最早的农业扩张:考古学、语言和人类”,《科学》,出版中;以及 Peter Bellwood 和 Colin Renfrew,《检验语言/农业扩散假说》(剑桥: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2002)。这两篇文章和那本书提供了详细近期文献的参考。关于农业扩张在现代日本人起源中的作用的近期专著是 Mark Hudson 的《身份的遗迹:日本列岛的民族起源》(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
有关新西兰毛利战争(Musket Wars)的详细记录,请参阅 R.D. Crosby 的著作《毛利战争:部落间冲突史 1806-45》(奥克兰:Reed 出版社,1999)。这些战争在 James Belich 的两本书中被更简要地总结,但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新西兰战争与维多利亚时代对种族冲突的解释》(奥克兰:Penguin 出版社,1986)和《造就民族:新西兰人的历史》(奥克兰:Penguin 出版社,1996)。
社会科学家为识别欧洲与中国分化背后的近因所做的两项近期努力包括 Jack Goldstone 的文章”世界历史中的繁荣与经济增长:重新思考’西方的崛起’和工业革命”,《世界历史杂志》13:323-89(2002),以及 Kenneth Pomeranz 的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相反的方法,即寻找终极原因,体现在 Graeme Lang 近期的文章”国家体系与现代科学的起源:欧洲与中国的比较”,《东西方对话》2:16-30(1997),以及 David Cosandey 的著作《西方的秘密》(巴黎:Arléa 出版社,1997)。Goldstone 和 Lang 的这些文章是我上述引用的来源。
分析现代财富或增长率的经济指标与国家社会或农业的长期历史之间联系的两篇论文是:Ola Olsson 和 Douglas Hibbs,“生物地理学与长期经济发展”,将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以及 Valerie Bockstette、Areendam Chanda 和 Louis Putterman,“国家与市场:早期起步的优势”,《经济增长杂志》7:351-73(2002)。
第 12 章:J. Beckett/K. Perkins,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 2A17202。
第 12 章:由 V.I.P. 出版社提供。
第 12 章:由 Myoung Soon Kim 和 Christie Kim 提供。
第 12 章和 233 页: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 13 章:伊拉克利翁博物馆,希腊共和国文化部。
第 96-97 页之间
图版 1 和 8:Irven DeVore,Anthro-Photo。
图版 2–5。作者提供。
图版 6。P. McLanahan,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337549。
图版 7。Richard Gould,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332911。
图版 9。J. W. Beattie,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12。
图版 10。Bogoras,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2975。
图版 11。AP/Wide World Photos。
图版 12。Judith Ferster,Anthro-Photo。
图版 13。R. H. Beck,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107814。
图版 14。Dan Hrdy,Anthro-Photo。
图版 15。Rodman Wanamaker,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316824。
图版 16。Marjorie Shostak,Anthro-Photo。
位于第 288 页和第 289 页之间
图版 17。Boris Malkin,Anthro-Photo。
图版 18。Napoleon Chagnon,Anthro-Photo。
图版 19。Kirschner,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235230。
图版 20、22、24、30 和 32。AP/Wide World Photos。
图版 21。Gladstone,Anthro-Photo。
图版 23。上图,AP/Wide World Photos。下图,W. B.,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2A13829。
图版 25。Marjorie Shostak,Anthro-Photo。
图版 26。Irven DeVore,Anthro-Photo。
图版 27。Steve Winn,Anthro-Photo。
图版 28。J.B. Thorpe,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编号 336181。
图版 29 和 31。J. F. E. Bloss,Anthro-Photo。
贾雷德·戴蒙德
读书小组指南
讨论问题
关于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科学生涯始于生理学,后扩展到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和生物地理学(biogeography)。他已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哲学学会成员,并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奖学金、Phi Beta Kappa 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Burr 奖和国家科学奖章。他已在Discover、Natural History、Nature和Geo杂志上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
[*]在本书中,关于过去约15,000年的日期将使用所谓的校准放射性碳定年法(calibrated radiocarbon dates),而不是传统的未校准放射性碳定年法(uncalibrated radiocarbon dates)。这两种定年法的区别将在第五章中解释。校准日期被认为更接近实际的日历日期。习惯于未校准日期的读者需要记住这一区别,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我引用的日期看起来有误,比他们熟悉的日期要更久远。例如,北美克洛维斯考古层位(Clovis archaeological horizon)的日期通常被引用为公元前9000年左右(11,000年前),但我将其引用为公元前11,000年左右(13,000年前),因为通常引用的日期是未校准的。